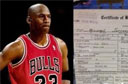邵華澤:我與攝影
學攝影,原本是連想都沒有想過的事。在解放軍報工作21年,都是同文字打交道,從沒有拿過照相機。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到人民日報社當總編輯。在工作中深感圖片新聞的重要性日益突顯,但由於種種原因,報紙刊用新聞圖片還是一個薄弱環節,離圖文並茂的要求還有相當距離。報社的同志和許多讀者都希望這方面的工作能有所加強和改進。在同一些兄弟報社的老總交談中,對此也多有同感。
1990年8月20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和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在銀川召開首屆全國報紙總編輯新聞攝影研討會。我根據了解的情況和實際工作中的體會,在大會上作了“兩個提高,一個關鍵”的發言,提出一是要提高對新聞攝影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二是要提高新聞攝影作品的質量。而要做到這兩個“提高”,關鍵在報社領導,特別是總編輯。這個觀點得到與會同志的認同。過了不久, 1991年1月11日,經我提議,召開了“人民日報新聞攝影座談會”,邀請了首都40多家報社攝影部門的負責人和部分攝影記者參加。與會同志肯定本報攝影報道的進步,同時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我在講話中表示:“能不能在抓好文字報道的同時,抓好新聞攝影報道,也是衡量工作成績的一個重要標志。如果不把這個環節抓好,那麼作為總編輯,應該說是一種失職。”又過了半年,1991年 8月10日,全國地市州盟報總編輯新聞攝影研討會在北戴河召開,到會的有40多位老總,我應邀到會上講話,題目就是“總編輯要親自抓新聞圖片”。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感到除了同大家一起採取多種措施加強新聞攝影工作之外,自己作為總編輯,也應該學一學新聞攝影,至少是表示一種重視,也增加一點發言權。於是,我決心拿起照相機:從零開始,邊學邊干。每次出差或出國訪問,我給自己定位,是總編輯,也是記者,必須帶上筆記本,隨時作文字記錄﹔也要背上相機,現場拍些照片。那個時候攝影還不普及,許多人看到我這個年近60的領導同志經常背個相機,還覺得挺新鮮的。有一件事特別讓我難忘。1994年9月4日晚,遠東及南太平洋殘疾人運動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我應邀出席開幕式,就座於主席台。在大型文藝表演進行時,我聽到靠我后面一排一位女同志正在給一位坐在身旁的人講解精彩的場景,那人一邊聽一邊贊嘆:“真是壯觀呀[真是壯觀呀[”我扭頭一看,兩位老人神情非常專注。當即站了起來,連按兩下快門。原來旁邊聽講的那位是盲人,而且是著名盲文專家、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黃乃,解說的是他的夫人。照片在人民日報刊出后,我接到不少表示稱贊的電話,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殘疾人激動地說,這體現了人民日報對殘疾人和殘疾人事業的關注,還對我表示感謝。這給我以很大鼓舞。這幅照片后來還在”改革之光”全國新聞攝影精品賽中獲得了“總編輯獎”。就這樣,我對攝影的興趣越來越濃,拍攝水平逐步有點提高,至今已堅持了二十余年,也積累了相當數量的作品。
曾經有人問我自己的攝影作品有何特點,我答:一、從來沒有預定拍攝計劃,多是利用出差和出國訪問,走到哪裡拍到那裡,全部作品都是現場抓拍的﹔二、因為是從學習新聞攝影開始的,因而比較關心社會,關注人,以拍攝人物為主:特別是婦女、兒童是我的最愛,有人開玩笑地說我攝影也是“以人為本”﹔ 三、鏡頭主要對著世間美好的東西。反映大自然之美,反映人類對美的追求和創造,反映人們和諧相處、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是我攝影作品的主旋律﹔四、在人民日報社任職十一年,在中國記協任職十年:因對外交往的需要,走的地方比較多,拍攝地域廣,遍及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實踐使我深深體悟到:
攝影是件需要下功夫去學習和探索的事情。攝影,看上去很簡單,但它是一種獨特的藝術,也是一門涉及多方面知識,檢驗一個人綜合素質的大學問,新聞攝影還要求新聞性、思想性和可觀性的統一,要真正懂得它掌握它絕非易事。我作為一個初學者,一是向書本學習,看各種通俗讀物、理論評論著作和攝影畫冊,更主要的是結合實踐向報社的攝影記者和內行的同志學習,同他們交朋友,向他們請教,送作品請他們點評。蔣鐸、王東、孟仁泉、劉振祥、張雅心、王忠家、魏銘祥、李培義等同志都給了許多幫助:我非常感激他們。2011年在千島湖藝術館一次座談會上,有人間我學習攝影最主要的體會是什麼,我說就五個字:“甘當小學生”。
攝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要想從千變萬化的生活中拍攝到好照片,必須勤觀察、勤跑動、勤思考。有時要走許多路,有時要等很長的時間,甚至還要費一些周折。特別是在任職期間,隻能在公務之余或結合參觀訪問拍攝一點作品,這就更需要有點毅力。
攝影是件很快樂的事情。深入到生活中去發現美、捕捉美、把這種美的瞬間用相機凝固下來,這是一種創作。創作過程和獲得創作的成果都是一種享受。閑暇時把滿意的作品翻出來看看,總能勾起美好的回憶,余味無窮。
攝影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攝影有益於加強自身素養,對子提高觀察事物的能力和思維的敏銳性,提高藝術鑒賞水平,乃至對於鍛煉意志、增強體魄,都很有作用。攝影還有利子交朋友,有利於文化交流。出訪歸來,及時把拍的照片或者刊登照片的報刊寄給邀請方,人家感到你很尊重他們。2004年冬我把海外兒童攝影集送給了刊有該國照片的31個國家的駐華大使,他們有的打電話,有的寫信,表示稱贊,認為我做了一件促進中國同各國人民友誼的事情。2003年印度駐華大使梅農先生看到我訪印所拍的照片,非常喜歡,主動提出幫助辦攝影展、出版攝影集並作序。印度外交部長亞斯旺特·辛哈收到畫冊后來信稱“這部攝影集將會使中國人民對印度有進一步的了解”。2004年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問中國,在一次招待會上對我說,他看到了這本攝影集,並稱贊我“做了∼件對於促進印中友誼很有意義的事情”。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翻開這一幅幅照片,一個個人物,一處處風景,一段段回憶涌上心頭,上面凝固了多少難忘的瞬間啊!要說我的攝影水平有多高,這肯定是過譽。2002年在天津第一次舉辦攝影展時,我說我不是攝影家,只是一名攝影愛好者,是出於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感,出於辦好報紙的需要,才拿起照相機的。原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邵華同志生前曾為我海外婦女攝影集作序,題目是《責任·興趣·責任》,這很好地概括了我的攝影歷程。
(2013年5月1日)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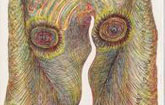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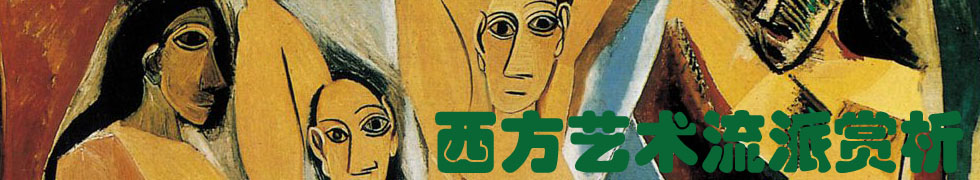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