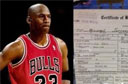鏡頭后面的思考
——讀《海外印象·邵華澤攝影選》
范敬宜
相機是機械的,鏡頭卻是通靈的。
相機是沉默的,鏡頭卻是傳神的。
手持相機的攝影者:無論性恪如何內向,就在快門的”喀嚓”一聲中,他的思考,他的觀察,都立刻通過鏡頭定格在底片。鏡頭是人們心靈的訴說者,什麼也瞞不過鏡頭。
看了邵華澤同志的海外攝影選——《海外印象》,我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了這幾行話。
華澤同志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老朋友。他重視攝影、愛好攝影,我是早就知道的。早在1990年,我還在《經濟日報》工作期間,拜讀了他在“銀川會議”上的著名講話。正是在這次全國報紙總編輯新聞攝影研討會上,華澤同志繼穆青同志提出“圖文並重,兩翼齊飛”的口號之后,又提出了“兩個提高,一個關鍵”的觀點。當時新聞攝影正在冷落時期,報刊上的新聞圖片數量很少,而且往往只是“豆腐塊”和“火柴盒”。穆青和華澤兩位新聞界權威人士的見解,在新聞攝影界乃至整個新聞界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熱烈響應。我也是其中之一,並且率先在《經濟日報》上進行試驗。不過,當時隻認為華澤同志的講話,是作為報界資深領導人對新聞攝影的一種倡導,並不知道他本人就是攝影愛好者。
知道華澤同志愛好攝影,是我1993年到人民日報工作以后。當時我發現他出國訪問或參加一些社會活動,經常帶著照相機,也偶然見到他在報刊發表的一些攝影作品。這在當時領導干部中是比較少見的。但是我也只是把這看作是他的一種業余興趣,還不能和他書法藝術的造詣相提並論。
這次看了他的《海外印象》,我才發現自己判斷的“失誤”。 ”失誤”的主要原因在於過去沒有仔細傾聽他鏡頭的訴說:沒有去發現他在鏡頭后的思考。他的攝影作品和他為人、為文的作風一樣,平實、沉穩、冷峻、有點嚴肅。相對於一些著名的攝影家,他沒有刻意追求奇崛的角度、新奇的構圖、特殊的技巧。他拍攝的各國風光、人物,表面看來,似乎與普通旅游者拍攝的沒有太大差別,很平常,很熟悉。但是當你靜下心來,細心地“讀”它,就會發現幾乎每一幅圖像后面,以及那些頗為抒情的文字說明,都蘊含著他深沉厚重的思考——歷史的、哲學的、文化的、人生的思考,耐人咀嚼,耐人尋味。隨便舉幾個例子:
第12頁《夕陽中的笛聲》:一座印度的石雕像。它要表現的是: “千百年來,他一直在吹奏。這笛聲穿越了歷史,定格成了永恆。”
第27頁《掙扎》:一座耶路撒冷現代派的藝術造型。作者要告訴人們的是:這座歷史上曾經 50次被圍困,36次被征服,18次被夷為平地的城市,被束縛的人們在掙扎,在呼喊,在抗爭……
第56頁《古來征戰幾人回》:盧森堡的美軍公墓。高入雲天的杉樹林,襯托著密集的白色十字架, 5076名戰死在沙場的美軍官兵長眠在這裡……
第68頁《清晨靜十肖’哨》:意大利佛羅倫薩的黎明,長街空無一人,這座文藝復興的傳統和藝術的寶庫,似乎還在文藝復興時代裡沉睡……
第74頁《衛城的神像》:雅典,千百年來,女神在這裡默默地佇立著,支撐者,守護著,一直到化為石雕……
第75頁《參天大樹》:排排高高的大樹,如擎天之柱,是它們為人類撐起了一片碧藍的天空。
第98頁《老人、孩子與海》:在海邊的沙灘上,一位滿頭銀發上身裸露的老人匍匐在地,和面前三四歲的愛孫對話。說明是:“富有哲學意味的圖景,使人聯想到時空的變遷,歲月的綿延,生命的無限……”
多麼精彩!不用摘引更多的例子,讀者就可以想象到,作者在捕捉著或動態或靜態場景的瞬間,頭腦裡的思維正在與歷史、哲學、文化、人生對接,思接萬千,神游八荒,於是,他心中歷史、哲學、文化、人生的積澱與相機的快門一起閃光。我想,華澤同志攝影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鏡頭后面的思考。
這一點,也許與他的理論修養和書法修養有關。他的理論修養是眾所周知的,這裡且不多說。單說他的書法。中國書畫藝術審美標准最注重的是一個“品”字。“所貴者品,所要者魂”,技法、技巧都是第二位的。“品”是一個人綜合修養的集中反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積累起來的。華澤同志從原來與攝影無緣到今天對攝影卓有成就,我想不能簡單地用“勤學苦練”來解釋,而應該從他多方面的修養中去尋找答案。這一點,特別值得年輕一代攝影工作者深思。
最近,科學大師錢學森同志再一次強調: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藝術修養。對於與藝術似乎“隔行”的科技工作尚且如此,那麼對於與藝術有著直接“血緣”關系的攝影,當然是“尤其”如此。“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宋代大詩人陸游,曾經對喜愛寫詩的侄兒作過這樣的告誡。什麼是“詩外”?我想應該是指各類學養和人生經歷以及由此升華的思考和感悟。——這也是我讀了《海外印象》之后的一點思考和感晤,不知華澤同志以為然否?
2005年8月9日夜
(作者時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原人民日報總編輯)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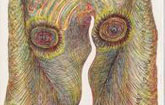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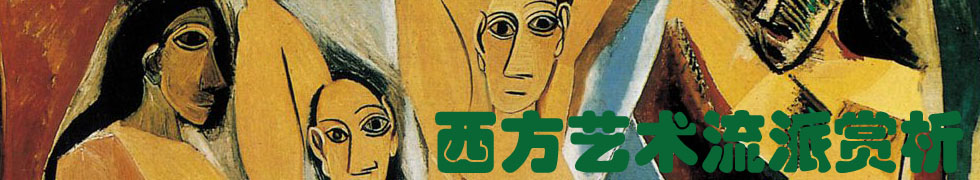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