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的關懷與現實悲憫溢出畫框
在這近百年的發展中,俄國油畫經歷著內部突破以及外部擠壓的雙重影響,一直發生著微妙的變化,然而一種對於人和人的價值的充分肯定卻始終流淌在藝術的血脈中。在畫展中最多的人物畫中,充滿了對人性的逼視、對人的關懷以及對苦難的悲憫。阿爾希波夫筆下的農婦,面頰如暢飲過伏特加般緋紅,衣裙濃艷,配上憨厚的笑容,一種舒心混雜著鄉愁扑面而來;普拉斯托夫將哺乳的母親與孩子置於青草與溫暖的陽光下,身后的狼狗機警地守護著主人,誰都無法拒絕這種慵懶而溫柔的善意;舍萬德洛諾娃筆下圖書館中小讀者,歪著腦袋張望圖書架,窗外是矮矮的白雪,知識與人性自成一個溫馨的氛圍,隔絕外部的嚴寒。
即便是在呈現風景與景物等客觀物象時,這些畫家力圖表現的依舊是人的情感和審美感受。畫家尤恩在8月,抓住了傍晚射入林中小木屋的最后一縷陽光,一種稍縱即逝的美麗哀傷讓人惆悵;而在康恰洛夫斯基筆下,冬日狩獵來的野味與蔬果靜物,則折射出人們在勞作與生活中必須面對的焦慮與欣喜。最是鄉愁斷人腸,從畫家眼中的故鄉,我們看到俄國的繪畫與文學精神氣質的一脈相承,色塊與光感的運用體現出俄羅斯藝術的浪漫性和烏托邦色彩。
對中國觀展者而言,特列展也是一個安放“俄羅斯情結”的地方,20世紀50年代以來,俄羅斯文藝曾在我國廣泛傳播。而其中曾在中國開辦油畫訓練班的馬克西莫夫不得不提。在兩年多的中國教學期間,他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油畫家。這一次,馬克西莫夫的作品《小拖拉機手薩沙》也來到了展覽現場,這幅描繪勞動青年質朴形象的畫作,帶著一股向上而又真實的生命力,也正是這幅作品奠定了馬克西莫夫的藝壇地位。
對歷史與繪畫發的“雙維度”反思
除了令人沉醉的俄國風土人情,在展覽中,幾組展現對戰爭反思的畫作十分矚目。在波普科夫的《回憶,寡婦們》中,五位穿著絳紅色裙裝的老年女性面容惆悵失落,她們或眺望窗外,或撫膝而坐,或垂手而立,逼仄的室內環境昏暗壓抑,戰爭對婦女的精神傷害揪動人心。在畫展轉角處,一幅展現西班牙斗牛運動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梅爾尼科夫以略帶仰視的角度繪出一位成功殺死公牛的斗牛士,鮮紅的背景、公牛絕望的眼神勾出觀看者復雜的心緒。頗有意味的是,雖然斗牛士擺出了勝利的姿勢,但是在他的眼神中卻讀不到絲毫的喜悅。藝術家全山石介紹說,這其實是一組“三聯畫”作品中的一幅,另外兩幅的主題分別是遭到轟炸的教堂以及被納粹殺害的詩人加西亞·洛爾卡,在西班牙風情背后,寄托了畫家的反戰情緒。
“反思”亦是始終貫穿特列展的無形主題。在這些跨度近百年的繪畫作品中,俄國繪畫在“藝術表現與藝術內容”間的搖擺與掙扎隨處可見。展覽中藝術家康恰洛夫斯基的兩幅作品為這種藝術的“反思”提供了一個濃縮案例。在作品《小提琴手》中,康恰洛夫斯基採用了十分先鋒的手法,粗獷的線條結構像是對過往寫實主義油畫語言的一種強烈反叛,新穎的藝術手法更加注重畫面的質感,追求近乎幾何形態的立體感,而對作品的內容和主題並不特別關注。而之后他繪制的另一幅女兒的肖像則在藝術表現和內容主題中探索一種平衡,畫面中,色塊的運用依舊帶有粗?的先鋒色彩,而女孩彎腰穿鞋的動作,以及臉部的表情卻用寫實的手發展現得分外生動。藝術家個人與整個俄國繪畫都在反思中一路向前。在畫展的尾聲處,一幅描繪女子伏在窗前,眺望佛羅倫薩風景的作品分外動人。窗外跨越百年的佛羅倫薩建筑沐浴在傍晚的夕照中,柔和的色調像是對過往繁華的無限追思,屋外與屋內兩個通過窗戶連接的空間似乎在進行一場持久的隔空對弈。這幅畫仿佛是一種俄羅斯藝術家在百年歷史中不斷吸收著歐洲藝術傳統養分,同時又孜孜不倦尋找著自己民族語言的生動寫照。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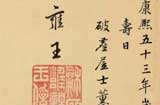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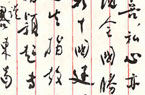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