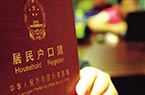《逃難》3
我常常在思索,如真的存在靈魂,那當年的受難者會是怎樣地告訴今天的人們,他們身心的創傷?!我曾訪問遇難幸存者常志強,這位親眼看著自己母親被日本人刺死,親弟弟淚水、鼻涕與母親血水、奶水凍凝一起。時光已逝去七十個年頭,可這位八十歲老人仍然聲淚俱下,噩夢未醒。我有一個強烈的欲望,要復活那些受屈的亡靈。紀念館內那些頭蓋骨上的刀痕,那被砍斷的頸骨,那兒童骨頭上的槍眼……,那在光天化日下被剝光衣服的婦女的哀哭,身上還投射著日本軍帽的影子﹔那被反綁著雙手、跪著,剎那間,身首已分的俘虜﹔那被集體活埋的婦女、青年,在日本兵鐵鍬覆土的間隙,昂首不屈的男子……,在我不平靜的創作遭遇裡,無數徹夜難眠的夜。我甚至走在南京舊城區,也不自覺聽到轟鳴與刺殺的哀鳴!試想,紀念館的大門就是攻陷的中華門,如果每個進館內的人,相遇了這批由城內而逃出的亡靈,這當是歷史與現實,幻覺與真實,災難與幸福,戰爭與和平的相遇。我將這10組21個人物置於水中,與行人及建筑若即若離,營造時空的對語。尺度近乎真人,從感覺世界裡與觀眾互為參與。他們中有:婦女、兒童、老人,有知識份子、普通市民、僧人等。最為讓人悲憐的是常志強的母親將最后一滴奶喂給嬰兒﹔最為勾起回憶的是以兒子攙扶八十歲母親逃難的歷史照片為原型的創作﹔最為令人驚恐的是那被日軍強奸的少女為一洗清白而投井自盡﹔最為引人沉思的是僧人為死者抹下含冤的雙目……。這二十一個人物,虛實錯落形成悲烈的曲線。雕像為銀灰的色質。迥然於見慣了的青銅、古銅色,它是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時空冤魂,是彌天恐怖中逃出的難者。
這組雕塑我做得極為淋漓酣暢,它可以憑籍體態、動態的極端夸張而達到 極強的表現意念,可以將老人那顫抖的筋脈刻劃得入微而生動。也可以從他們凸起的雙眼揭示那驚恐與仇恨!在這裡,精妙的寫實和概括的寫意,准確的塑造和變形的夸張,結構和比例的所有標准隻服從於“表現”!這種表現是緣自於魂的底層又深入到骨子裡的大表現!由此,我真正體會到結構與靈魂的對應﹔表現與精神的對應﹔夸張與情緒的對應。這組《逃難》原本設計是由數十組逃難者組成的人流,以造成氣勢,好象一下子從城中涌出來。但方案被評審專家給否定了。他們建議以少勝多,以每組獨立的雕塑而概全貌。這是虛中的實象,是中國戲劇舞台的表現智慧。但落成后,也有另一批專家認為該用原先方案,以多取勢,以多求逃難人群的豐富性。
歷史上,無數藝術作品的個案証明,有些隻有唯一的設計,往往妙不可言。有些可有幾種設計方案皆能採用。一旦某種方案實施了,時間久了,也便成了心理上的唯一。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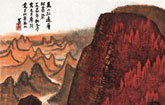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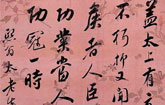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