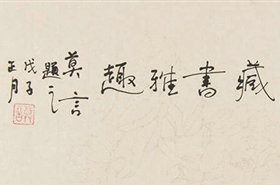川江號子來到北京
在北京八達嶺長城、國家體育館鳥巢、798藝術中心陸續出現一隊唱著號子的纖夫,引來大批游客和市民圍觀,甚至引起游客現場即興模仿。
這些唱號子的纖夫為“印象”系列實景山水演出《印象·武隆》的演員,他們專程從重慶武隆來到北京,意在將川渝大地的號子唱響中國,呼吁人們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父輩精神,傳承民族文化。接下來,他們將走進上海、廣州、西安、成都、香港、澳門等地,明年還將走出國門到歐美展演。
《印象·武隆》是“印象系”第七部實景演出作品,由王潮歌、樊躍擔任總導演,張藝謀任藝術顧問。它以瀕臨消失的川江號子為演出精髓,以武隆自然地貌和靈秀山水為舞台,是“印象系”的首個實景歌會。2012年4月23日公演以來,它已演出幾百場,觀眾逾50萬人次,票房收入達5000萬元。
川江號子該怎麼唱
該劇的主題——川江號子曾經是船工們拉纖時為了統一節奏和緩解情緒的歌唱形式。當機動船代替人力船后,纖道消失了,巴蜀大地父輩們的勞作景象也消失了,川江號子已成千古絕唱。根據《印象·武隆》主創團隊的前期考察和統計,當年的纖夫許多已經辭世,如今仍然在世的烏江纖夫有11人,川江段纖夫有8人,會唱川江號子的僅余20人。
川江號子到底該怎麼唱,一千個人有一千種說法。樊躍回憶說,創作組初到重慶武隆,他們想把號子收集整理一下,先是求助於當地的文化部門,后來又走訪了當地音協,卻都找不到號子的記錄。
后來他們發現,號子是一種勞動方式,是勞動的一部分,是纖夫帶有智慧和技巧的生活方式,纖夫所有的氣息、調整的步伐,都是從生活中來的。
“號子不是歌,川渝人說話拉長了就是這個味兒,跟川腔是一個意思,號子寄托著纖夫朴素的理想——想生個孩子,想回家了,想吃什麼,想翻過這座山,想喝頓酒,完全是即興的東西,所以無法記錄。”樊躍說,我們今天把號子看做歌,或者把它當做藝術,看做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這個使用本身是帶著思考的,你隻要把它拿過來,和生活一對,就會發現《印象·武隆》裡的號子已經很藝術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失傳的不僅是號子,失傳的是生活。當年的生活方式和現在的生活方式反差巨大。纖夫們很難想象現在電視、冰箱、飛機以及所有現代化的設備能那麼普及,然而讓人特別悲哀的是,在物質極度豐富的當下,我們這代人一點兒幸福感都沒有。反而是那一代人,他們所有朴素的理想,以及奔理想而去的那股勁頭,讓現代人汗顏。“印象是詩化的結果,父輩所有的記憶,插上了印象詩化、理想的翅膀,以號子的形式表達出來,頓時鮮活了。每個人都有心中的哈姆雷特,每個人對心中號子的記憶都是不一樣的。”
人力開山造劇場
收集整理號子難,更難的是《印象·武隆》的創排。武隆雖然山清水秀,但要在當地的山水間開辟一席之地供演出用,同樣難於上青天。王潮歌回憶,雖然都是在大山之間演出,不同於在福建武夷山演出的《印象·大紅袍》時品茶溫書的安然狀態,《印象·武隆》給人更多的是絕壁求生的震撼。
“在巴蜀大山裡,看到的是巴掌大的一塊兒庄稼地,他們努力種了一些土豆和苞谷。武隆的山不同於福建的山,它有一種絕壁的感覺。我們開辟武隆劇場的時候,它是一個峽谷,不可能有機械進入。之前我跟樊躍第一次踩點,山上沒有路,專門找了個人在前面一把鐵鍬一把鋤頭地開道,我倆手拉著手,互相攙扶,一步一挪地走下山。當時后面有一幫村民好奇尾隨,但他們沒有下山,就在半山腰的位置看。”王潮歌說,她和樊躍突發奇想,能不能讓村民在上面喊兩嗓子,聽聽那個地方的聲場,於是他們給上面的人打了個電話,問他們可不可以,沒想到,那些村民十分熱情和配合,一直不停地喊叫,從那一天起,他們就被這些老百姓的朴實震撼到了。
劇場的搭建也是幕天席地,開劇場要砸通隧道,而那個險峻的山谷沒有任何車輛和大型機械可以進入,全部靠當地婦女用系在頭上的背簍和筐運送石塊和土方。后來牽來了騾子和驢,又慢慢打樁,那些很粗的鋼筋全是人力扛進去的,一串人前胸貼后背抬一根鋼筋,一寸一寸挪進山裡。
在建造劇場人力搬運的過程中,勞動號子已經出來了。王潮歌和樊躍住在山上,過了幾個月極度艱苦的日子,沒有廁所,不敢多喝水,不敢多吃東西。當時每個人備了兩雙鞋,裡邊穿一雙鞋,外面再穿一雙到膝蓋的水靴,地上的泥漿一直沒到膝蓋,爬一段山就要磕泥,否則泥坨越粘越大,走不動路。演員們也不辭辛苦,滿是泥水的排練場地,說趴下就趴下,臉上沾滿泥湯,面目難辨。
號子聲中有他們的勞動觀
談及《印象·武隆》創排初期的走訪,王潮歌忍不住熱淚盈眶,“如果你想知道真正的號子,已經晚了,很多纖夫死了就失傳了。他們打夯、種地、抬石塊、抬滑竿、做棒棒,互相之間的交流都是號子。我坐過一次滑竿,抬滑竿喊的口號就是號子,號子協調他們的步伐和手臂用力的方向。我對那種肩膀上抬自己生活、抬一家人生活的朴實勞動感到震撼。”
最令王潮歌動容的是巴蜀人民在勞動觀念上與北京人的鮮明反差。“我是北京人,在北京城裡遇到最多的是‘爺’,感覺到最多的是‘爺不伺候’,甭管給多少錢,干不干得憑‘爺’的心情。”但是在川渝人的概念裡,有一線可以活下來的生機和路數,他們都會拼命抓住。王潮歌說,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還有女纖夫,他們走訪到的那個女艄公頭已經70多歲了,她當年拉纖的照片居然也和男纖夫一樣赤裸上身,甚至連兜襠布都沒有。女艄公頭以前不是纖夫,但她丈夫是,老頭死了,她順理成章地接班。
採訪那個女艄公頭的時候,王潮歌懷著一種悲愴的心情,原以為她有多麼悲傷、多麼苦難,這種想法隨即被女艄公頭江湖氣十足的豪爽大笑沖銷。“川渝的女人,太值得敬佩了,要不怎麼雇保姆都願意要四川的。她們自尊心的底限在於用自己的雙手掙錢吃飯,從不會因為貧困而覺得低人一等。這一點我是相當欽佩的。這對像我這樣的北京人,對現在的城裡人,是另一種洗滌。”記者 胡 芳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