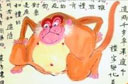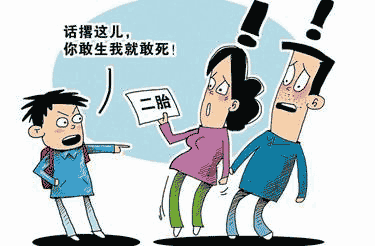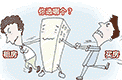編者按:
《時代氣度——滑田友雕塑藝術紀念暨捐贈展》於2008年3月27日至4月5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3月28日在京部分雕塑家、理論家於中國美術館七樓會議廳舉行了學術研討會。會議由學術一部主任陳履生研究員主持,范迪安、錢紹武、盛揚、王鏞、尚輝、隋建國、鄒躍進、鄒文、李永林、斐建國、岳潔瓊、呂品昌、鄭濤、王少軍、曹春生及滑田友先生家屬出席並做了發言。
現選擇部分發言(根據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閱),刊登於下。
范迪安:(中國美術館館長)
滑田友藝術展和捐贈作品展開幕,在雕塑界引起了十分強烈的反響。
滑田友藝術這是距離幾年前展覽又一次比較集中,而且特別是比較單純的學術層面的展示。
在21世紀的今天來看待滑田友的藝術,特別是他的學術特征、學術貢獻,聯系我們現在美術發展、雕塑發展新的形勢,形成了許多新的認識。借這個機會能夠對滑田友藝術做出再認識,即可能提供很多新的歷史資料,又更多能夠闡發滑田友藝術在20世紀中國雕塑的現代歷程中的學術地位,使之能夠更加清晰、更加准確。
錢紹武:(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我覺得滑先生的雕塑,和我后來到蘇聯學習的是有很大區別。它的特點在什麼地方?或者法國學派有什麼特點?歐洲學派也有兩派,一種是阿波羅式、一種是酒神式的,滑先生的藝術既有阿波羅式又有酒神式的特色,傾向於酒神式的多一點,直截了當的、完全情感出發的多一點。所謂阿波羅式是從理性分析客觀世界、客觀現實,歸納的很合乎規律性的一種體察。酒神式的就是完全情感的。滑先生教我們的時候,我記得我們做人像,總是不像,做得不准確。滑田友先生說。“你們首先看看像香蕉還是像蘋果。”這一句話就使我感覺和學做雕塑需要用工把量,對照模特量,用人體復制的那種方法不一樣。
滑田友先生的作品,有一批到保加利亞去做的頭像,造型特色非常明顯。由於時間原因他得做很多頭像,做得很快,所以就沒有辦法那麼講究了。和歐洲的嚴格解剖知識的那種相比,他的人手點是不一樣的,所以他的造型特別明顯,特別鮮明,你說准確的話,不一定,不像嚴格的解剖結構,但是非常有特色,而且非常有意思。
從“香蕉”和“蘋果”的看法裡,我覺得滑先生是把中國的傳統教學方法和歐洲雕塑方法結合起來,而且首先是一種最自然地,藝術地來了解世界、觀察世界,也就是歐洲的酒神式方法,這個體系就和歐洲或者是俄羅斯學派的體系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效果也有非常明顯的區別。
滑田友先生總是用簡單到極點的語言和簡單到極點的例子來讓你了解最深刻的道理。這一輩子,入門就是這幾條,但是,最后也就是這幾條的發展。這和李政道先生談到科學觀都是這樣的。科學一開始就是一些簡單的規律,但到最后的科學發現,也就是這個規律再深入探討、深入研究所得到的規律。藝術也是這樣的,一開始看到“香蕉” “蘋果”的一個最基本特點,從這個基本的感受出發,最后發展到最高的成就。
我覺得到一定程度,解剖這些東西都是對雕刻家觀察世界、掌握世界都有好處的,但是如果僅僅被這些規律束縛在裡面,那就不是藝術家,就會有很多藝術的因素受到忽視,不能得到充分發揮。我自己就有這樣的感覺,我在做《李大釗像》的時候,假如我還是按照蘇聯學的那一套走,那肯定不可能有現在的效果,所以我要非常痛苦地把這套解剖的東西全部去掉。就是看是“蘋果”還是“香蕉”,而不是解剖,不是照片本身和人本身長得怎樣,而是你自己的創作意圖和理解感受成為一個最基本的形象,也就是中國畫所說“神遇而跡化”,山川是我,我是山川。這時你會體會到這既是你自己情感的體現,又是客觀現象最基本特色的體現,把對象特點和自己的理解完全結合在一起,是“香蕉”還是“蘋果”,這樣來造型,而不是量來量去,校來校去,那樣你怎麼樣也做不出來的。
其次,滑田友先生對形體,又是很傳統,把歐洲傳統學的也非常好,結合了很多中國的方法在裡面。
第三點,我們做雕塑,大體有了,然后必須要有細節。沒有細節就不成為藝術品,沒有細節,往往生動性就不夠,豐富性就不夠,具體性就不夠。所以必須要有細節。往往細節和整體統一就是一個不得了的大問題,這就是藝術家和非藝術家的區別,就是照相和藝術的區別。要懂得如何把豐富的東西變成一個整體,整體中間又有無限的豐富。
滑田友先生就做了一個比喻,說:首先你看它是一座山,你再走進去看,山上還有路,再走進去看,路裡還有很多石子,很多石塊,但是,石塊再豐富,再千奇百怪,不能把路的感覺破壞了,遠遠看去還是一條曲曲彎彎的路。所以,石塊的豐富,石塊的具體化,石塊的各種特色不能破壞路的整個特色,路在山裡繞來繞去,路再大,隻能豐富山,而不能讓山的特點沒有了。所以,看到石頭要在路的整個概括中間,看到路要在山的整個概括中間,要豐富山的大形,要豐富山的整體感,不能破壞山的整體感,可以使它更具體、更生動、更豐富。假如路的復雜,破壞山的大形,最后不能把整個山的豐富性突出,這就不行了。滑田友先生就把先看到大山,然后再看到它的路,再看到路面的石頭,這三者的關系如何來統一,用簡單到極點的例子。隻有這樣看法,這樣來統帥,這樣來看整體和局部的關系,就能夠解決得非常透徹。
這一點在滑田友先生捐贈的作品裡,每一個雕塑都可以看到。這好像是在雕塑中間的一個具體問題,但實際上牽扯到雕塑創作中間的一個什麼階段、什麼情況下部會碰到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觀察世界,如何概括世界,如何在單純的、強烈的總體感覺中間又有無限豐富的細節,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三點,滑田友先生都是用最簡單的方法,最容易接受的方法,最是引導學生可以理解的方法,而得到了一個培養學生最根本的藝術感覺,引申到如何藝術的概括世界,如何藝術的變成雕塑的一個整體,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的一套經驗,或者說一套基本方法,一套基本原則。
滑田友先生說:“你們做人體,就是像串冰糖葫蘆。”為什麼像串冰糖葫蘆呢?就是任何的東西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形,上面又有附著的形體,所謂的每一個山裡紅都是七高八低的,葫蘆都有方有圓,都有特色的,不是機器做出來的,它是自然形態的,每一個都有它的特點,但是串在一起的,裡面隻有一根棍,自始至終的、最中間的核心它是一致的,它是統一的,它是自上到下貫穿的,它不能是歪歪曲曲的,中間有一根最基本的形體,然后有冰糖葫蘆覆在它上面,裡面再凹、再深不能連棍都沒有了,最后都是有聯系的。所以,這就是人體的各種肌肉起伏和各種變化,用冰糖葫蘆解說也就非常有意思,特別有米開朗基羅的一個《掙扎的奴隸》,兩個胳膊往后面,身體擰過來,這個胳膊就是滑先生所說的串冰糖葫蘆,那裡面骨骼的結實、統一、堅強有力,上面的肌肉變化非常豐富,都不破壞基本的線,也不破壞串冰糖葫蘆的棍,這對人體的豐富和基本形不能破壞,用“串冰糖葫蘆”說就非常好了。
滑田友先生又說,“你們要看一個形體,你們要像編柳條筐子似的。”為什麼編柳條筐子那麼重要呢?大家看看我的拳頭,這個拳頭是方方的基本形體,但是,上面有這些骨頭、有這些骨頭(舉手示意),中間最主要是,從這個低的地方到這個低的地方都是串得過去的,都是一條,假如這中間凹得太深就穿不過去了,就完了,這個筐子就不成圓的了,就成了七歪八扭的東西。所以,筐子要有個基本的圓形,它有一個柳條編織基本的串得過去的感覺,這是低點。編筐子有凹下去的地方,有高起來的地方,高點呢,高點又是互相聯系的,都是不能破壞這個筐子,都是豐富這個筐子,最后把筐子的形狀顯示得很確切。“編柳條筐子”又是一個形體中間所有的高低起伏變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用這個比喻來塑造中間的互相聯系,本身又是很基礎的基本型的完整,又有各種各樣的關系。
這幾種都是滑田友先生他自己創造的名詞,好像很隨意,但是,又非常生動、非常朴實、非常民間的,沒有一點現在有些人所說的那種,老實說我都看不懂的,說是有物理和化學的東西,但根本看不懂。滑田友先生絕不用這些,但是又是非常生動、非常確切,而且容易理解,也就說明真正的大家必然是深入淺出的,應該是言之有物,很深的東西,他說得非常單純,非常簡單。而現在有些人的文章把非常簡單的事情說得誰都不懂,這兩種技巧是不一樣的。滑田友先生是真正的大家,總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非常引人入勝,而且誰都可以理解。
他又把中國的“六法”歸納起來,依我看“六法”是不是滑田友先生的解說?也不一定,也有符合一般國畫能夠理解的,也有滑田友先生提了以后,按滑先生這樣的理解才能體會到滑先生所指的原意是什麼,當然也概括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通過用“六法”的說法,來闡述他畢生的雕塑創作中間、在雕塑教學裡面所體會出的規律性的學問。
滑田友先生為人也好,做學問也好,他的特點就是非常簡朴、實在,一針見血,絕不弄虛作假,絕不是把簡單的東西復雜化,把最復雜的東西說得人人都懂,這才是真正大家的創作心得、體會,他對世界的貢獻,人人都能接受,而且大家都能提高。
盛揚:(中國美術家協會雕塑藝術委員會主任)
滑田友先生作為中國現代雕塑和現代雕塑教育開拓者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它,珍視它,發掘它,弘揚它。滑田友先生繼承了我們中國藝術家的共有的品質,就是什麼東西學過來以后都是和我們中國本身的東西相結合,把它融化,從而產生新的東西。滑田友到法國學習,從他學習那一天,一方面虛心的向西方學習,一方面不斷探索怎麼和我們民族的東西相結合,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這個過程貫穿他一生。對整個中國來講,把外來的東西變成我們自己的,也不是我們一個人完成,不是一個時代完成的,是要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探討,而滑田友先生在他的一生中做出非常可貴的貢獻,這是他非常可貴的精神。你現在看到的他的東西,不完全是西方的東西,又不完全是我們古代的,你再看,還是感覺有中國的味道,又有世界的東西,而且有他個人的風格。
我跟滑田友先生在一起,生活很多年,我曾經問過他,你對雕塑到底是怎麼理解?怎麼做的?他講了很多例子,很生動。
比如他說:你看東西(對象)首先是感覺大形是什麼,是圓、是長、是方、是蘋果還是香蕉。他跟我講的時候,他說這其實是一個‘情感,他說,有人把美院雕塑教學認為是學院派的,開始學的時候模特什麼樣,你就照著做什麼樣,你現在不要考慮,把模特做出來,你學到基本功了,然后再發揮、再創造,其實我們這些老先生,特別是滑先生根本不是這樣的。他說,一開始做習作的時候,你就把它當成藝術品來做,帶著情感來做,但是你現在是在磨煉自己的情感和技術,並不是說,現在擺在這裡的模特是讓你完全理性的解決長短、肌肉、骨骼的解剖,他說你還是要憑你的感覺,帶有情感來做,帶有創作意圖來做,但是在磨練中間,必須尊重客觀對象,他強調的是這個東西。我們開始做的時候先做整體,有時候理解不夠做不下去。他就講,你可以再做一點局部,局部現在做不是目的,是調你的情感,因為局部一做很生動,情感就來了,之后你回過頭來,不惜犧牲你的局部,繼續求雕塑整體的完整。所以,美院雕塑的教學體系,我覺得是自從中國有現代雕塑教學體系以來(過去都是師傅帶徒弟),也有幾十年的歷史,這幾十年的歷史,特別是在中央美院形成了既有國外的影響,又有我們本土的因素,再加上我們老前輩的精心探索形成了在中國比較好的、比較完備的、比較穩定的體系。昨天我很興奮的聽到靳尚誼院長,作為官方的姿態講了, “我們中央美院形成了完整一點的、先進一點的相對穩定的……”我覺得這就很不容易,這份遺產我們確實不要全否了,人類的文化是要有繼承的,是要在巨人的肩膀上走,不可能完全絕對,完全斷裂,我覺得美院教學體系比如油畫、國畫都應該這樣的,我們美院幾十年形成的教學體系,不能說是最完備、最先進,但確實是在中國一百年來現代雕塑發展史上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有待於補充、發揮,有待於把過時的拋棄,接受現代的東西,但是是要在我們的基礎上繼續完成,千萬不要斷裂。我覺得這是我們對老先生、對滑田友先生反過頭來再研究很有價值的地方。
這次展覽裡面我也感覺到,它有一定的社會意義。我覺得雕塑再怎麼發展,它總有雕塑本身的母語,雕塑在發展,語言在豐富,應該吸納新的語匯、新的語言,但是雕塑總有它自己的母語,這就是雕塑最本質的東西,如果把雕塑的母語都忘記了,而把聽來的局部的某一個方面的、某一個性能的語言來代替了雕塑的母語,雕塑就會悲哀,就會走向另外的路子。
我覺得我們當代的雕塑家對我們雕塑的母語研究太少了,而用一些直接、局部的某種性能的語言作為炫耀、作為新、作為旗幟、作為興奮劑,來博取一種喝彩、博取一種榮譽,我不排除這些東西,但要和母語相結合,比如說放氣球,國慶節和五一節都放氣球,很美,很好,但是,你要把氣球挂出來,說這就是雕塑,我並不是說不好,但是說成雕塑,我覺得雕塑本質的東西就沒有了,我並不排斥新潮,你在節日裡面氣球比你雕塑還能產生它的作用,就像噴泉,有了噴泉就好看得多,但是我不把它看成是雕塑,因為雕塑有它本質的特征。
我們學習滑田友先生的作品,要對我們的母語有分析、有研究以發揮我們語言的豐富性。
滑田友先生很注重傳統,但他絕不保守,他的代表性的作品《轟炸》,不論從骨子裡面到外面的東西都是中國的,但是,你又不能說,他照抄中國傳統,因為他整個的氣質就是中國的氣質,但是他的雕塑語言又有中國的特點,《轟炸》婦女的棉襖隻有中國蘇北老鄉才有的,那種臉的造型,那種動態,不是歐洲人的,現在我們很多做的人像都是歐洲人,穿上中國的服裝,或者是傳統線條。我覺得,我們要把外來的東西和我們本民族的東西結合,但絕不是完全照抄外國的,也不完全照搬傳統,就是要怎麼推陳出新。
我曾經問過滑先生,你對雕塑怎麼理解?在50年代的時候,我們雕塑系有一個很好的學術活動,王臨乙先生著重研究秦漢的雕塑,竹韶先生著重研究北魏的雕塑,滑田友先生專門研究唐代的雕塑,傅天仇專門研究宋代雕塑,我們跟他們搖旗吶喊,一起去學。我曾經問滑田友先生你怎麼看待唐代的雕塑,怎麼研究傳統的東西,他講了很多,也有很多的心得。
他說雕塑,歐洲講究貫穿,滑先生非常講究貫穿,一種潛在的力量就是貫穿。也就是 “串糖葫蘆”。我的理解,他的主導是說:人本身有結構上的貫穿,就是骨骼、建筑感,一種內在必然規律的貫穿。但是,成為藝術,成為特定動作的時候,還有偶然的貫穿,必然性的貫穿是本身的結構,偶然性的貫穿是具體的構圖和所表達的情緒,這裡面的貫穿可以把作品完全組合在一起。比如說大樹,為什麼感覺參天大樹那麼好看,那麼雄偉,你要研究他的枝干、葉子是怎麼互相串聯起來的,有很多東西是樹本身長成的,有的很多東西是風搖擺造成的,你把樹本身的貫穿和風搖擺的貫穿,這種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貫穿結合起來那就是神秘的,就是高明。如果隻有必然性的貫穿是死板的,如果隻有偶然性的貫穿是虛空的。唐代的東西,我們中國的東西就是這樣的。
中國唐代的東西有一個特點,我們把它吸收過來。一個整體的東西是自然的,你把他不和諧的低點填平,不和諧的高點壓低,然后形成一個整體。而這種整體既有豐富性又有和諧性,這是唐代的雕塑的特點。我就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他學習的傳統不是照貓畫虎,他是用雅塑的語言,所以他的東西做得很不一般,很有特點,你可感覺到有歐洲的優點,有中國的優點,還有個人的優點。
王鏞:(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滑田友的作品有美術史的價值,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對中國現代雕塑的發展,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的認識。看了這些作品和國外看到的現代的,包括羅丹也們這些大師的作品,應該說是在一個檔次上,從寫實的角度來訓:也是很杰出的。
滑田友的作品,把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寫實結合、綜合起來。看了滑田友先生自己寫的“六法”和雕塑關系的文章,他談到,剛到法國留學聽不懂法語,老師講課聽太懂,就知道要生動和有力,他自己就聯想到中國繪畫的“六法”,就想把這“六法”運用到雕塑裡面,第一條是氣韻,他理解就是貫氣,人物結構內在的聯系,法國的雕塑也是強調表現主義精神氣質的,這和中國的氣韻相通是一樣的,他從法國老師那裡得到最大的收獲是,雕塑要強周整體感。這個在以前的“六法”裡是沒有講的,他就把貫氣和整體感結合起來了,所以他的雕塑作品裡可以看到,確實是把中國的傳統東西和西方的東西結合起來了。
再有從這一點可以看到他對雕塑理論的思考,滑田友先生把“六法”運用於雕塑,自己解釋了“六法”,把自己所理解的“六法”和西方的雕塑理論結合起來,這種整合本身就是創造,就有理論價值,這個思路值得我們當代雕塑家繼續探索。
滑田友先生的雕塑作品有很強的現代性,為什麼他的《轟炸》會被巴黎的現代藝術博物館收藏,我考慮兩點,一點是現代性的方面,直接進入現實,反法西斯的,再一個,簡潔、朴素,而整體感又非常強,我理解的“現代性”是強調個性,他的個性很突出,這個個性一看就是東方人的,中國風格的,包括他的《農夫——少年中國》,既簡潔又整體感強,渾然一體,一直到《五四運動》的雕塑,強凋中國傳統的造型,我覺得這個也值得我們當代的中國雕塑家去學習,沿著他的路繼續探索。
尚輝:(《美術》雜志主編)
毫無疑問滑田友先生是20世紀、也是中國現代第一代雕塑家進行寫實雕塑本土化探索的杰出代表,也毫無疑問是現代中國雕塑教育的開創者和杰出代表。滑田友先生的雕塑是寫實的,他的雕塑毫無疑問是可以在世界美術史上、在中國的篇章上佔有很重要的一頁,所以這個問題讓我們如何看待滑田友先生雕塑本土性的價值,這是非常重要的。
設想滑田友在30年代出國時,他到法國看到歐洲雕塑的傳統是非常豐富的,有古希臘羅馬的雕塑,有羅丹的現代的雕塑,也包括馬約爾、德加、馬蒂斯的雕塑,在他的眼裡,歐洲雕塑的傳統從古典主義到現代主義等等很多的派別都在他的日艮裡呈現,作為第一代現代中國雕塑家,滑田友出國時‘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文化選擇,是他要學習哪一種雕塑流派風格的選擇和繼承。滑田友先生在出國之前雕刻的陳散原的像,可以體現他很高的天賦,他和徐悲鴻接觸比較多,是徐悲鴻把他帶到法國,顯然徐悲鴻的現實主義寫實繪畫對滑田友也是有影響的。
寫實,造型基礎的扎實,這是一種基本的方法和道路,但是,寫實,造型扎實並不等於藝術本身。能從基礎的造型裡,從很准確的解剖和造型功底裡能夠闡發出他對藝術的認識,他對人對事對情感的表達,這點是非常難得的。我覺得滑田友出生在蘇北,在出國之前有很強的雕塑的沿襲,特別是他在蘇州用直保聖寺對唐代雕塑的修復,無形中先天的第一口奶接受的是中國雕塑的傳統,所以他在法國學習的時候,在接受西方傳統寫實雕塑的同時,也融會了、滲入了中國雕塑的語言,今天來看他的雕塑很顯然有很強、很濃郁的本土化的特色。我概括:簡朴、簡練、簡潔,敦厚、朴厚、著厚、渾厚。
一般來說中國藝術、中國文化是意象性的,可以包括意象的形象性,不是鏡子式的、摹仿式的、意象式的筆法。藝術是自然的兒子,實際上中國的藝術本身就是主人,藝術是自然的父親,這是中國的認識方法,這是我們認識的意象的形象性。還有很多地認識,就是寫意性。滑田友先生,在本土化的探索中,更多強調意象形象性。滑田友先生把“六法論”繪畫的表現方法,中國文化對自然世界的認識方法轉化為他對雕塑形象的一種認識,在他同一代人,在第一代雕塑家中,認識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轟炸》《母愛》《農夫》表現者都是對形象的簡化寧拙勿巧,寧方勿圓,這是非常優秀的,非常出色,他的雕塑語言上,表面是粗糙的,表現了扎實的體量感、古朴的意趣,和雕塑語言都很有關系。
在展廳裡可以看到他對傳統的東西吸收了很多方面,他這種造型形象也接受了米勒簡化的形體的表達方法,他的《轟炸》那個衣服褶既有一定的裝飾性,也有一定的簡化性,他研究得非常透徹。“米點”可以說是中國山水的米點的方法,也可以說是接受了印象派的“點彩”的方法,用點的方法塑上去,更強凋了塑造感。他用刀的方法,用泥的方法,轉化為米點,所以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來是刀具還是手按上去的,他做了很多豐富的探索。
談到寫意性,滑先生的兩件作品,一個是《轟炸》,一個是《轟炸后》,他是用一種靜態的雕塑語言,他的靜態裡面有一種凝固的雕塑語言,他的那個作品並不大,《轟炸后》父親抱著孩子,你感覺裡面有千鈞之力。如何使用雕塑的語言,這裡面有對雕塑語言的轉化問題。
看了滑田友雕塑展,我感覺中國第二代、第三代雕塑家一直到今天的雕塑家,可以說在藝術觀念上、藝術趣味上、藝術個性上都有很強的追求和表現意識,但最缺少的是對中國古代雕塑傳統的繼承和研究,缺少對歐洲傳統、古典主義傳統的繼承和研究,我們缺的是對人體本身骨骼的理解,所以冰糖葫蘆串不起來,對人本身的理解上的欠缺,對人理解的表現上不能達到。
看了展覽以后,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我們當代的藝術家需要補課,看了雕塑和他的速寫是有一定的互補性的,他的雕塑是本土性中很嚴謹的,是寫實的,但是,他的速寫恰恰是很放鬆、很夸張,有很多的現代意味,研究一個人是有豐富性、兩面性的。不管怎麼說,中國美術館舉力、這樣的雕塑展覽,舉力、這樣的研討會對於我們現當代雕塑研究和收藏都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隋建國:(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
滑田友先生是雕塑家,也是系主任,他很善於自己琢磨事兒,琢磨雕塑的事兒,他有大篇的教學大綱,這其中《我對雕塑的基本看法》這篇文章和《我怎樣教雕塑實習》我沒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和大綱有關系,包括他對“六法”、“以中化西”的方法都是自己琢磨出來的,這其實是實踐者的思考,因為他親身做這個事情,他就琢磨,包括“蘋果與香蕉”、“山”或者是“串冰糖葫蘆”和“編筐”,都是一個實踐者總結的。可惜,由於解放后的歷次運動,各個系主任在討論教學的時候,總是要有一些新的精神,教學總要和新的精神結合,這其實是對基本的教學、學術研究都是有干擾的,使這些思考不能持續下去,或者說不能讓它變成看得見的東西,就是因為這樣的動蕩,沒有可能讓這些思考的東西落實下來。
滑田友先生肯定是個天才,當他進入雕塑領域的時候,一開始就遇到一個寶藏,就是用直壁塑,滑田友做了兩年,他是實實在在的做。從體會裡面去理解這個東西,所以這個“六法”在他的腦子裡生根。當他出國學習過程中,他很虛心,並沒有說,中國文化就比外國高,他覺得外國的好的東西我們來了就是要學習的,他認為好的東西是相通的。他這樣有了中國的第一桶金,或第一桶奶,又去挖掘,等他回來的時候收獲是巨大的。而且像人民英雄紀念碑這都是很好的機會,讓他發揮出來。但是,我看到后半截作品的時候發現,也是中國文化給了他悲劇性的東西,這些運動最終讓他的晚年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和創意,都沒有實現出來,一個是在文字上實現,一個是在作品上實現。
滑田友的作品我看了一些,我覺得在相當程度上是有平面性。跟羅丹當時說的“你要看到一個物體,它是對著你刺出來的”,滑田友的作品有不同,它是這樣斜著刺出來的,這個大概隻有雕塑家才能體會。我記得來美院讀研究生是1986年,讀到一本美國人的《世界雕塑史》,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小節,大概半頁紙,談到了中國的雕塑,他舉中國佛教雕塑例子,沒有什麼可說的,就是平面的東西。我讀了之后一宿沒睡著覺,覺得特別不公平,中國雕塑真是有平面性,可是讓人這麼說好像不值錢。只是在后來我的實踐當中,我覺得這個“平面性”美國人是不懂的,做雕塑當然是三維空間的東西,但是這個三維空間如果只是實實在在把三維空間反映出來,你只是寫了實﹔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方法並不完全追索、完全遵守復制這個真實三維空間的形體,那才是智慧,中國的雕塑其實就是智慧。其實一個雕塑形體放在那個地方,有光線、有跟觀者的距離、有跟環境的關系,你完全做三維的復制,從鼻子尖到后腦勺是40公分,就40厘米,也不見得真正在視覺上能達到那種效果,這種感受給作者的感受在不同的情況下是完全不同的,這時有作者自己的品味。這時我覺得如果能用20厘米達到40厘米的效果那就是智慧,雕塑從來沒有要求你要絕對達到物理空間,它永遠是一個視覺世界,它是視覺的東西。我看滑田友先生的《轟炸》,你要從側面看就是一堵牆,但它的趨勢是傾斜的,傾斜著出去,這個出去的力量我覺得是比這樣的(手勢直著出去)力量要強。我很喜歡他的《農夫》《母愛》《五四運動》《紅色游擊隊員》《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基本上找到一個方法,就是傾斜的出去,去佔有空間,去給人感覺。
這是特別智慧的方法,當然滑田友先生自己沒有說,他對中國傳統雕塑怎麼看,對中國傳統中好的雕塑怎麼看,但是他已經把握到了這個東西,對空間和形體的把握,並不是完全復制物理的空間,而是用自己主動的東西,把“氣韻生動”放在第一位的時候,具體的像與不像,物體上的空間就不重要了。
曹春生: (中國雕塑學會會長)
我覺得滑田友先生一輩子做人和他做藝術都體現了他的人格魅力,體現了他的學術品德。大家都談到,他能保持自己民族與文化的身份,在這個前提下,在西方那樣一個時代,研究西方的文化或者是法國文化的精華,把自己了解的中國文化能相融合,創作出我認為是國際水平的國際大師級的作品。
我們今天國家處在文化開放,把過去的禁錮、封閉完全打破了,我們今天有更多的機會面對世界的文化,而世界文化紛繁的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有的是好的,也有些是糟粕,我們怎麼能夠冷靜地去思考?在今天也有這樣一個現實問題,在今天怎麼學習西方?學習外國文化的同時,保留我們自己的民族品德,保留我們民族性,很好的結合,我覺得滑田友先生在那麼多年前實際上給我們做出榜樣。當然,今天我們有更大的選擇,但滑先生他通過自己的藝術實踐,能夠把作品呈現在我們面前,他說和做是統一的。他教學也好,做雕塑也好,他一直很低調,他從不張揚,他從不說我要有什麼“主義”,我要怎樣,他只是踏踏實實、勤勤懇懇的在工作。而且他在法國待了15年的時間,非常艱辛,他沒有公費,開始還有一些徐悲鴻先生的補貼,后來完全靠自己,他要維持生計,又要做出這樣一些作品,他沒有違背自己的意願去做,也沒有迎合某些時尚的潮流。因此,我們在今天學習的時候,也應該思索老一輩藝術家在對中西文化交融的時候如何把握自己的民族品格,把握住自己的文化身份,我覺得他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永遠懷著虔誠的敬意,所以他的作品具有中華文化淵源的一種博大,立足本土來融合中西,這些確實在我們今天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阿庚 滑夏整理選編)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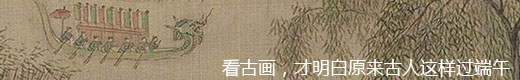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