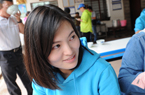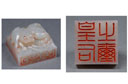續鶴賢
油畫作為一種外來畫種、一種繪畫的表現形式,100多年來經過幾代中國畫家的艱辛移植、播種和耕耘,在我國本土已開花結果,並受到國人的廣泛接納和青睞。
學習了30多年的油畫,當游歷觀摩了西方的許多博物館后,與珍藏內心的中國油畫相比對,不管古代、現代,還是視覺感觀、構造格局,個人覺得是兩碼事。國內許多同行也有相同的感受,常有中國油畫不得正法、亟須正本清源之嘆。我倒覺著兩者不同並不是壞事,造成此種局面,有東西方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的原因,說白了,就是各有各的吃法、活法和想法。
遙想東漢末年,印度佛教傳入華夏大地,至盛唐,可謂舉國尊崇,萬民禮拜。有記載,當時偏遠的高昌、交河小國也是佛寺百所、僧徒三千了,但大唐高僧玄奘還是覺著中國佛學與天竺摩揭陀國那爛拖寺的正本學說分歧不一,才決意西行,越阻涉險,求法取經。事實上,佛國天竺的佛教其后就日漸沒落了。我不知道今天的印度還有多少人在念經,但1000多年來華夏大地仍然香火不斷,佛窟寺院、晨鐘暮鼓依舊。也許不必追究佛教是外來的還是本土生成的,它與印度的真經正教有何區別,能延續千載並流傳下來,它一定是符合本土的政治、文化、人文、情感的需求,補充和構建了我們無比自豪稱頌、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這可能就是佛教的中國本土化之路吧。
西方繪畫源遠流長,巨匠輩出,讓人目不暇接,尤其文藝復興,更是天才輩出,佳作連連。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現代藝術家們更是標新立異,常見狂才、怪才、天才出世,給我們留下無數豐厚的繪畫藝術遺產和美輪美奐的視覺珍品。
每讀名典,常被西方一代代繪畫藝術大師勇敢的創造力所鼓舞和啟迪。我認為,文化藝術創造資源屬於全人類,美妙的藝術作品讓全人類共享,所以油畫是土還是洋並不重要。我不知梵高的藝術之路屬於荷蘭的本土化還是法國的異域化,隻聞當年梵高從荷蘭海牙初到法國巴黎,繪畫創作構想山窮水盡之時,恰是日本的浮世繪幫了他的大忙。
我又偏激地認為油畫只是一種繪畫藝術的表達形式。它在過去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是由一代代藝術家隨著時代的變革而發展的,無論是思想意識、畫面構成,還是在繪制形式、材料運用等方面。
單論油畫,它的祖先在500多年前並不姓“油”,而和我們的祖先同姓“水”和“膠”,是從北歐弗拉芒畫派的揚·凡·埃克兄弟之后才改姓“油”的。它由西方古代膠彩畫、木板蠟彩畫、濕壁畫、丹培拉演變和發展而最終形成。西方繪畫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隨著時代變革和經濟發展,無論從創作內容到表現形式、材料運用都曾有窮則思變、就地取材的過程,直至當今西方的眾多藝術家仍在大膽嘗試現代工業材料運用和新的獨特藝術理念表述。
作為中國當今有所作為的藝術家,不應該局限在對傳統油畫油色的迷戀。學習西方繪畫大師精湛技藝的同時,更應該學習他們勇猛精進、別開生面的創造精神,打破百年來國人對西方繪畫前輩的偏見,積極地感受我們所生存的這個時代,大膽自由地追尋繪畫藝術更多表現的可能性,尋覓各自內心深處真實的那個自我。隻有如此,才是對前輩藝術的尊重。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就有“油畫民族化”“國畫現代化”的倡導。3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回望歷史,覺著民族化、現代化的說法太過口號化、運動化,大多為的是鼓舞和宣揚民族自信心,但清點中國主流油畫的創作,大多還停留在西方傳統繪畫表面的描摹和翻版。
反觀國畫創作,也存在諸多問題。當年在國畫現代化思想的指引下,國畫家們越來越覺著文人畫才是水墨藝術的正脈。於是乎一擁而上,展覽畫冊多見梅蘭竹菊、深山幽寺,還有不知哪朝哪代寬袍大袖、假惺惺的古人。可笑的是,這樣的藝術家死后,將難題留給了后代,其作品甚至難以斷代。
當今中國的藝術家生活在前所未有的變革時期,有著太多太好的視覺平台,有太多的精神鼓舞和物質基礎,讓藝術家們創造劃時代的藝術作品成為可能,因為我們擁有比前輩太過優越的生存條件和視覺經驗。
麻布油彩、宣紙黛墨只是材料不同而已。油畫、水墨畫都是畫,作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確立我們自己的藝術理念,自主地構建新穎鮮明的繪畫表現法則,創作出有鮮活精神氣質的作品。隻有思想自由,藝術才能自由,繪畫表現不擇手段,才無愧於東西方的前輩先師,也無愧於我們所生存的本土——古老文明的中華民族。
(作者為油畫家)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