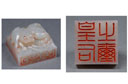丝玉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些活跃在其中的策展人与艺术家、画廊、媒体等处于一线的力量,同时面对着中国当代艺术全面资本化的大时代。身在其中的“第三代策展人”在接受着大大小小、重要或不重要的展览时,面对的最为核心的拷问依旧是:作为策展人,是否可以推动艺术史的发展,是否可以在展览的自身系统中有所作为?
对新一代策展人而言,技术问题逐渐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在完成技术批评的那天,或许才能迎来人们对这个行业真正的尊重。从栗宪庭、费大为、高名潞等第一代策展人,到皮力、邱志杰等第二代策展人,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当下时,“第三代策展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却遭到了质疑。比如,划分的依据只是根据年代和时间,便没有了针对策展人本身的问题性;如果根据年代来划分,那活跃在其中的策展人却依然有年龄悬殊的现状。于是,“第三代”的提出,好像除了把当下的策展人整体化之外,还提前在归纳总结中结束了这个时代。在深入策展人的工作内部,并呈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实则是他们对艺术的见解,于展览的专业程度,以及人的品格、性情和气质对展览产生的作用。
从2014年美术馆层出不穷的策展人扶持计划开始,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策展人愈发的关注,实则是对现状的不满。由于近几年展览的过度商业化,以及大部分的展览并无作为,以至于早在前几年便已有人宣布了策展人时代的消失。当我们试图谈论“第三代策展人”的作为时,首要谈论的还是策展人在职业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职业化,是策展制度形成后对以策展为生的策划人的描述。在极度商业化的中国当代艺术中,策展人对“职业化”的谈论却是相当谨慎。
当策展成为一种职业时,其中最难处理的便是如何以此为生,但又不沦落至市场的附庸者?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每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地给予什么意见。如果职业化在今天并非问题的矛盾中心,那么如何做一个专业的策划人却是正中要害的提问。
比如,从展厅之内对地板、灯光、墙面,以及整体视觉的控制和把握,到展厅之外,宣传、讲解和各种关系的调和,是否可以在每个展览中都做到精益求精?除了这些需要亲力亲为的执行事项,是否可以写出一篇没有逻辑错误、语言简明、准确且有深度的策展手记?单单这一项,就足以把许多以玩弄文字、滥用概念的策展人拒之门外了。
当然,我们与策展人谈及专业化的时候,并不能从他们的表述中得知这些“专业化”能够在真实的展览现场实现几成?对展览一分一毫的用心谨慎,不在于策展人是否专业,而在于一份专业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里还有一丝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展览本身的念想,即便没有100分,也在去往100分的路上了吧。
今天,我们还需要策展人吗?这是一个萦绕在我脑海里近两年的问题。两年前,我和友人在谈论未来的“策划人”该何去何从时,从艺术家的需求、艺术生态的状况、策展人的作为三个方面分析,悲观地得出一个结论:在遍地都是策展人的今天,那曾经属于策展人的荣耀却在不断消失。这种荣耀,曾几何时也只在前辈的言谈中感受到一二,无论是谈及“85美术新潮运动”时理想主义的热情,还是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代艺术的步履维艰,艺术家、策展人和一同走过的那些展览,都印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向前迈出的每一步。
有策展人调侃道:“策展人的理想状态是导演,实际状况是包工头。”这的确是许多策展人不断抱怨的现状。一个好的展览,从思想的出现到感觉的爆发,策展人在其中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全力以赴的。只要你投入其中,便是博弈和斗争的开始。在力量的角逐中,有些人为名,有些人为利,有些人则为艺术家、为艺术、为展览。所以,能够独立在商业之外,像大师一样纯粹地做个展览,应该是这个时代不可为,却一定要努力让之可为的事。
理想很伟大,现实很残酷。除了自己,没有人还会真的在意你是否拥有高贵的品格和对艺术基本的尊重和道义。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说多了也是无益,语言和行动的缝隙间是越来越职业的表白,带有表演性的勤奋和越来越没有进取之心的虚伪和懒惰。过眼烟云般的展览,浪费了太多这个行业里的资源,它们既不能为好的艺术家打开一扇门,也不能对艺术的发展有一丝一毫的推进。当代艺术领域中,大部分策划人的展览最终只能也仅能成就个人的历史,而无法为艺术的发展或艺术史的发展给予真正的推动力。
在今天,一个好的作品,在一个错误的空间,最终也只能成就一个无效的展览。如何实现作品的“在场”等于艺术家的“在场”,同时又能让展览的“存在”成就艺术家和策展人同时的“不在场”,是一个好的展览最难把握和控制的地方。
当我们完成展览的技术批评的时刻,或许才能迎来人们对这个行业真正的尊重。而在展览之外的空间中、在当代艺术生存的环境中,这些策展人的态度和作为依旧承担着让整个生态有所好转的责任。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