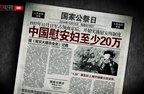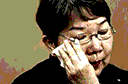内蒙古包头秦汉长城遗址
与考古发现相辅相成的是一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目前全区共有馆藏文物50万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90件、二级文物4050件、三级文物6545件。这些文物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浓郁,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碧玉龙,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鄂尔多斯市霍洛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鹰形金冠饰、虎牛咬斗纹金带饰等珍贵文物,是匈奴贵族单于王的重要遗物。乌兰察布市发现的“虎噬鹰”格里芬金牌饰、金项圈,象征着匈奴王权的尊贵与威严。呼伦贝尔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等地发现的“叠兽纹”“三鹿纹”金牌饰以及其他的金冠饰、金带饰等文物,都是鲜卑贵族使用的代表性装饰品;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双鱼龙纹银盘、鱼龙纹银壶、波斯银壶,是唐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一批重要文物。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黄金面具、龙凤形玉配饰,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褐釉鸡冠壶、双耳穿带瓶,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彩绘木棺、鎏金宝石镜盒以及造型各异的瓷器、金器、玉器及装饰奢华的马具等,是辽代文物的精品。元上都遗址出土的汉白玉龙纹角柱与柱础,再现了元代皇家宫城建筑的华丽与辉煌的气势;金马鞍是体现蒙古族游牧与丧葬风俗的绝品文物,具有游牧民族“四时迁徙,鞍马为家”的文化特点,又是蒙古贵族“秘葬”风俗习惯的真实反映;而八思巴字的圣旨令牌,是代表元朝皇权的典型文物,既是传达皇帝圣旨与政令的信物,也是蒙元时期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特点与国家驿站制度的综合体现。元代瓷器类文物首推青花、釉里红瓷器,其中以包头燕家梁出土的青花大罐,集宁路出土的青花梨形壶、釉里红玉壶春瓶最为珍贵。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是内蒙古自治区珍贵的文化资源,是草原文明的主要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文化重要的实物例证。
充分发掘草原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并取得累累硕果,重要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有力地保障了自治区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遗产日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夯实了草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内蒙古地区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草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如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属于旧石器文化的石器制造场与其他的人类遗迹,相当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文化面貌,将内蒙古地区人类的历史上推到50万年前;再如红山文化遗址及典型文物碧玉龙的发现,堪称中华文明的曙光。红山诸文化考古序列的确立,如同中原地区第一次从地层上明确划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时间序列的意义一样,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从发端到发展的历史脉络勾勒得一清二楚,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白,极大地完善了草原文化研究的序列与谱系。
其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内蒙古文化强区的时代需要。文化遗产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的物化遗留,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人们唯一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文化实体,具有无可比拟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因此,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既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与认知,也是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所以,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动力,在文化建设上实现新的跨越,这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区的迫切需要。
再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是让文化资源惠及民众的有效途径,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需要。文化遗产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承载的信息量丰富,知名度高,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介质。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鉴赏者和传承者,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也必须惠及社会,融入社会,为民造福。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实物见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发展,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也是保护、弘扬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 上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