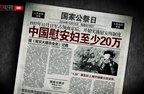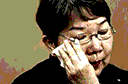谁都不敢随便说它是真是假。藏家把它带到北京,找诸多专家鉴定,结果却得出了官窑、民窑、乾隆时期、民国仿等诸多结果。对于转芯瓶来说,这几个身份的价格犹如坐上过山车,有着天壤之别。
于是,藏家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了关海森的高科技仪器上。相比人眼得出的“专家结果”,也许高科技的“机器眼”更可信。
关海森开始用各种设备及方法对这件转芯瓶进行了将近两个多月的“诊断”。
这件瓷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四部分组成的。别的瓷器都是一个整体,用仪器检测几个环节就能下结论。但这转芯瓶不行,有专家说这四部分可能是新老拼凑起来的。那么,对其做科技测试,就需要相当多的步骤。
首先可以确定的,便是它是否为新仿。第一步,关海森让它接受了“皮肤测试”,也就是用放大40倍的显微镜来观察它的底足。因为这底足没有釉保护,坯体是露在外面,如果经过百年,水和空气要沁入在里边,会出现一些斑驳的地方,坯体上的这些痕迹要比釉显现得更为明显。
结果,它的底足上现出了污垢状东西,这是由于经过多年外部环境的沁染与坯体材料自身氧化共同造成的,完全吃在坯体里边了。关海森认为,这些斑痕少说也得百年以上才能形成。相反如果在显微镜下底足上出现类似黄色和白色均匀的小颗粒,也就是氧化铝,肯定是现代仿品。
原来,传统烧窑是把瓷器放在一个匣钵里,古人为了保证瓷器的质量,一般一件瓷器配一个匣钵。但是现代仿品为了节约成本、批量生产,就把瓷器摆放在棚板上直接裸烧。为了避免烧成后瓷器的底足和棚板粘连在一起,就在棚板上撒上一层白色的耐火材料粉末,常用三氧化二铝粉等。等烧成出窑后,凝固的釉将这些白色的粉末粘接在瓷器的足底上了,而古人没有氧化铝粉,所以底足上不会有这些小颗粒。
经过对转芯瓶底座的排查,这件底座的确是老的,少说也得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那么,这件瓷器会不会是老底儿和新瓶子拼凑在一块儿的呢?于是,关海森进行了第二项排查,那就是看皱纹。瓷器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长“皱纹”,只不过它们的皱纹,行话叫开片,也就是细碎的裂纹。要看釉上彩是否老化,可以通过开片的形状、颜色,包括附着物,判断这个裂纹的断裂原因和时间。如果是老开片的话,细缝儿里不但呈黄色,而且还会是蜿蜒、不规则的形状。结果,在放大200倍的显微镜下,这件瓷瓶果然出现了这些现象。于是,可以判断瓶身也是老的。
接下来,怎么能够证明这四部分是原配,而不是后来拼凑在一起的呢?关海森介绍,瓷器也有血缘关系,可以用“DNA化验”来验明正身,那就是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对坯体和透明釉检测,每种含量都可以看出来。结果,这瓷瓶四部分里边含有的钙、铁、铅等元素都相差不大。通过这个测试,瓶体的主要元素基本和底足的坯体是一样的,说明是一体的。
前面的所有科技检验结束后,已经可以说明这个瓷瓶是老的。但是,这个“老”究竟老到什么地步呢?它可能是晚清民国的,也可能是清中期的,说不定还是乾隆本朝的。这时,科技就要和考古分析结合了。
关海森介绍,这个瓶身上的画片所表现的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兵临北京城时的情景,说的就是多尔衮率领八旗不费一兵一卒得了天下,是在为大清歌功颂德。而在民国,则不可能出现为清朝歌功颂德的题材,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当时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那么,它有可能是乾隆时期的吗?关海森对底足上粉彩的几种颜色用多功能光谱仪进行了检测,也对乾隆时期相同颜色的粉彩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它和乾隆时期的有差距,因而判断它不是乾隆的。最终,关海森得出结论,这件转芯瓶是清中晚期的作品,因为当时同治皇帝大婚时烧造过一批黄釉粉彩。不过,这种断代方法,只是作为一种参考,不是铁证。
关海森认为,从这件转芯瓶的整个鉴定过程可以看出,科技手段对于瓷器的新旧有很强的判断力,但在断代方面,还应该和传统的考古方法结合,去考证它的艺术风格和历史背景。也就是说,科技手段和考古手段两者是互补的,并不排斥,就像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一样。关海森自己,便是先学了“中医”,后来再成为“古玩西医”的。
如今,这件转芯瓶的鉴定全过程已经成为中国文物科技鉴定的经典案例。
“文物是载体,玩古玩是乐子,会感觉把你的生命拉长了。人一辈子就这么几十年,经历越多,生命越长。比如我接触古代的文物,就会觉得是在跟古人握手,因为它传达了一种情绪、一种体验。”关海森说。
十多年前,在一期电视节目中,关海森先生说自己的理想是:“开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网站,能出自己写的书。”如今,这些理想均已实现。
最近,他准备出一本《古玩解剖辨伪图说》。这本书,他写了20年。
关海森说现在又有了新理想:“希望能建立个古玩真假对比博物馆,现在我正在筹备真假文物对比展览。”
在关海森的办公桌上,放着前面介绍的转芯瓶图片的瓷器“收藏证书”,证书的背面罗列了各种仪器分析结果,尾部有非常醒目的一行字——“以上数据由关海森提供,并对所述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在中国文物鉴定界,他是第一位提出由自己承担法律责任的文物科技鉴定家。
多年来,关海森一直从事着文物鉴定的公益事业,但他说自己不会参与社会上的古玩鉴定活动,也没精力接待来自各地的收藏爱好者,“凭我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将各类假古董一网打尽。”
他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各种鉴定方法、工具向社会推广、普及。“只有让每一位收藏者自己学会并掌握辨别真伪的方法后,不再购买那些赝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赝品泛滥的问题。”
从地摊上一路走来,关海森一直不把自己当“专家”。自己和周围的朋友都受过假古董的蒙骗,他要自己想办法,辨别真伪。“用心找,不放弃,就能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思考的过程,真假是有绝对区别的。”他说,“最好不去碰不熟悉的东西。鉴定家永远只能在造假者后面。新造假手段出来了,才会有新的鉴定技术的出现。”由于自己也是个收藏家,拿着真金白银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因而关海森一直是在失败中学习和改进。他会对那些擅长“吹牛”的鉴定家说:“先死的是大夫。”
上一页12下一页
| 上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