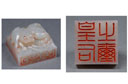遠山(中國畫)
田黎明

窗外(中國畫)
田黎明
田黎明的畫和人之間,有一種天然而明確的對應性。他的畫是漂浮的霧氣。我透過霧氣看到田黎明。
可生長的創新
藝術創新,是1978年以來整個中國文藝界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曾經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天天都在冥思苦想怎樣創新,但是少有人把創新本身作為一個理論問題認真探討。近年來有各種各樣的創新。有的創新當時很轟動,后來就沒有了,就像孩子們在沙灘上努力壘起來的城堡和房子。還有一些創新,或許當時沒有那麼轟動,卻像銀河系裡的恆星,持續地發出光亮。創新是有類型性的。田黎明的創新,有一定的引領性和恆定性。因此,田黎明和他的畫,對當代中國畫創作的影響,也具有一種滲透性。這在大量的創新型畫家中為數不多。因為歷史的選擇,是很嚴格、很嚴酷、沒有什麼客氣和溫情的。
田黎明的創新,帶來了什麼呢?
陽光、空氣、水,是田黎明繪畫表現的主體。三者共同的特征,就是從容、透明、輕盈、恬淡、靜謐。田黎明畫那些在田野、在河邊、在山林裡,只是自然隨意地站著、倚著、躺著,幾乎沒有任何戲劇性動作,梳著兩條長辮子、穿著一身過去農村女孩的朴素衣衫,雙眸淡淡地看著世界沒有任何刻意表情的少女﹔還有那些似乎隻知道在村邊小河裡無拘無束游泳而不知道人間愁苦的孩子。他們本身就像陽光一樣明朗,空氣一樣透明,河水一樣清澈。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一點被世俗功利熏染后的污濁。那些不甚清晰有點飄忽,離今天很遠而且越來越遠的關於童年、田野、少女的記憶,經過想象和藝術的加工、提純,變成了宣紙上的夢和詩。可以肯定,那些純真的少女曾經深刻地映入過他兒時的眼帘和心靈,而那些在河裡快樂戲水的童子,他,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正是這些,構成了田黎明中國畫作品中非常特殊的抒情性和詩意,並適應了時代精神的別一種需要——這個時代的情緒太喧囂太騷動,色彩也太強烈太斑駁,田黎明給這個時代,帶來了精神上一些非常缺乏而全新的東西,以及對美好、寧靜、詩意、純真的期待。畫中流淌的那股清純得幾乎沒有一絲雜念、雜質的情愫,就像清晨剛被露水洗過的嫩草葉子,像山澗邊初開的一朵不知名的小花。這是影響他一生的記憶積澱,也是他畫裡最讓人感動的東西。
田黎明的創新,從上世紀80年代到今天,一直都在堅持、努力的行進過程之中。創新要有恆久性。其奧秘就在於,創新的圖式語言本身要有可生長性,要像一顆有生命活力的種子,能在時間的流動裡長出新苗、樹干、樹枝、綠葉,能夠年復一年地開花、結果。田黎明作品的圖式語言便具有生長性。他1988年創作的《小溪》《草原》,背景是一片空無,年輕和年長的女性面容和身軀極其朦朧,依稀可辨。慢慢的,他筆下的人物五官輪廓變得稍稍清晰起來,景物也從一片空無裡淡淡地浮了出來。田黎明最早畫古裝人物與現代女性、兒童,后來從女性擴展到男性,從兒童擴展到成人。他作品的圖式結構也由無背景的單個人的簡單,慢慢變成了人物和景色的有機交集、人物和人物參差組合的復雜,便有了《群賢畢至 俯仰天地》渾然一體的結構。他的創作視野由早期的淳朴農村慢慢走向現代城市,穿著時尚的都市女性、掃街的農民工、提著行李的打工妹紛紛闖進了他的畫面。在那裡,富有原生態的大地河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高高的樓群和如織的車流、人流。這樣,他的繪畫不但有抒情性,也有了頗具抒情意味的社會性。藝術語言的生長是一個緩慢漫長的時間過程。田黎明繪畫語言的生長過程清晰、有序,每一步都走得很堅實。
“淡”的發現
中國畫用墨,常規上既不焦也不淡,超過常規的那些墨色都是附加性的,不能成為主體,比如極淡的淡墨和焦黑得發澀的焦墨。田黎明把這些非常規性的原來只是局部或偶爾使用的繪畫語素,發掘出來並加以持續放大,進而摸索成一套能持續使用的規范的繪畫語法系統,使之潛在的功能得以釋放。極淡的淡墨和同樣極淡的淡彩渾然一體,讓中國畫擁有了一種全新的審美上的陌生感。
中國畫歷來強調筆墨。20世紀以來,中國畫對墨的發現和運用,超過了對筆、對線的發現和運用。人們發現不常使用的淡墨、宿墨、焦墨,都可以成為中國畫墨色的主體、主調。淡墨和焦墨處於中國畫墨色的兩極。墨色的核心是對水的分寸感的掌控,水是中國畫技術體系中最不直接露面但操縱一切的精靈。如果說焦墨是用水的極度收斂,那麼淡墨就是用水的極度放縱,放縱大量的水對墨的極度稀釋。在田黎明的作品裡,極淡的淡墨使畫面基調呈現抒情意味極濃、帶有夢幻色彩的淡淡的銀灰調子,給人余音裊裊的想象和韻味。
我把田黎明的藝術語言的創新,稱之為“淡”的發現。他有一張山水高士圖,畫題即為《萬物皆淡》。畫中兩個淡如疏影的高士,面容衣著淡如羽翳,站在淡如曉霧的山石間,流露出一派萬物與我何干的淡泊心情。對於田黎明來說,“淡”是一種藝術的整體。不僅是墨,還有色。
田黎明繪畫對色的新的發現,與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外各種各樣的繪畫流派大規模地被引入到中國有關。在新的藝術語境下,中國畫的發展呈現一種新的趨勢,就是對色彩和新顏料大規模地運用和開掘。這種開掘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畫的表現手段,使傳統中國畫煥發出新的時代氣息。但這種開掘和運用,經常還是集中在常規意義上的。田黎明的用色,可以看到印象派注重外光的明顯影響。那些飄落在人物臉龐和軀干上的光斑,是他對印象派外光的理解和消化。更重要的是,田黎明的用色有自己的巧妙用心。和他的淡墨一樣,九分水一分色,色溶於水,極淡極淡,淡到大地、山川、林木、庄稼和人物的色彩,都有了一種離紙而去的漂浮感和輕盈感,把中國宣紙吸水、化水的特點用到了極致。這是一種境界。應該說他對色彩的運用,是非常規的。以水色、水墨渲染形成的水汽迷蒙的塊面,構成田黎明繪畫的主體。人物和景物徘徊在平面和立體之間,再加上他用色的純淨,就有了一種視覺上似是而非的朦朧詩意,有了一種心理上寧靜純澈的安詳穩定感。
我總覺得田黎明的畫,某種意義上有點像20世紀80年代初的朦朧詩,飄忽、朦朧。但是,朦朧詩指向晦澀,總是要人注解,否則很容易產生歧義。在當年,關於朦朧詩產生了很大的爭論。而田黎明的畫,好像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爭論。因為他的朦朧指向了清晰、清新——形象物象是大體清晰的﹔情緒主題是清新的。我看他的畫,就像自己走在早晨的田野裡,有霧氣扑面而來,低下頭就可以看見草叢中露珠的感覺。田黎明描寫的是心理上屬於“清晨大地的東西”。他對極淡色調的發現和運用,完成了對美的追求。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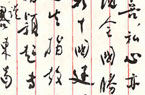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