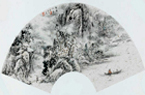田黎明 《河邊小歇》 鏡心 49×69厘米

李華? 《絲瀑》 紙本水墨 114×236厘米

吳冠中 《江南春色》 紙本水墨 68×92厘米
自上世紀80年代李小山以“中國畫窮途末路”宣判中國畫的終結命運以來,在以革命和前衛追求為主旨的藝術家群體中,“水墨”一詞便開始替代“國畫”而以一種更開放和靈活的姿態,不斷地演化並變生為包括“抽象水墨”“實驗水墨”“都市水墨”在內的眾多新名稱。
雖然每個階段的水墨變種都不乏“激起千層浪”的震動能量,但無論是創作者、評論者還是收藏者,似乎都沒有因為任何一個變種而心滿意足。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水墨這種延續千年的藝術形態才具有如此強大的新陳代謝能力,不斷地以更名、變形、變象的方式演繹並書寫著自身歧路多舛的歷史寓言。
作為一種時刻自警又遷流不息的藝術形態,在媒體大力熱炒“中國當代藝術重新洗牌”的當下,“水墨”這個藝術界的骨灰級老朋友又以“新”字打頭再次出場,用“新水墨”這個響亮的名號引來業內外無數關注的目光。
然而,“關注”不是“下注”,關注的同時還意味著審慎的觀察和各種各樣的疑問。於是,“新水墨”少不了要擺開陣仗迎接各路好事者的品頭論足。無論是人頭攢動的各種“新水墨”的展覽現場,還是網絡上此起彼伏的論戰陣營,支持者有之,反對者有之,追問者更有之。在經歷了當代藝術市場的大漲大落之后,無論是對於創作者還是對於評論者、收藏者而言,昔日一人振臂而萬夫沖鋒的場面再也難得一見。面對新水墨來勢洶洶的宣傳陣勢,多數人保持了必要的冷靜和觀望的態度,並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喧鬧中嘗試提出自己心中的諸多疑問,耐心地等待著業界人士給出合理的回答。
“新水墨”真的是中國當代藝術的下一站嗎?“新水墨”真的意味著藝術收藏和投資的光明未來嗎?“新水墨”真的是一劑拯救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和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仙丹良藥嗎?
如果我們用時下流行的環拍鏡頭橫掃全球的藝術史和當下的藝術實踐,便會驚奇地發現,水墨之於我們,就像夏夜裡突然撞見的蛛網,纏結沾粘,揮之不去。而這看似簡單的藝術現象,卻因為牽扯了我們太多的家國舊夢、民族傳統、文化自信、族群形象等大問題而變得異常復雜。似乎沒有哪一個民族,也沒有任何一種藝術形態,能夠像中國人與水墨這樣,“怨偶”式地長久處於一種難以厘清的矛盾和糾結當中,人們總是想方設法地試圖把它講得更清楚、做得更明白,但又似乎總是事與願違。
上世紀80年代的“抽象水墨”因其對個性化和自我價值的強調而與之前的藝術形態形成對比,並在符合當時文化邏輯的基礎上為自身贏得了一席之地。但“抽象水墨”由於難逃西方抽象影響之嫌,容易被看做西方形式主義抽象藝術的水墨變體,從而使得傳續千年的“水墨精神”隻留下材料和技法的空殼,內部的精神氣韻卻被假想的西方藝術勁敵抽空了,因此很快不了了之。
90年代的“實驗水墨”因不滿於抽象水墨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強調水墨藝術應該進一步拓展和開放自身的變異空間,通過與符號挪用、材料拼貼、行為表演、裝置現場等更“當代”的嫁接而發出另謀出路的呼聲。但是,雖然藝術家們希望借用古代中國的視覺文本、技術經驗而與西方流行的當代藝術創作方式相結合,但水墨自身的現代轉向問題並不能通過西方樣式和方法的引入而得到解決,這種做法只是“另起一行”的策略,而上一段落未寫完的文句仍然難以處理“文氣不通”的舊弊,最終落得個虎頭蛇尾的結局。
至於“都市水墨”,則是企圖從主題上突破山水、花鳥等前現代中國的審美趣味,將關注點從傳統文人士大夫的詩意生活轉移到當代人的現實境遇,用人群攢動的“都市”替換舊時代畫面中山野荒林的“郊外”。但都市水墨就像都市油畫、都市雕塑、都市版畫一樣,原本就是一種邏輯不通的“應急措施”,既與水墨精神的傳續問題無關,也與水墨形態的當代轉型無涉,用“都市”這個定語來修飾“水墨”,實在是隔靴搔痒的權宜之計,至多被視作水墨藝術的都市形態,而不能反過來用“都市”去化約或規避水墨藝術遇到的諸多問題。
那麼“新水墨”又能否出奇制勝呢?“新水墨”的提法沒有選擇“抽象”“觀念”“都市”等指意明確的名詞性定語,而選用了表示“別於以往”的“新”字打頭,在新形態與舊形態、新視角與舊視角、新美學與舊美學之間輕巧地劃了一條若隱若現的邊界。
倘若觀者能夠“善解人意”,那麼“新水墨”首先提示了一種更加開放的姿態,放棄主動選擇某種立場的策略,而用模糊的形容詞定語暗示了水墨創作現狀的混沌和難以確定的未來。其次,“新水墨”似乎告別了30年來中國當代藝術習慣的“革命模式”,刪除了革命的假想敵,而以改良的姿態“低調”登場。第三,因為方向不明,於是“新水墨”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特別明顯的替代動機,而只是表達了與舊有別的簡單意圖。
但是,“新水墨”這種放棄正面沖突的迂回方式,也很容易引起人們更多的策略揣測——倘若不是革命而是改良,那麼是否意味著80年代以來爭取藝術獨立自由的努力(無論是針對社會生活的外向努力,還是針對藝術本體的內向努力)已經不再是藝術發展的內源動力?倘若藝術家放棄針鋒相對的姿態,是否也同時意味著放棄了“不合作”的姿態而以更加積極的、策略化的身段投入與商業的長袖共舞之中?倘若上述兩種猜想成立,那麼“新水墨”在進入收藏市場甚或藝術史書寫之后,又能在學術層面具有多大的藝術價值、歷史價值、文獻價值、研究價值?又能在收藏層面具有多大的未來增值空間?畢竟,“藝術‘品’”的收藏流通價值依托於“藝術”的學術嚴肅程度,這恐怕是新水墨的同盟軍們必須嚴陣以對的問題。
同時,上述詰問中還隱含著某種更加深層的探討——“抽象水墨”和“實驗水墨”的發生都與彼時中國的所謂文化邏輯相關,有它們萌芽、生長、發展的藝術內驅力。相對的,“新水墨”的“模糊策略”在呈現自身開放姿態的同時,似乎也模糊了它之所以能夠立身的邏輯起點,而這個邏輯起點又將同時成為撬動“新水墨”學術價值和市場價值的重要支點。因此,如何安放這個邏輯起點,如何在紛繁復雜的當代藝術價值系統中為自身的價值呈現找到支點,就成為了“新水墨”必須不斷思考和強調的關鍵。
當然,作為一種正在發生並不斷發展的藝術現象,用明確的概念來框定“新水墨”確非明智之舉,那樣的做法既難以避免學術建構上的潛在漏洞,也可能造成市場策略上的意外偏狹。但是,創作者、評論者和推廣者們至少可以嘗試為“新水墨”這艘大船的入水提供必要的航道設計,並逐漸揀選出一些原則性的分析線索。雖然這些線索不足以構成“新水墨”價值判斷的精確標准,但至少可以作為展開討論的相對參照。
因此,“新水墨”能否在主題的選擇上與都市水墨、新文人畫、實驗水墨等表現出不同的側重?能否在作品的方式上避免對水墨的抽象化、水墨的裝置化、水墨的符號化等方式的重復?能否在美學表達上實現對氣韻生動、文人意境等傳統水墨美學的革新或拓延?都是關系到“新水墨”能否讓自己如理如法地立身於水墨歷史,並合邏輯地書寫水墨未來的系統性問題。所以,雖然“新水墨”的提出動機是可以理解的,其兼容並包的模糊策略也不失為鼓勵當下水墨創作多元化發生和發展的明智之舉,但是,畢竟水墨之於中國藝術,已經有過太多的實踐、推演、猜想、爭論,汗牛充棟的水墨經驗已將“水墨如何創新”這個老問題擠了歷史的夾縫之中,而“新水墨”也必然意味著水墨藝術的盟軍們將要開啟一段易言難行的荊棘之旅。
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水墨”能否“新”起來,或許只是水墨盟軍們的自擾之題。倘若從當代藝術的綜合角度來觀察,“水墨”這個藝術問題完全可以因其深厚的歷史經驗和豐富的文化指涉,而成為一個在“東方思維”層面深入討論的文化追究。
無論是抽象水墨、實驗水墨、新水墨,還是其他的××水墨,“如何水墨”其實並非問題的核心,而如何在百年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歷史語境中,以水墨為載體提出與西方藝術經驗相互呼應補足的獨特的“文化價值觀”和“藝術方法論”?如何讓水墨創作從族群歷史、本土問題的糾結中跳脫出來,轉化為一種與藝術家“個體氣質”明確相關的藝術表達?如何通過具有當代性的水墨創作來彰顯藝術家在思維方式層面的自我錘煉、歷史反思和當下關照?如何使水墨創作的主題、理念、技巧、方式、面貌等各個方面都能充分呈現藝術家在“文化思考力”和“藝術創作力”方面的獨特氣質?隻有深入而系統地解決上述的一系列問題,才有可能使中國人心中的“水墨魔咒”不攻自破,也才真正能夠從當代藝術的角度來思考水墨,而不僅僅是從水墨藝術的角度來介入當代。
誠然,水墨就像油畫、版畫等其他藝術形態一樣,包含著豐富的創作方向和創作意圖,並不能單從“當代與否”的角度橫刀切斷。但是,或許我們可以借用一個有趣的比喻來暗示某種思考的線索——有人說,林林總總的藝術形態或可分作3種簡單的類比:其一,藝術是零食,好吃,但是沒有營養,口感的快慰之后,隻留下對身體的損傷﹔其二,藝術是糧食,並無特別誘人的味道,但人必須每天都吃,口感也許有些無奇,卻保養身體﹔其三,藝術是良藥,入口苦澀難咽,卻能治病療傷。倘若在中國當代藝術近30年的熏習當中,我們確實感染了一種尋醫問藥的強迫症,那麼當藝術家們開出“新水墨”這一劑藥方時,我們就不得不審慎地追問——“新水墨”真的是一劑良藥嗎? (武湛)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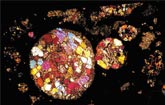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