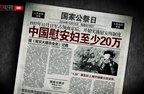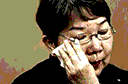《橙、红、黄》马克·罗斯科
《自画像》梵·高
梵·高
人间怪胎 灵魂圣洁
木心先生曾经梳理过艺术史中几对伟大的朋友关系,席勒与歌德是典范,至死不渝。1805年,歌德在给席勒的新年贺信上无意中写下“最后一年”,惊觉不对,换纸重写,信中又出现了“我们两个之中,总有一个是最后一年”。席勒于那一年,卒。歌德平时喜怒无形色,唯得知席勒死讯,他双手掩面如女子般哭泣,后来说:“我一半的生命死去了。”木心先生对这样的朋友关系赞不绝口,文中时常表露出欣羡,难怪有人称先生是活在当代的理想主义希腊人。
人生能得这样一知己,实属幸运,可大多数人往往没有这样的福分,就像梵·高。当他到达法国阿尔的时候近乎疯狂,他爱上阿尔的一切,在等待高更到来之前,梵·高活在浪漫的理想国里,他情绪亢奋,用颜色描绘着阿尔的所有,《繁花盛开的果园》,《罗纳河畔的星夜》等,甚至用高更的笔法画了一幅《阿尔的女人》,在等待高更到来之前,他将房屋涂成了金黄色,一切都梦幻到无可挑剔。然后翘首以盼自己的朋友——高更到来。他将高更拉入他的理想国。
将两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家放在一起,就像将两匹优良的烈马放在一起,梵·高与高更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生了剧烈的争执,从生活方式不合到思想观念相左,长期的冲突让这个金黄色的理想国瞬间崩溃,在混乱之中,梵·高身体内潜藏的精神病发作,于是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高更去了巴黎,而梵·高堕入了精神疾病中无法自拔。
这段时间瑞典哥德堡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关于梵·高和高更的展览。本次展览,以梵·高与高更画作风格的发展为主轴,两人的作品相对而放,好像全世界的大多数人只记住了他们住在阿尔的短暂快乐时光,而忘记了他们之间的纷争。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最后一幅画作,是弗朗西斯·培根所画的梵·高,红绿交错,加上弗朗西斯独特的“撕裂人格”的绘画风格,让观者对于展览布置一切的赞同与反对都变得无关紧要,起码每一位观者都是笑着离开的。
其实,从梵·高的画作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问题,他总是情绪激动,如《向日葵》;也总是意志消弭,如《星夜》。在他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时常语气悲伤,并且具有自杀倾向,他曾借用福楼拜的话:天才就是长期的忍耐。不难看出他一直在忍耐生活,可是忍耐的最后往往伴随着毁灭性的爆发。梵·高的一位画家朋友纪约曼回忆他突然激动起来的情景时说:“他为了迫不及待地解释自己的看法,竟脱掉衣服,跪在地上,无论怎样也无法使他平静下来。”
因为其身后之名影响深远,每每当有人询问周遭你最爱的艺术家是谁,很多人都会迫不及待地回答:梵·高。时隔经年,我们都对其充满敬仰,可是在他生活的年代,所有人都嘲笑他为疯子,一个孤独的,失去了耳朵的,白痴。
“在我面对自然的时候,画画的欲望就会油然而生。”梵·高在自己的绘画中,像他的《向日葵》一般,梵·高就是生机勃勃,充满生命激情的太阳。他的画无所谓思想深度或者诗意,非要深谈实则无意,只是形象家,如同威廉·柯柏、德彪西一般,这类人一般可爱,单纯,善良,很好相处。走灵魂智力路线的艺术家却不好相处,他们挟灵智而令众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一书中的梅什金公爵,人人皆称之为白痴,但他像一个虚无主义者,站在玩弄灵智的群像之上,梵·高和他一样,被人看作怪胎,却拥有着圣洁的灵魂。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