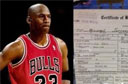今日美術館前岳敏君雕塑作品。
中國並非“沒有好的公共藝術”,只是稀缺好的當代公共藝術。
首先,中國不乏公共藝術。我不同意公共藝術隻會產生在現在民主時代、民主社會的霸釋。隻要藝術試圖作用於公眾,就會被視讀、被針對、被影響。花山岩畫、司母戊大方鼎、龍門石窟,這些出現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非民主時代的藝術,顯然也有公共性。古代社會生生不息的民間藝術,基本上都算公共藝術,一隻風箏飛到天上,不管誰放的,不管屬於誰,公眾可賞,風箏即具公共性。
其二,就算不加上以前的公共藝術,當代中國的公共藝術總量也是全球最多的之一。“公共藝術”概念的門檻沒有想像得那麼高,依存於開放空間的造型藝術,就是公共藝術。區別於私屬空間的開放空間,反映為大眾無須特別許可(包括無須專門付費)就能視讀。由於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城市建設規模持續相當於全世界其他國家規模的總和,海量的需求、巨資的刺激、短時的擠爆,令當代中國公共藝術30多年來的產出量至少超過了以往300年的總和,600多個中國城市平均出現百余件公共藝術。保守估計,當代中國公共藝術可達六位數字,僅北上廣就超過萬件。
第三,公共藝術的精粗良莠,是是非非,不能基於階段效應定好壞。否則,當肯定我們擁有大批“好”的公共藝術,你就是搬出維納斯、哀悼基督、美人魚、自由女神像,小於連,中國也有社會影響面、知名度不遜的例証,如偉人像、熊貓像、收租院雕塑、“農業學大寨”、“隻生一個好”的地景標語等等,把它們算上,中國當屬公共藝術影響最多人口的大國。
現在,中國公共藝術為何卻沒有眾口交譽?我認為是因為非精品太多,精品太少。原因主要有八:
一、新的文化准備不足。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最需要的心態是感恩公眾敬畏公義。公共藝術的建造目的重在先進文化的福利分配而不是上游的一方向下游一方的宣傳、勸服、告誡,它要體現新文化的精神,要設定優先目的是予公眾文化啟示和審美。但從事者這方面思想准備不足,還在很農業甚至有些封建地利用公共藝術。
二、公眾決定權旁落。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公眾本該是公共藝術的唯一主人,但公共藝術立項不反映公眾需求,是好是壞,喜歡或厭惡公眾插不上嘴,忍無可忍時以“順口溜”吐槽抗擊之,多數時候麻木處之。多數走過場的公共藝術項目公示並不真實採納民意,公眾決定權常常被架空、剝奪。另一方面,公眾整體素質、審美水平掣肘,還會反作用於令精品委身遷就平庸。一個嚴重缺乏真正公共藝術人口的社會,難以奢求公共藝術的“好”。
三、創作群體不勝任。當代從事公共藝術的藝術家,大都沒有理想的公共藝術知識結構,一些文化修養較低的雕塑家、畫家客串著公共藝術家。他們是那種強調特立獨行,追求個性的私人色彩濃重的藝術從業者,心理滿足在文人畫家身份的功成名就,絕少公共情懷,帶著農業文明心態,未解公共的新文化意義,隻想通過本人作品楔入社會積累市場影響,顧不得服務公眾,佳作低產,往往長期歉收。
四、創作急迫,過於倉促。一些業內人把公共藝術當“活”,綁定城市決策者或房地產開發急切,可以大量取得資金,逐利者雲集,處處為錢而藝術而暗戰。城市建設是中國改革開放最直觀的成果,公共藝術是城市建設最直接的受益門類,除了建筑,任何藝術門類都沒有像公共藝術那樣獲得如此巨額的城建資金,集中而巨量的需求刺激,讓公共藝術常常批量化產出,精益求精者少。
五、輿情分裂,不好的作品沒壓力。輿論界面對“不好”的公共藝術也還總是見仁見智。明明很丑的雕塑揭出了竟會出來另一派的辯護聲音,平庸的作品於是總能安全地躲在相峙的輿情下不斷涌現。
公眾(人民)本來是公共藝術的法理上的建設主體,但它被抽象到沒有立項權。納稅人被分解成活生生的個體時,誰也不自覺自己出了值得當真的錢,擁有可以當真的發言資格,便拱手讓出表決權,讓輿論去代表(在美國一些州,如果要建造一處公共藝術,除了專家委員會要審定,還得征詢每一個從自家窗口看得見該“藝術”的居民的同意,不簽字意味著不同意,可致一票否決)。電視、報刊、網絡無暇旁顧公共藝術的跟蹤或較真,“不好”的公共藝術得以輕易立足,雜草叢生,也怪輿論剪草不力,更不好的是,很多低品質公共藝術出現時,公眾、輿情多數失語、少數夸贊。竟能造成頗受歡迎的錯覺。
六、“二主”終裁,甲方說了算。某項公共藝術建在誰的地面,誰出的錢,誰才最終決定其主題、形態、風格、體量、材質、朝向甚至取名。把公共藝術當活的藝術家,懂得要緊的是讓“地主”和“財主”滿意。甲方貌似代表公眾,強勢推動不少低俗的定制。(在發達國家,公共藝術建造資金或通過社會募捐。“百分比”法定提取,由專家委員會結合社區代表意志支配,方案可以不受制於甲方,隻對社會的有效監控機制負責)。“不好”的公共藝術不太好在眾目睽睽之下安身。
七、管理機制不健全。中國幾乎沒有公共藝術的職能管理部門。一種“城市雕塑委員會或辦公室”代司其職,一般歸於建設系統。但由於公共藝術的跨界因素,市政、交通、園林、文化、宣傳、街道、校園、企業也可以基於“二主機制”偶爾強力作為,這個常設於多數省市的機構往往處於空轉狀態。更有的城市職能部門,經不起利誘,直接或間接介入公共藝術工程。有的政府性質的考核發放“執業資格証書”,事與願違地給許多能力水平堪憂,但出得起發証前培訓費的人發放了“政府”許可。有的跨界別部門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多數成員經常兼為投標人,他們既是裁判也是運動員,專家身份成了自己攬活的招牌利器而根本沒有代表的中立性、公共性。更重要的是,公共藝術沒有續存管理機制,一經立項,則默認為百年大計,沒有壽命預估而量“命”投入,建成以后疏於養護、維修、揭幕剪彩即開始中衰,每況愈下,讓后來的觀眾隻能面對其舊態。
八、公共藝術精品正面臨全球性枯竭。任何國家都能舉出幾個好或壞的公共藝術個案。整體的情況是歐美發達國家好的公共藝術的總量要多些,非洲、南美洲國家的都會城市出現好的公共藝術的比率最大,甚至超過歐美。而中國是不好的公共藝術比例最高的國家。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啟示我們,公共藝術求好的秘訣就在於控制總量,寧缺毋濫,精益求精。事實上,歐美國家基於社會產出機制調控做到了這一點,非洲南美國家因為資金短缺做到了這一點。由於公共藝術在相對休眠的城市建設中的長期待業,國際上的公共藝術家十分羨慕中國同行的“活源”——美術學院的進修生也不愁沒公共藝術的活干。全球性的情況是,公共藝術的需求劇減,而中國的公共藝術供源無限擴大,世界上的公共藝術家都成中國公共藝術的智庫儲備。但他們往往難解個中深味,不服水土,隻能眼饞中國同行。中國公共藝術創作群得益於某種攘外機制,沒有像建筑界那樣失守自己的壟斷。負面的結果是,一些擁有專業實力的雕塑家,逐漸因為活多作品多而滾雪球一般建立起權威,成了中國各地重要公共藝術項目的主要供源,導致大量的自我重復和地區雷同。
總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這裡進行公共藝術體現的進文化分配,是對七分之一人類的負責。我們有理由呼喚“好”的公共藝術。
□鄒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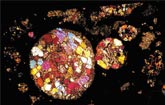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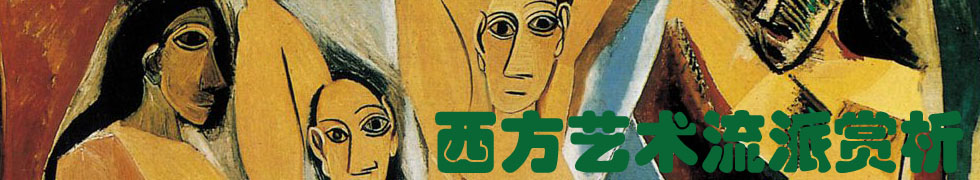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