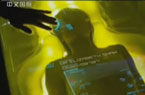李毓芳
我國著名古代都城考古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阿房宮考古隊隊長。1943年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系。在古代都城遺址斷代等方面多有建樹,關於阿房宮遺址考古使她蜚聲海內外。近來,又發現並挖掘秦漢時期世界上最長的古橋遺址——廚城門大橋,引起世人極大關注。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漢杜陵陵園遺址》《漢長安城未央宮》《漢長安城桂宮》《西漢十一陵》《陵寢史話》等。
印象:生來就是干考古的命
來自陝西西安的最新消息,於1995年破土動工、2000年正式運營的原阿房宮景區將被拆除。因為該景區大部分位於正在規劃建設的“阿房宮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控制地帶,為保護這一重要遺址,原人造“景區”被拆除理所當然。阿房宮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去年,國家文物局批准了《阿房宮遺址保護規劃》,規劃將以阿房宮遺址的文物保護為核心,建立一個全方位展現秦文化及秦代歷史風貌的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和城市中央森林公園。
“阿房宮考古遺址公園”的規劃基礎是確定阿房宮遺址范圍,而阿房宮遺址范圍的最終確定,則是阿房宮考古隊歷時6年艱苦野外作業的考古成果。前不久,記者專程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阿房宮考古隊隊長李毓芳。
她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精神、干練、快人快語,說話大嗓門兒,哪像70歲的人呀?幾十年跑野外,風霜雪雨的拍打,人倒顯得年輕。她說話快、走路快、反應快、思維快,到大學講座,大學生提問題多快?學生剛閉嘴,她的回答就頂上了,還不打錛兒,就這麼快。
北京人倒有天津人的性格。原來,李教授是咱天津衛的兒媳婦。老伴兒劉慶柱是天津人,倆人在北京大學考古系是同班同學,畢業后同在考古所工作,結為“考古夫妻”。丈夫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博士生導師,曾任考古研究所所長多年,還是阿房宮考古隊顧問,對阿房宮考古也十分熟悉。
李毓芳常年在西安,去年下半年,她隻回北京3天,匯報工作,完事立馬回西安。過年了,老兩口才回到北京。不等過完正月十五就回西安。干嘛這麼著急?她說,工地開工啦,我得趕緊回去,這個空檔,車票好買啊!
70歲了,還常年工作奔波在考古一線,實在是令人敬佩。
她說她生來就是干考古的命。他們那一屆干考古的學生中,她是唯一的女生。沒辦法,就樂意出野外,有癮!她做了幾十年古代都城考古,多有建樹。讓她名震四海的是阿房宮考古,因為她顛覆了人們的“傳統認識”,沖破重重阻力,顯示了勇敢的科學精神。
關於阿房宮,有許多文獻記載,正史、野史、傳說,還有許多文學描寫。李毓芳說,我們搞考古的,就是直接面對考古實証。要以考古資料為准,不能以文獻為准。文獻是后人寫的,考古資料才是原始的記錄。考古就是重証據,眼見為實,就是還阿房宮的本來面目。
這話說著輕鬆,做起來實在太難。不論酷暑嚴寒,在荒郊野外,一個探方一個探方地做,挖出史上最長的探溝……經過6年艱苦的野外工作,在前殿遺址夯土台基上面,東、西、北三面牆裡都沒有發現秦代文化層和秦代宮殿建筑遺跡。又在北到渭河、南到昆明池北岸、西邊到封河,135平方公裡的范圍內,尋找阿房宮遺址,沒有發現與阿房宮前殿同時期的建筑。原來說的秦始皇上天台、烽火台、磁石門等,經過考古工作,都不是與阿房宮前殿遺址同時代的建筑。上天台,只是一個高台建筑群,戰國時建的,沿用到漢代。傳統上的宮裡能有烽火台嗎?它根本就不是烽火台。磁石門就更不對了,它是個宮殿建筑的形式,根本就不是門,更不是“安檢門”。
根據考古實証,李毓芳得出結論:阿房宮前殿遺址,就是兩千多年以前秦始皇想要修建的阿房宮遺址。阿房宮沒建成,在土台子上沒有發現火燒的痕跡——紅燒土。項羽火燒的是咸陽宮,而不是阿房宮。
說項羽沒有燒阿房宮,不僅在百姓中反響強烈,在考古界也引起震動。之后全國文物工作會議在廣州舉行。當時有兩個專家說沒發現火燒痕跡,是因為農民平整土地時,把紅燒土給拉跑了。有人說了這樣的話,李毓芳睡不著覺了,血壓也升高了。
她說,因為他們是長輩,我尊重他們,但他們脫離考古一線時間太長了,離實踐太遠,說出來的話不合乎常理。我尊重長輩但絕不迷信權威。我不怕你是誰,真理隻有一個。
她所面臨的壓力和困難遠不止這些。比如,西安以前曾搞過一次阿房宮遺址考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10.84平方公裡。李毓芳得出的結論是2.4平方公裡。她寫出阿房宮考古報告報上去了。當地有的領導看到了,說這阿房宮考古,怎麼把阿房宮給搞沒了?下面的工作人員迫於壓力,建議李老師能不能“修改”一下?她把考古報告發給考古網,隻提了一個要求:一個字也別改。結果,隻改了倆標點,全文發表。
這就是李毓芳的性格。
在有些人看來,這可能有點兒“不近人情”。但她唯一忠誠的就是科學,是真理。
她在台灣輔仁大學講座時,有個學生提問:您考古得出這個結論,得到誰承認了?她說我不管誰承認,我隻知道我是通過調查、鑽探、考古,實事求是得出的結論。至於改不改歷史教科書,那不是我管的事。
讓她深感欣慰的是,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編輯出版的最新歷史書《中國通史讀本》已經採用關於阿房宮沒建成、沒被燒的結論。國家文物局已經通過了“關於阿房宮遺址的保護規劃”。確定了遺址范圍,才能確定保護范圍嘛。這等於國家正式承認了她的考古成果。正在規劃建設的阿房宮遺址公園,僅土台子上面的拆遷就涉及4個村子,台子外邊還有呢,這是個不小的工程。“人造景觀”被拆除理所當然,能夠還阿房宮本來面目,我們覺得,多年的付出,值了!
關於阿房宮的讀音
記者:我們上中學或讀古典文學的時候,老師教的發音是阿(e)房宮,您為何主張讀阿(a)房宮?
李毓芳:陝西是塊神奇的土地,不僅地下文物遺存豐富,而且,在民間也是保留中國古代文化比較多的地方,當地人說話,秦調秦腔,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讀音和語法習慣。比如,站直了,他們叫“站端”﹔快跑,他們叫“跑快”﹔環城路叫“繞城路”……
在阿房宮遺址東北邊一公裡的地方,有一個村子叫阿房宮村,這是在宋代以后出現的村子,當地人的發音叫阿(a)房宮村,簡稱阿房村,不說阿(e)房村。而且,旁、方、房,在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讀音,屬同音字。我想,這種民間口頭語言的世代相傳,是有根有據的,顯示了古代漢語讀音的生命力,應該入鄉隨俗,跟著陝西的農民叫阿(a)房宮。所以,我一直叫阿(a)房宮。至於讀者採用哪種讀音,自便吧。我只是說出自己的見解,這是我的責任和義務。
為什麼說阿房宮沒建成
記者:您得出阿房宮沒建成的結論,有充分的考古實証,但我想請您用通俗的語言,告訴讀者為什麼說阿房宮沒建成?
李毓芳:先給讀者普及一點兒考古知識吧。古代建房子跟現在不一樣,現在是先圍一圈兒牆,在牆裡蓋房子。但是在戰國、秦朝是先建主殿,然后再建配殿、宮城,最后再建整個大城。秦始皇為什麼要建阿房宮?當時他嫌咸陽城太擠、太小,要在“渭河以南上林苑”建阿房宮。為什麼選這兒?上林苑在戰國時期就是國家公園呀,面積非常大,后來漢武帝又給擴大了,有2000平方公裡,風景也優美。在阿房宮沒有修建以前,渭河以南整個一大片地方已經有了很多建筑,這些建筑是上林苑的一部分。秦始皇在上林苑裡面找了一個高地,向西南發展,欲建阿房宮。
記者:我明白考古隊為什麼先從阿房宮前殿遺址開始工作了,前殿是第一個建的嘛。那阿房宮為什麼沒建成呢?
李毓芳:因為時間太短啊!秦始皇35年始建阿房宮,37年他就猝死途中。修阿房宮的35萬人都調去修驪山陵墓了。秦二世在公元前209年4月重修阿房宮,之后陳勝吳廣起義,第三年秦二世就自殺了,滿打滿算不過4年時間,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沒有建成宮殿是可以理解的。
司馬遷的《史記》不愧是“史家之絕唱”,寫得很清楚:“先建前殿阿房”。司馬遷就住在漢長安城,離這個土台子很近,騎馬半小時,他完全可能到阿房宮去看看。所以他記載:“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他說阿房宮沒有建成,如果建成了還要起一個美好的名字,因為沒有建成,而在“阿房”這兒建的,所以天下人稱阿房宮。《漢書·五行志》裡寫:“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也是真實的記錄。
實証為本,考古調查非常重要
記者:阿房宮沒建成,火燒就沒有可能了。但是,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描繪深入人心,怎麼會沒燒呢?
李毓芳: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考古以實証為本。在土台子上我沒有發現火燒的痕跡呀。沒有紅燒土,怎麼能說項羽火燒了阿房宮?考古實証表明,項羽火燒的是咸陽宮,而不是阿房宮。許多人說我給項羽平反了。我們在咸陽發掘宮殿,在一、二、三號宮殿建筑遺址發現全部被火燒了,牆被燒成黑色的,柱子的灰都是黑的,土坯燒成跟磚似的,瓦片都燒紅了,那是被項羽的大火燒的。“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項羽進咸陽搞的是“三光”燒光、搶光、殺光。
記者:您說項羽沒燒阿房宮,不僅在百姓中反響強烈,在考古界也引起震動,有專家質疑,說紅燒土被農民平整土地給拉跑了……
李毓芳:我手裡有充分的考古証據,心裡有根。實証為本,考古調查也非常重要!我回來就趕緊訪查,誰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業學大寨”的時候是生產隊長?找到兩個,聚駕庄一個,趙家堡村一個。正好央視“發現之旅”來拍電視,他們就把當時的情況說了。平整土地,沒往下邊拉土。只是從北邊平高墊低,往台子的南部墊了墊。另外在土台子西邊剛拉了兩車土,西安市就來人了,說這裡的土不能動,要保護。從那以后,就再沒有動過土。這是最重要的人証。再說,農民怎麼可能隻把秦代的紅燒土拉走,而它上面漢代堆積層的土和瓦片不動呢?
當時,我們所考古科技中心副主任到台子上取了土樣,拿回北京的實驗室做分析。結果,沒有發現被火燒過的証據,也就是說台子沒有被火燒過。我的心就非常踏實了。后來,考古圈兒裡再沒人質疑這個問題了。
面對壓力堅守科學精神和勇氣
記者:您說考古就是要還原歷史本來面目,但這個“還原”太難了,有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講真話也不容易呀。
李毓芳:我老伴兒劉慶柱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考古學的使命就是尊重歷史事實,通過考古科學研究成果,還歷史以原貌,恢復我們真實的、科學的“歷史記憶”,糾正不正確、不准確的“人類記憶”。這是我們共同的觀點。但糾正這些東西,太難了。比如,當地有一處所謂的阿房宮景觀,裡面有大量火燒阿房宮的“資料”與“情景”。開始,“老板”對我們非常熱情,說別住農民的房子,住我這裡吧,條件好。我們當然沒去。結論一出來,沒發現火燒痕跡,他態度立馬變了,冰火兩重天,說影響他生意了……
記者:聽說來自“業內”的壓力也不小?
李毓芳:起初,當地文物部門的一些人也不相信。說哪兒哪兒還有土台子呢,我把這些都挖完了,在135平方公裡的范圍內,沒發現與阿房宮同時期的建筑。我們挖的最長的探溝62米長、4米寬,這在中國考古史上,可能是最長的探溝了。像這樣的探溝,挖了幾十條,還有高密度的洛陽鏟鑽探,20厘米一個探眼,做得相當精細了,就怕有所遺漏。阿房宮考古報告報上去了。當地有的領導看到了,說這阿房宮考古隊,怎麼把阿房宮給搞沒了?
西安以前曾搞過一次阿房宮遺址考古工作,他們得出的結論是10.84平方公裡。我得出的結論是2.4平方公裡,這差遠了!下面的人很為難,說李老師這個稿子得改。要把肯定、清晰、明確的結論改成模糊的。他們頂不住壓力。你說,我能不生氣嗎?我血壓能不高嗎?你愛怎麼改就怎麼改吧。我把原稿給考古網發去了,說你們不能給我改一個字。他們隻改了兩個標點符號就發了。
知錯必改,理所當然。可是,要改也難。就說博物館裡的那個玉杯吧,是戰國上林苑的東西,不是阿房宮遺物。阿房宮沒建成,怎麼會有玉杯呢?大殿還沒建成,先弄個玉杯擺上,那可能嗎?玉杯出土的位置跟阿房宮一點兒關系都沒有。我為這個著急上火,明明不是阿房宮的東西,已經証實了的,怎麼還不把解說詞改過來?我跟阿房宮沒冤沒仇,我憑什麼跟它過不去?我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也不影響我的工資。但是,我們要尊重實証、尊重科學嘛!
野外考古以苦為樂上了癮
記者:您這麼大年紀了,放著北京舒適的家不呆,常年跑野外,圖什麼呀?
李毓芳:跟你說實話吧,圖過癮!幾十年干考古,上癮了。苦是苦,但苦中有樂,其樂無窮。我在家坐不住,就愛往野外跑。一是願意過考古的癮﹔二是我不樂意做飯。租農民的房子住,請當地人做飯,我就愛吃農家飯。蘿卜大白菜,特好吃。我身體這麼健康,與長期在工地有很大關系,空氣好,飯菜香,污染少呀。一天要走很多路,也是鍛煉。
其實,我有一條傷腿,左腿半月板撕裂。一到冬天腿就冒涼氣,弄個皮護膝,一瘸一拐跑工地。做西漢帝陵調查時,每天爬坡上?,腿累得不能打彎兒,得掄著腿上床。我一到工地就來精神,看到有老農,跟他們聊天,一聽他們說話的聲音腔調,哎喲,感覺那個親切啊!考古就是我的幸福,能到考古工地去,就是我最大的快樂!
記者:我有體會,西安的冬天很冷,聽說那裡還經常停電?
李毓芳:遭遇停電,我在農村幾十年,都習慣了。原先是澆水澆地停電多,要保証農業用電。后來,用電量大了,老是掉閘。一停電,我們用的電暖氣就冰涼,租農民的房子,不敢生火呀,怕把人家屋子熏黑了。那個冷呀,寒氣往骨頭縫兒裡鑽。點著蠟燭,圍著大棉被坐在床上。一個星期停兩次電,就算正常。這次回北京之前,又停兩次電。有時修得快點兒,有時就很慢,夜裡12點也不來電。凍得人躺不下,隻能圍著被子坐著。
記者:為了考古,您一個女同志常年出野外,能行嗎?
李毓芳:有人認為女同志干不了野外考古。我偏要讓他們看看,我干了幾十年,而且干得挺好。那些年我住過牲口棚,住過農民的柴草房,弄得身上都是跳蚤。我還親眼看見過老鼠怎麼偷雞蛋呢!那個年代吃什麼?哪有菜呀?挖點兒野菜,挖點兒農民的苜蓿,咸菜就餑餑,我都快成“王寶釧”了。糧食定量不夠吃的,肚子裡沒有油水呀,就買肉聯廠的湯油,是有問題的豬肉在大鍋裡熬的油,現在想起來都要吐,可那時是美味兒!一次買一塑料桶,能吃半年。
最對不起女兒和家人
記者:您在古代都城考古方面,屢有重大發現,建樹頗多,這些業績的取得,您最感激的人是誰?
李毓芳:我最反感說套話。說實話,我最感恩的人就是家裡的親人。沒有他們的付出和支持,哪有我和老伴兒的成果?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女兒。我女兒1970年出生,剛生下來擱在我母親家,為了繼續跑野外,我就吃回奶藥回奶。其實我也心疼,女兒沒吃過母親一口奶,這個決心也不好下呀!剛生完孩子,我就要求做絕育手術。醫生說那不行,不給我做。我女兒很自立很懂事,她上學、工作、談戀愛、結婚,都沒讓我們操心。她生小孩兒,我得好好表現表現。我頭天先住到在北大的同學家,她家離醫院近呀,第二天一大早,我到醫院了。女兒看見我特別激動,您這麼早就來了,她剖腹產,我得給她坐鎮呀。盡母親的義務,我的感覺很幸福。
我非常感恩家人的幫助和支持,感謝兩邊的老人,都沒讓我們照顧,主要靠兄弟姐妹替我們盡孝。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力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最大支持吧。我們抽空就到天津去,兩個弟弟和弟媳為我們家付出太多了,我們對他們感恩不盡……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