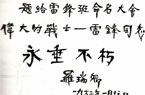晉陸機雲:“存形莫善於畫”。繪畫作為一門造型藝術,形象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隻有形象,哪怕形象刻畫得再逼真,也不能稱其為藝術。繪畫不僅要表現物象的自然生意,還應該凸顯畫家的性情。
漢朝王延壽在《魯靈光殿賦》中對於“圖畫天地”,提出“隨色象類,曲得其情”的要求,反映出繪畫對形神兼備的重視。此或為南朝謝赫 “隨類賦彩”、“氣韻生動”理論之源。但最早的形神論多應用於人物畫之中,只是到后來文人畫漸熾,形神論逐漸擴展到山水、花鳥畫領域。可以說中國繪畫是以“傳神論”為主的意象思維方式作為審美需要的,就審美本體而論,這種寫意性為主的創作觀一直是中國文人繪畫的傳統。
就花鳥畫而言,花鳥畫家並不只是滿足於對客觀花鳥形象的簡單模擬,而是以自然中的景物生靈為參照,借助筆墨“托物言志,托物言情”,這是建立在對民族文化、自然物象深刻體驗觀察之上的一種高度凝練的情感表達,宋鄧椿說:
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而。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眾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隻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
可見, 人物畫要求形神兼備,山水、花鳥亦皆有精神。繪畫的作用就是要為天地之間的萬物傳神,而不單是摹寫其形跡。蘇軾詩雲:“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中國花鳥畫一直都沿著“寫生”與“傳神”兩個脈絡分分和和地發展。“寫生”並不是照搬原樣,“傳神”也不是空洞無物的玄談,而是立足於自然與人息息相通之整體,對物象作出全面、本質的把握。唐代韓干畫馬經常寫生,曾語玄宗:“陛下內廄之馬皆臣師也”,故其下筆如有神助,馬的精神、形態甚至於馬的性格畢現。五代的黃荃也很重視寫生,嘗自養鷹禽,以觀其生態。所以他的寫生珍禽圖形神兼備、栩栩如生,如果沒有畫家長期深入的觀察、寫生實踐,對象的神態也就很難表現的活靈活現。所以徐悲鴻先生提出寫生時要“盡精微”,就是畫家要善於觀察抓住必要的細節進行刻畫,方能“致廣大”,才能使作品能感染人。“傳神”不是不要形象,也是在形象確立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主觀情緒進一步挖掘物象生動的內在氣質。清鄒一桂在《小山畫譜》中提出“活”和“脫”兩字訣:
活者,生動也。用意用筆用色,一一生動,方可謂之寫生。脫者,筆墨醒透,則畫與紙絹離,非色墨跳脫之謂。脫仍是活意,花如欲語,禽如欲飛,石必崚嶒,樹必挺拔。觀者但見花鳥樹石而不見紙絹,斯真脫矣,斯真畫矣。
“活”、“脫”講的即是要傳寫自然萬物之精神。清代惲南田的花鳥作品,形色逼真,格調高雅,技法成熟而不俗膩,形象逼真然而不落甜俗。所以離開了形象,“神”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早在戰國時,荀況就在其《荀子•天論》中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理論,闡發了神對於形的依附關系。東晉顧愷之繼而提出“以形寫神”的理論,認為傳神必須建立在對客觀形體的描寫基礎之上。形存則神存,形是神的基礎,離開形,則無以談神。遺貌取神只是要求在某種程度上從形象和色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對形和色大膽取舍夸張,以達到神似之目的。宋陳去非論畫雲:“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作畫一如相馬,要見其內在生命精神,而不可拘拘於外在之形跡。蘇軾雲:“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隻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倦。”元末明初畫家王紱在《書畫傳習錄》中解釋倪雲林的“不求形似”雲:“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倪雲林畫跋原文如下:
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與蘆,仆亦不能強辯為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為求全其自然生意與胸中之逸氣,畫不工即退而求其次,並非不求似,而是隨意取舍,不盡求似,這即是中國所特有的意象造型。意象不同於西方的具象與抽象,而是在自然物象與作者主體情感的交流與通融之中,使主體情感物化,客觀物象我化的現象。故而繪畫的形與神隻在輕重取舍的程度尚有所差別,不存在絕對獨尚其中一面,而盡棄另一面之舉。
尤其是文人畫極重“逸氣”,提出鄙工取妙的形神觀,如清盛大士雲:士人之畫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畫工而未必盡妙。故與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但文人畫之“工”是不“必求”的,而非“必不”求,只是在工與妙兩相抵牾之時,更要重其內在的神質而已。然而文人繪畫直抒胸臆的標榜,又往往將一部分貧學畫家引向極端。由於這些畫家本身不具備扎實的基本功,文人繪畫鄙工取意的觀點便成為他們信手涂鴉的理論大旗。文人畫風漸漸向大寫意發展的過程中,很多畫家盲目任誕狂怪,不肯在造型的基本功上下苦功夫,把“放縱”等同於“放鬆”,畫學也漸導偏枯。這一點在傳統的花鳥畫中尤為突出。因為中國人物畫在清代以前一直延續勾描覆染的嚴謹套路,雖也出現象石恪、梁楷等的減筆畫家,但不在多數﹔由於山水畫始終保持著程式的延續性,它的大寫意化進程趨緩﹔唯獨花鳥,其取材和形式都比較靈活多樣,其創作的隨意性也尤為突出。因而,繼青藤、八大之后,又有揚州畫派興起,對大寫意畫風樂此不疲。但畢竟他們中大多還是比較有文化素養的支撐,其間的書卷氣息猶不失可觀。而今天的寫意花鳥畫壇,卻充斥一股促黑霸氣的風習。究其因,也主要是他們缺少學養和對自然形象的體察,而徑接學習古代大寫意的樣式。本身缺少因文化積澱所形成的氣韻,又不肯執著於物象的形跡,由是而形神兩俱亡矣。
另外,在當代很多畫家的花鳥畫中,增加了一些形式構成的因素。形式構成的 “形”固然與傳統形神論中所言之形有所差別。但如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不過是創作者對客觀物象的形進行了理性的構置,或使形象在原有基礎上進行適當夸張變形來增添其意味性。這樣的作品關鍵在於構成形式的合理性與創作主體精神的協調,而對於自然物象形體缺乏嚴謹性問題是可以不作計較的。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