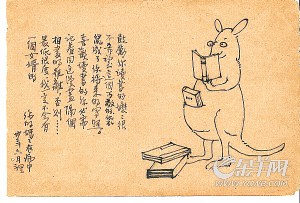亲爱的慰梅和正清:
读着你们八月份最后一封信,使我热泪盈眶地再次认识到你们对我们所有这些人不变的深情。我赶巧生病了,或者说由于多日在厨房里奋斗使我头痛如裂,只得卧床休息。老金把你们的信从城里带来给我,我刚读了第一段,泪水就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反应是:慰梅还是那个慰梅,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无法表达,只能傻子似地在我的枕头上哭成一团。
老金这时走进已经暗下来的屋子,使事情更加叫人心烦意乱。他先是说些不相干的事,然后便说到那最让人绝望的问题———即必须立即做出决定,教育部已命令我们迁出云南,然后就谈到了我们尴尬的财政状况。
你们这封信到来时正是中秋节前一天,天气开始转冷,空中弥漫越来越多的秋日泛光,景色迷人,花香四溢———那些久以忘却的美好时光。每个晨昏,阳光从奇诡的角度射来,触碰着我们对静谧和美依然敏锐的神经,而这一切都混杂在眼前这个满是灾难的世界里。偏偏佳节将临,多像是对逻辑的讽刺啊。别让老金看到这句。
老金无意中听到这一句,正在他屋里格格地笑,说把这几个词放在一起毫无意义。不是我要争辩,逻辑这个词就应当像别的词一样被用得轻松些,而不要像他那样,像个守财奴似地把它包起来。老金正在过他的暑假,所以上个月跟我们一起住在乡下。更准确地说,他是和其他西南联大的教授一样,在这个间隙中“无宿舍”。他们称之为假期,不用上课,却为马上要迁到四川去而苦恼、焦虑。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编者注:就是龙头村),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佣人房,因为不能保证这几个月都能用上佣人。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于一种可笑的窘境之中。所有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编者注:当时龙头村建这种小房的还有李济、钱端升等人),高兴地互相指出各自特别啰嗦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致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于每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蔽风雨”———这是中国的经典定义,你们想必听过思成的讲演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住进了这所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为舒适。但看来除非有你们来访,否则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等你下次来信时,我也许已不在这所房子、甚至不在这个省里了,因为我们将乘硬座长途汽车去多山的贵州,再到四川。
爱你的:菲丽丝(林徽因的英文名)
1940年9月20日 昆明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