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美院丨范迪安:世紀的大書
值此中央美術學院建校100周年,“悲鴻生命——徐悲鴻藝術大展”舉辦之際,謹以多年前寫就但未刊行的一文向老校長致敬。
——作者按
檢視一個世紀美術文化的風雲變幻,梳理百年中國美術的豐富篇章,成為當下美術學界的熱點。但是,無論是研究、撰述20世紀中國油畫和中國畫,還是研究、撰述百年來的美術思想和美術教育發展歷程,都繞不開徐悲鴻先生和他的藝術。先生所處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但先生的藝術遺產卻穿越時代,駐落在我們向歷史追尋的目光面前。這份遺產是一本世紀的大書。
作為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一代藝術家,徐悲鴻對中國美術的現代取向有清醒的文化認識。“現代”這個概念在徐悲鴻那裡,已不單純是某種美術樣式的指稱,而更大意義上是對一種美術新質的憧憬和構想。他在向西方藝術學習的過程中,所涉獵和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歐洲文藝復興到近代的繪畫,但他在認識上卻從西方美術遺產中找到了中國美術現代進程中所需要的“現代”內涵,那就是對社會現實的關切和對普通人的關注。20世紀前半葉中國社會現實的種種沉疴積弊激生出他強烈的憂患意識,在他最初的藝術中就隱隱透露出來。在對西方藝術深入考察和對現實生活深切體驗后,他的作品更加集中地表現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意識與“救彼蒼生起”的悲天憫人情懷。古往今來多少畫家也感喟世態與人生,他們畫的主要是避世的山水家園或幾枝寂寞花鳥,而徐悲鴻落筆驚劃長夜,塑就了一批不屈不撓的民生群像,從而使中國美術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的“現代”作品。

20世紀30年代,徐悲鴻攝於南京工作室(創作《田橫五百士》)
20世紀的中國畫家都有創作“大畫”的理想。展開寬闊的畫布,或許更能夠產生超越性的暇想和興奮。在中國油畫剛剛起步的年代,徐悲鴻大筆揮就的《徯我后》、《田橫五百士》是何等地令國人為之振奮!從形態上看,可以說那是他對倫勃朗《夜巡》、藉裡柯《梅杜薩之筱》、德拉克洛瓦《希阿島屠殺》等歐洲經典巨作的致敬。他曾經被那些史詩般的大畫所激動,稱嘆其“不愧杰作”,但是,一旦自己經營巨構,他的關切便落到了中國的“人”與“人生”上,落到了時代的“命運”上,從而為中國油畫開啟了“大畫”先河。或許可以說,后來中國畫家的“大畫”意識,正是從徐悲鴻那裡繼承過來的,那是一代畫家將自我生命與民眾生存現實聯系起來的藝術敘事和精神寄托。

1941年攝於重慶沙坪壩,前排右起為廖靜文、徐悲鴻、張葳、郁風,后排左一為張安治,后排右一為黃苗子
在時代風雲的變幻中直面人生,以理性的語言去探索人的生存價值,用藝術家的良知光芒照澈幽昧的思想長夜,在每一個形象塑造和每一筆色塊結構中寄注寬闊的人生抱負,是徐悲鴻藝術魅力經久不衰的真正原因。他認為:“為藝術之源有二,曰造物,曰生活,感於造物者,刊劃摹擬,傾向於美……探索生活蘊秘者輒以藝術為作用,刊劃宏願,啟迪社會……”從他的作品內涵來看,他重“宏願”甚於“摹擬”,重“啟迪”超過“得美”。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理想而理想容易受挫折、渴望人生而人生經常遭困頓的時代,他藝術創造的靈感不能不浸染著深刻的憂思。他的作品至今仍然感人,正是因為他沉郁的思想和情懷在筆下飽滿地釋放和流泄出來,從內在生的命力撐持起畫面雄強的結構。這種藝術風格承擔起了表現豐富的現實社會生活的文化責任,充滿了創造主體的精神力量,並和他那一代畫家的作品匯成20世紀中國美術發展的主流,贏得了社會和歷史的承認。

20世紀40年代徐悲鴻創作飛鷹圖
畫家不善言辭是一種傳統,因此中國畫史上留下的長篇論斷少而精辟語錄多。徐悲鴻學兼中西、博採諸長,在藝術實踐中產生了許多深邃的見解,從著述、演講、題跋等方面均可看到,成為“多管齊下”的一代宗師。在他的著述中,尤以1918年所作的《中國畫改良論》為精辟。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採入者融之”,這在當時的畫壇堪稱振聾發聵,在今天讀來仍讓人感嘆不已。對於20世紀中國畫來說,“守”什麼、“繼”什麼、“改”什麼、“增”什麼,都是尖銳的挑問和具體的課題,一個“融” 字,更是體現了一代先賢在中西藝術交匯、矛盾碰撞下的文化選擇。可以說,這既是青年徐悲鴻在文化變革大潮中的個人倡導,也是20世紀中國畫企盼時代變革的整體心聲。徐悲鴻一方面堅持批判中國畫創作在思想內容上的封建性和局限性,站在論爭的前沿,一方面積極弘揚中國畫藝術傳統的精華﹔在經過由中而西、由西而中的藝術經歷后,他堅定地走上了融寫實手法於水墨語言的中西融合道路。他的作品既體現出造型上的嚴謹,又不失民族繪畫特有的氣韻與意境,筆墨質朴蒼勁,內蘊儒雅,卓成一家。特別是他的人物畫,以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神形兼備的形象開拓了中國畫創作的新領域。對於民族傳統藝術,沒有繼承就沒有弘揚,沒有革新也談不上弘揚。徐悲鴻在中國畫方面的改革探索鋒芒和大量成功的作品為后來許多藝術家繼續創新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為推進中國畫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20世紀50年代初,徐悲鴻創作油畫《毛主席在人民心中》
實際上,徐悲鴻提倡的“融”,還不僅僅在於“以西融中”,同時也有相當的“以中融西”的內涵。畫史對徐悲鴻藝術的研究,多側重於前者而忽視后者,而觀察他的素描和油畫,在美學趣味和表現手法上一直帶有中國畫的特性,到后來越來越多地具有探索民族審美內涵的趨勢。他在傳統藝術研究中形成的修養,已潛在地滲透在他的油畫作品中,那就是畫面結構更加闊略、舒展,色彩更多有整體的韻調。他從南洋陸路歸來,經喜馬拉雅山所畫的油畫風景和后來的《庭院》等作品,已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民族藝術的特質。中國油畫家畫了多年油畫之后,整體上在1940年代開始有了對“中國油畫”的自覺追求。這一方面也是對傳統藝術再認識的結果,一方面也是地域性景物風情的啟發。仔細體味徐悲鴻后期的油畫,不難感受到他的畫風已體現出更深沉的民族藝術文脈。

徐悲鴻創作魯迅與瞿秋白
20世紀上半葉中國藝術家群星燦爛,他們的人生經歷比起當代人要富有色彩,甚至近於傳奇,他們的創造力在社會動蕩的局勢中也更加蓬勃。他們身影匆忙,在歷史夜空卻閃爍錚亮。有一個事實特別富有意味,那就是他們的職業選擇。在現代文學史上的諸位先賢,雖學富五車,寫作熱情旺盛,但大多從事報刊雜志的編輯工作,從郭沫若、魯迅到茅盾、巴金,無一例外﹔而現代美術史上的眾多名家,則大多選擇美術教育為自己的事業歸屬。實際上,文學家主編輯和美術家當教師貌異質同,都是以傳播思想和知識、發現和培養人才作為價值取向。這兩種不同的職業同樣體現了中國藝術家們身上與生俱來的知識分子情結,那就是樂為人師,甘為人梯。與徐悲鴻的人生道路最為緊密相連的是美術教育事業,這可能受到他的啟蒙先生蔡元培的影響,認為教育既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人類文化傳道與啟迪創造的最重要方式。他從青年時代起就矢志於美術教育,從1918年被蔡元培聘為北大畫法研究會導師開始,到1928年與田漢、歐陽予情共創上海南國藝術學院並任美術系主任,然后到北平大學藝術學院、中大的南京時期和重慶時期,再到抗戰勝利后的國立北平藝專和1949年以后的中央美術學院,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熱情和藝術才華都傾注在美術教育事業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1年,徐悲鴻為戰斗英雄畫像
一如整個近現代中國教育體制的根本變革,20世紀之初興起的中國現代美術教育一開始就面臨著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多種選擇與分歧。徐悲鴻以清醒的認識和全面的修養,提出通過吸收西方近現代美術學院教育的優長建立中國美術教育體系。這種講究科學和理性精神的主張和他的藝術思想一樣,是根據中國教育的實際需要出發,符合藝術教育規律的道路。在他主持教學的學校,逐步建立起新型的美術教育結構。他長期堅持在教學第一線,探索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他十分重視素描教學,強調素描是造型藝術的基礎,具有培養正確的觀察方法和表現技巧的意義。在素描教學中提倡“盡精微、致廣大”,要求研究三度空間造型的規律,又要求從復雜的對象中加以取舍和概括,使作品具有扎實功底和文化品位。他的大量素描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已超出了“寫生”和“習作”的意義,成為現代美術遺產中具有獨立欣賞和研究價值的藝術品。經過徐悲鴻和他的同輩許多優秀美術教育家的努力,到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美術教育從引進西學西法到建立自己的教學體系,進入了學科結構和教學模式都逐步完善的歷史階段。

1953年暑期油畫教師進修班合影。前排左起 江豐、王式廓、徐悲鴻、戴澤。后排左起 曹思明、庄子曼、馮法祀、倪貽德、李宗津
徐悲鴻在美術教育上的淳淳善誘和有效方法,影響了許多學生,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美術家和美術教育家。他更以廣納天下賢士於藝術園圃的寬闊胸懷,珍惜人才,善於發現人才。他曾傾力相助過許多遭遇困難的學子,為他們成才提供了條件﹔他也不計社會地位的高低和學派觀點的差異,團結了許多忠誠於民族文化事業、富有創造個性的藝術家,使他們成為美術教育的薪火傳人。譬如,20年代他不羈時俗聘請民間畫家齊白石到北大任教,40年代他不畏反動政治勢力,在重慶撰文介紹解放區的木刻,推崇延安的木刻家古元。在擔任國立北平藝專校長時期,他團結了包括吳作人、葉淺予、蔣兆和、李樺、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禪等一大批優秀的藝術家,為迎接新中國美術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人才基礎。在徐悲鴻去世后的許多年裡,他的作品和關於教育的著述不斷出版並在海內外廣為傳播,成為美術教育寶貴的思想資源。美術界在回顧和總結他的成就時,愈發認識到他的美術教育思想和實踐的體系性價值,他的學術遺產在新中國幾十年來美術教育領域仍然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徐悲鴻最后一次主持教學活動
20世紀中國美術還有一個有意味的現象,那就是前所未有的畫家之旅。中國美術的古訓要求畫家“行萬裡路”,20世紀中國畫家不僅僅在國內行路,而且穿越文化邊界,行走到世界各地,這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這段“世紀之旅”可以寫成一部專史,其中記載著中國畫家求學海外生涯的艱難和困苦,反映出他們對世界藝術的認識、體察和選擇方式,還反映出中國美術與世界美術的相互關系。在這支遠行的隊伍中,徐悲鴻的身影又是獨特的。他先是以“朝聖者”的虔誠跋涉歐陸,寒窗求索西學之經,繼而帶著“傳播者”的使命奔走各地各國,為弘揚民族藝術不遺余力,在溝通中西、宣傳中國藝術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曾在批判中國傳統繪畫的不足與弊端之時致力於西方美術的引進,期盼以西方科學理性意識土壤中生發的合理因素校正中國繪畫的頹敗之勢,其中心旨意乃是要使中國新美術能在“世界關系”中立住自己的陣腳。他的“拿來”是為了“拿出”。他高度評價過西方古典到現代的寫實主義繪畫觀念和技法,把它們吸收進中國繪畫肌體,借以改造傳統繪畫﹔但他在國外舉辦中國藝術展覽之時,則努力介紹中國傳統藝術的瑰寶和在20世紀的發展。他一生行旅匆匆,風塵仆仆,一方面以“學術者,天下之公器”的敬業精神,作不懈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為中國文化立言立心。他的藝術創造、教育教學和眾多的社會活動,都是為了謀求中國文化精神的實現與宏揚。在20世紀中西藝術交流中,他是一座寬闊的橋梁。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徐悲鴻先生留給后人的,遠不止於難以計數的作品實物,還有他的人生價值和精神風范。世紀回首,有興奮也有困惑,時代變化如此之快,藝術的老問題還沒有解決,新問題已層出不窮,新問題又聯結著老問題,這是因為中國美術是一個開放的發展進程。隻有不斷地重覽歷史,從先賢的藝術印跡中感受永恆的溫澤,才能更加清晰前瞻的目光。在徐悲鴻先生這本世紀的大書中,充滿著激勵勇氣、獲得真知、取之不盡的寶藏。
1995年5月於北京

1948年,徐悲鴻與齊白石、吳作人、李樺、攝於北京。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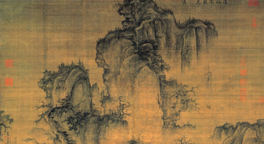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