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劉蟾 整理 本報記者 龔丹韻
作為著名畫家劉海粟的小女兒,劉蟾小時候並未學畫。雖然上班后在父親身邊得到一些指點,但系統地學畫卻在51歲以后。彼時父親已經去世,但他留 下的精神財富,讓劉蟾至今記憶猶新。採訪時,她娓娓道來自己與父親的故事,大半天都未談到學畫,以至於幾次問她:“那您是怎樣學畫的?”她都報以微笑: “聽我慢慢說。”
家書
與古為新、蟬蛻龍變。辛酉孟夏,書給蟾兒。劉海粟年方八六。
解讀
當時父親86歲,我還在父親身邊練習畫畫。他鼓勵我創新,畫畫膽子要大,格局要大。甚至說:“你要像我劉海粟的女兒,畫畫不能縮縮縮。”可惜的是,我后來還是畫傳統畫多一點,我的性格可能還是不夠膽大。 (劉蟾)
家訓
自力更生、自強不息。
人物小傳
劉海粟(1896-1994),字季芳,號海翁。漢族,江蘇常州人。現代杰出畫家、美術教育家。1912年與烏始光、張聿光等創辦上海圖畫美術 院,后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校長。1949年后任南京藝術學院院長。早年習油畫,蒼古沉雄。兼作國畫,線條有鋼筋鐵骨之力。后潛心於潑墨法,筆飛墨 舞,氣魄過人。晚年運用潑彩法,色彩絢麗,氣格雄渾。歷任南京藝術學院名譽院長、教授,上海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1981年被聘為意 大利國家藝術院名譽院士,並被授予金質獎章。
1918年劉海粟起草《野外寫生團規則》,親自帶領學生到杭州西湖寫生,打破了關門畫畫的傳統教學規范﹔1919年響應蔡元培之號召,在美專招 收女生,開中國男女同校之先河。他在現代美術教育史上創造的數個“第一”,至今仍有意義,而且這種意義已超出美術史本身,從一個側面展示出中國社會告別傳 統走向現代的曲折裡程。
父親很威嚴
有種不怒而威的氣場
我生於1949年,是家中最小的女兒。從小父親很忙,時常上海和無錫兩地跑。我常常見不到他。家裡雇了佣工和保姆。父親回來,佣工就幫父親磨墨。偶爾我們會在邊上看。有時候他為油畫打框,我也手忙腳亂幫一下。
父親很威嚴。坐在那裡不出聲,讓人害怕。其實他從來沒有罵過我們,但就是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氣場。我們幾個孩子從小就怕父親。平時在家裡很皮,走 廊上放了一個陶馬古董,我們就騎在上面玩。但是大家一聽到大門鑰匙在轉的聲音,就知道父親回家了,連忙跑到樓上躲起來。當時小學裡有學習小組,課后幾個人 一起做作業,每次輪到小組到我家來做作業,同學們都怕我父親,不敢哇哇吵。其實父親沒看著我們,就是很有威嚴。
我們家很講規矩,見到長輩要叫人。父親時常有客人或學生上門。他們在客廳,我們幾個孩子都不聲不響,走樓梯輕手輕腳。吃飯也不敢出聲。父親不拿 起筷子,我們不能先吃。尤其是有客人來的時候,先要把菜給客人吃,隨后幾個孩子才分到一些。正式請客有一桌子菜的話,孩子都不上桌。
父親從小就主張,要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父親當年就是靠自力更生,來上海創辦美專。1929年,經蔡元培先生申請經費,父親可以去法國進行美術 考察,他帶上了我的大哥劉虎。父親在法國很用功,把大哥送到寄宿學校念書。大哥從小一個人在法國,自己生活。他念書很好,考上很好的學校,此后沒有隨父親 回國,長大后在聯合國工作,一輩子都靠自己。
父親常常以大哥為榮。有時候,他會把大哥小時候的畫拿出來給我們看,說:“你看,這是虎兒畫的。”
小時候,母親讓我學鋼琴,我其實坐不住。同學會在窗外叫我的名字,讓我出去一起玩。我哥哥看見就說:“不要亂叫,她要彈鋼琴,叫她干嘛!”我每 天在客廳裡彈鋼琴,心裡一直不耐煩。媽媽常說:“我們賺錢也很辛苦,出了錢給你學,你要好好學。”仿佛我是為了他們在彈,聽著聽著我就流淚,覺得委屈。
但是每當父親回家,他在客廳畫畫,無形中就管住了我。他其實知道我坐不住,就對我說:“傅雷教育孩子是打傅聰,我不贊成他的教育方法,這要靠自覺。你喜歡你自會好好學,你不喜歡打也沒用。”
當時我年紀小,聽不懂。隻覺得坐在那裡很冤枉,淚水直往下掉。
蝸牛爬到臉上
他笑說這是法式蝸牛
被打成“右派”后,父親中風,右半邊身子癱瘓。母親始終沒有放棄,與父親共同度過艱難困苦。生病期間,父親的手無法畫畫了,但是他對畫畫的愛好從來沒有放棄過。他讓母親把畫挂起來給他看,繼續琢磨研究。
那時候家裡氣氛凝重,幾乎沒有聲音。父親從一級教授降到四級,各方面待遇下降,但他需要補充營養,家裡看上去排場很大,開銷也大,一棟洋房要付 房租,當時一個月工資也交不起房租。我母親很不容易,她哥哥在香港,寄來很多糧油糖,她就拿這些東西去換錢,給父親買補品。那時候我讀書也受到影響,老被 人說出身不好,平時夾著尾巴做人,一般同學不搭理我。
“右派”脫帽后,父親心情好了,病也好了,又要出去跑,出去寫生。我又看不到父親了。之前母親一直幫父親推拿癱瘓的半邊身子,父親很堅強,病好了以后,不僅可以畫,可以走,還活到了98歲,你說是不是一個奇跡?
我初中畢業,家裡過了幾年平平安安的日子。但是我考高中還是受父親影響,不能上太好的學校,隻能到職業學校,學紡織印染。錄取后的一天,班主任 來家訪。我們家很洋派,有沙發、地毯、鋼琴、油畫。這次家訪完后,班主任就在學校到處講,說有些學生家裡怎麼怎麼豪華,說得我很難受。
“文革”時,我家房子被封,留下一間客廳,父親、母親和我們幾個人打地鋪。家具隻有一張方桌,四把椅子。全家生活費隻有20元。除了父親有一瓶牛奶之外,一日三餐都是青菜辣醬下飯。之后我們又被掃地出門,那時父親已經60多歲,全家搬到另一處小地方居住。
但我父母從來沒有唉聲嘆氣。他們很樂觀,還互相開玩笑。冬天,我們冷得要命,申請去原屋拿衣服。佣工很好,偷偷拿點筆、紙和畫冊,送到我們的住 處。父親依然在畫畫。我們居住的地方,中間有一個天井,可以洗衣服,后面是暗暗的廚房。我們睡的地方特別潮濕,常有蝸牛爬過。父親睡在最外面。晚上,蝸牛 就爬到父親臉上,父親還在呼呼大睡,睡得很香,忽然感覺不對,手一拍,臉上怎麼黏答答的。他講笑話說,這是美食法式蝸牛。
家裡再有錢
堆成山也沒有意義
我自己也沒想到,反而是那段日子,我一直陪在父親身邊,拉近了我與他的距離。
父親一直跟我回憶在法國的留學生涯。他說,當時的時局不穩,留學的資金有時會發,有時沒有。他就去賣畫。每天去盧浮宮,一邊寫文,一邊寫生。 “留學時間有限,這麼好的機會,我自己學都來不及學,一定要好好珍惜。”父親說。所以他那時很用功。最后實在沒有錢,他就從市裡的閣樓房裡搬到了法國郊 區,租了間房子。
父親每天早晨學法語,慢慢地就能和郵差對話了。法國郵差告訴他:“今天很高興,兒子來看我,我兒子現在是法國文化部長。”父親驚訝地問:“兒子 已經是部長,那你可以不用做郵差了呀?”對方說:“我很喜歡自己的工作,我為兒子驕傲,但我喜歡這份工作,不會因為兒子怎樣,就不做自己的工作了。”
父親對我感慨:家裡再有錢,堆成山也沒有意義。孩子自己沒本事,隻能坐吃山空。一定要靠自己,這是誰都奪不走的,是自己的財富。
那段日子,他常常和我說起這些。以前我看到他就怕,覺得他離我很遠。人家女兒可以與父親撒嬌,我們家卻不行。反而是這段歲月,拉近了我和父親的 距離。他對我講了很多道理。一家人雖然生活艱苦,但是很開心。隻要能畫畫,父親就很高興。他說:老驥伏櫪,志在千裡。他不相信現狀會長久下去。
隻有一次,抄家時有人燒了他的收藏。父親很擔心,說這是文物,是國家的寶貝,不是“四舊”,燒了就沒了。他一急,打電話給市領導,希望有一個人來處理這些收藏。后來終於有人來,說不要亂燒,終於保留了一部分收藏。
父親一直對我說:“這些收藏是國家的,不是我個人的。我只是把它們收起來,作為研究資料,將來捐給國家,讓大家看,讓愛好美術的人看,才能發揮它們的價值。”父親從來沒有把這些收藏當作財富,他認為,它們是精神的財富,不是錢財的財富。他一直叮囑我,生存要靠自己。
字要寫大字
畫要畫大的
家裡孩子沒有人學畫。父親的教育理念一貫是,喜歡就學,不喜歡就別學。我們也沒人主動提出學畫。后來我們看到父親因為畫畫受累,大家都怕死了,更加不會提出學畫。
就在“文革”的小屋裡,紙筆有限,父親每天會睡午覺。母親整理家務,隨時擋人。母親原本也畫得很好,她為了父親放下自己的愛好,挺可惜。
我閑著無所事事。有一天,母親忽然對我說:“你反正也是閑著,這麼多學生老大遠跑來請教你父親,現在你就在父親邊上,怎麼不學點畫?”可我還是 怕父親,不肯學,推說怕被父親罵。母親說:“你怕什麼?你要畫得比你父親好?那不可能吧?”我想也是,畫壞了也就是一張紙的事。我整天看畫冊,每當學生偷 偷摸摸來請教父親,我就在邊上聽。聽了許多,對畫畫並不陌生。
於是我就開始畫了。起初拿張小紙畫,用鋼筆臨摹畫冊。父親下午睡覺時,我就在那裡畫。一察覺他要起來,我就停筆。母親說:“別停,畫下去。”我說:“爸爸醒了,我怕。”母親說:“怕什麼,畫。”我當時手抖得要命,大樹畫得隻有一點點大小。父親看了看我,不出聲。
一段時日過去后,有一天父親終於忍不住說話了:“你要畫大畫,不要老是縮縮縮。縮得格局太小,沒氣魄。一張畫主要看精氣神。你是我劉海粟的女兒,怎麼畫畫格局那麼小,要有大氣魄!”他指著我畫的樹說,這樣不行,要用大筆畫。
父親沒有手把手教我什麼基本功,他就是關鍵時點撥幾句。他的教育風格就是不干涉你,先看你的路子走得怎樣。我怕他,他在的時候越畫越小。后來他 拿了一張大紙教育我:畫和人一樣,出來的氣質不同,個人風格也不同。但是氣質是可以磨煉的,一個人念書,學音樂,氣質會變好。他教我用毛筆畫鬆樹,先給我 說鬆樹的道理,要求我畫出鬆樹的氣質和精神。
他說:“重新來過,字要寫大字,畫要畫大的。膽子放出來,格局要大。”
要創新
但不是放棄傳統
回想起來,我小時候家裡也有大衛像。父親說,大衛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畫大衛,要把他的性格表現出來,而不是畫得一模一樣。有一次,一名學生到家 裡來學畫大衛,父親一看,畫得很大氣,就覺得好。父親滿意地說:“你不要細描細繪,要畫出大衛的氣魄。”所以,父親的教法和現在的美術教學不一樣。他甚至 不同意我用鉛筆畫。覺得鉛筆容易畫小了。他說即使是素描,也不是表現塊面,而是神。寫生更是,寫的是人的生命力。他會講道理,但不會讓你這裡擦掉,那裡擦 掉,這種細活他從來不教。他說:“大膽入筆,不要怕。”他還告訴我,學國畫一定要學書法,特意讓我練習寫大字。
父親常常把一句話挂在嘴上:平時自己練。他主張,自己學會欣賞和自學。比如,我喜歡文徵明的畫和筆法,那就自己研究。他會在旁邊指點幾句,文徵明用什麼手法,怎樣畫出那種風格的畫,但他不會具體到你這裡不對那裡不對。自己領悟很重要。
有一陣子,父親喜歡帶著我們去復興公園散步,那裡有個荷花池。我們走半天一定會在荷花池邊坐下來。我們以為父親只是走累了,沒有意識到他其實在觀察,研究荷花的光影。那陣子他畫了很多荷花,有重彩,也有潑墨。
白天,桌子給父親畫畫。有一次畫完他睡著了,我就用隔夜的墨,臨摹他的畫,畫了一朵牡丹。第二天他起得早,看到我畫的牡丹,激動得不得了,在我 的畫上題字。我確實沒有臨得一模一樣。他和我說,這幅很好,像雨中牡丹。朋友來了也拿出來炫耀。可惜當時我還不夠用功,在印染廠上班,三班倒,沒辦法全身 心練習畫畫。
有一次,父親說你要學會拉線條,建議我臨摹 《朝元仙仗圖》。當時正值夏天,我每天畫一點,兩個多月才畫完。畫的時候,用毛巾把手臂包起來,不讓汗水滴下來。
外人誤解,以為父親就提倡創新,拋棄傳統。其實父親傳統的根底很好。父親說,我們要留下這個時代的藝術品。老祖宗的作品,學得一模一樣沒意義。 我要創新,但不是放棄傳統。即使畫油畫,也是中國意味的油畫。為的是創作我們這個時代能夠留給后人的作品,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所以,父親並非隻知創新,不要傳統。恰恰相反,他告訴我,要了解古人,學習古人。他對我的要求是什麼都得會。母親總批評我眼高手低,別人的畫看不上眼,自己又畫不出來。我們三人一起互相開玩笑。
那段歲月,讓我對父親母親的了解更深了。
仿佛回到
父親在法國的留學生活
改革開放后,母親覺得我在廠裡翻三班對身體不好,讓我去香港。父親處境變好了,到處有人邀請他,他很開心。而我則在香港為生活而忙碌。那時候通信依然困難,電話費很貴,也不太打電話。
父親曾說,去了香港也別放棄畫畫,他覺得我天賦可以,應該繼續努力。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父親不在,我心態不好,總是沒耐心畫,還生了一場病。我是1979年去香港的,此后我在香港結婚,一直到父親1994年過世,這15年間我都沒有再拿起畫筆。
1994年3月,上海市政府打算給我父親過生日。我當時恰好回上海,父親沒問我還畫不畫,母親說了幾句,但是看我工作特別忙,也無可奈何。父親 說,自己一生隻有一件事未了,就是自己的創作和收藏想捐給國家。“希望我捐的東西,能夠常常展覽,給美術愛好者參觀。”父親說。后來政府部門的人回答,准 備為他建立一座美術館。
同年,劉海粟美術館建成。聽母親說,他坐著輪椅去看了新美術館,拍了照,很滿意。父親心事俱了,就在這之后去世了。
2000年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還是要畫畫,不然太可惜。我就去南京藝術學院進修。那是我父親呆過的學校。當時我已經51歲,但很用功。每周一去南京,周五回上海看母親。火車來回4小時。一直學到2004年,身體變差,走不動路,才改為每兩周回上海一次。
在進修時,曾有一位老師說我:“你是劉海粟的女兒,應該有傲氣,你父親是大師呀。”我說:“這是我父親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我有什麼可以傲氣 的?”借著父親的光,我傲不起來,反倒覺得自卑,因為與父親差太遠了。也有人說,進修4年后,你也可以當一名教師,但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
我認認真真學了四年畫。學油畫,也學國畫。南京藝術學院的老師不大敢說我,可能因為父親名頭太響,其實我不會介意。那段日子裡,我時常會想起父親以前教我的場景。靠自己領悟,靠自己勤奮,多看畫展,多練寫生。時光仿佛回到幾十年前,父親在法國的留學生活。
我看到很多,學到很多。
來源:解放日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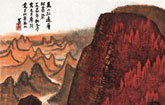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