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美國克拉克藝術館收藏的雷諾阿作品《劇院包廂》。
19世紀的巴黎成為了創造現代性的神話之都,由於城市的改建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人居場所的原有狀態,使得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界限漸漸模糊,印象派畫家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種互相交織的空間結構,於是一種在私人領域與公共景觀交織的空間就成了畫面上新的場景再現,其中就包括作為19世紀巴黎市民休閑重要組成部分的劇院和包廂。
陳瑤
19世紀對於巴黎來說,是個重獲新生的時代,在這一世紀裡沒有任何其他城市像巴黎那樣被賦予如此之多的語言描述和筆墨刻畫。巴黎成為了創造現代性的神話之都,成為19世紀當之無愧的首都。印象派藝術家們迫不及待以獨特的視角追隨時代的印記,並通過畫面呈現他們眼中正在發生的現代性的面貌。由於城市的改建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人居場所的原有狀態,使得原初的歸屬感和群聚意識變得混沌,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界限也漸漸模糊,印象派畫家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種互相交織的空間結構,於是一種在私人領域與公共景觀交織的空間就成了畫面上新的場景再現,這其中就包括作為19世紀巴黎市民休閑重要組成部分的劇院和包廂。
雖然劇院和包廂在官方沙龍的展覽語境中是個頗為新穎的題材,不過劇院本身已融入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特別是隨著19世紀中后期休閑產業在巴黎的穩步發展,到了法國第三共和時期,劇院已經變得格外流行。
包廂內外在場的男性目光 印象派盛期,巴黎的劇院包廂成為社交活動的重要場所,審視他人與被觀看始終是包廂題材繪畫中不可忽視的雙重結構,巴黎的精英階層和渴望融入巴黎社交圈的海外游人都將這一領域視為展示自我的絕佳場所,富裕的中產階級在其間穿梭社交和逗留欣賞。僅1862年,馬奈就創作了《杜勒利花園的音樂會》、《西班牙芭蕾舞者》和《老音樂家》等表現藝人和公眾休閑活動的作品,不過他不久之后就放棄了對劇院主題的刻畫,轉向了咖啡音樂廳,“在馬奈最后十年的作品中,他踐行著富爾內爾、塔克曼和莫福德所觀察的那樣:巴黎本身成為了他的劇院。” 和馬奈相比,雷諾阿、卡薩特更熱衷於表現正在欣賞表演的觀者。
雷諾阿1868年的《小丑》是他首次涉及劇院的題材。同一年,年長雷諾阿七歲的德加也首次演繹了劇院的題材,其《歌劇院的管弦樂團》可以說是印象派初期首幅具有現代感和成熟期風格的劇院作品。
1880年,德加創作了與雷諾阿《包廂》(La Loge)同名的色粉畫並參加了當年的第五屆印象派群展。從19世紀70年代末開始,德加創作了從劇院包廂內視角出發的一系列色粉畫,其中包括1880年的《芭蕾舞中》、1879年《拿花的舞者》以及1885年的《芭蕾舞者和拿扇子的女士》。在這三幅作品中,德加將我們的視角納入包廂之中,使觀者本身成為劇院活動的參與者,我們站在女性觀賞者的身后,我們的視線穿過觀者直達舞台。畫家將我們置於人群之中的同時,卻以扇子或不完整的截斷構圖作為一種隱形的帷帳,從而使敘事性完全讓位於瞬間即刻的感受。
雷諾阿在1874年第一次印象派群展中展出的《包廂》毫無疑問是包廂劇院題材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從形式分析的角度看,這件作品展現了雷諾阿十分嫻熟的繪畫技巧,無論是對光線的處理還是對衣紋、容貌的刻畫都頗為完美,色彩的流暢與和諧悄無聲息地滲透在畫面中。不過,在這些感官愉悅的背后,一種對兩性觀看雙重地位的思考慢慢凸顯了出來。畫中形象分別是雷諾阿的弟弟埃德蒙和來自蒙馬特的模特妮妮·洛佩茲,其中女性形象佔據了畫面的主體,同時也是畫面被觀看的主要對象。女人頭上及胸前的花、火紅的唇色、珠寶配飾和手中的雙筒望遠鏡構成了畫面最耀眼奪目的點綴。相比之下,穿著黑白素色並以較潦草筆觸刻畫的男同伴似乎成為了一部分背景和陪襯。畫面中的女人輕輕放下了望遠鏡,仿佛沉浸在對歌劇的欣賞中。然而,相反於女性略顯拘謹的姿態,男性形象舉著望遠鏡向高處仰望的動作就顯得積極而主動。這時我們會察覺雖然女性的目光是向畫外延伸的,但畫家將她的眼神定格於一種迷離的狀態,避免了與畫外潛在觀者的直視。而關於觀看的特權,雖然女性手拿著望遠鏡,但在畫面上,那一抹金色似乎更像是為畫面的色調增添一抹光亮,真正具有觀看主導權的依然是她身后的男性。“《包廂》從隱含的意義上看可以被認為是呈現了社會上合法的‘觀看’模式,也因此加強了一種傳統關系,這種關系不僅表現為畫面中的男性和女性,而且體現了繪畫本身和繪畫之外預設觀者的男女關系。”
在《包廂》創作的那個時期,“來自一個良好家庭背景下的時尚女性都統一被描繪為寬眼,精致的顴骨、嘴和下巴。而雷諾阿的女性形象和這個范式有悖,她有一些微胖,臉有點略腫,嘴巴也比較寬而且肉感。” 因此關於畫中女性社會地位的界定成為學界常常爭論的議題。在巴黎,劇院猶如一個微觀社會,包廂的不同等級暗示著坐在其中觀賞者的社會階層。例如在1870年代,在法蘭西劇院裡預訂一個一等包廂需要的花費幾乎是最便宜包廂票價的12倍多。對於不富裕的雷諾阿來說,在劇院好一點的包廂看場演出可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因此,畫中女主角可能是雷諾阿對上層社會女性形象與著裝的想象和渴望。她在畫家心中可能是大家閨秀的淑女,也有可能是輕浮的交際花,這種雙重而模糊的身份使她更加散發著神秘而朦朧的魅力。雷諾阿的畫筆猶如一種激發身體感官愉悅的工具,他的筆觸觸碰的部分如同溫柔的輕撫,喚醒了畫中生命美的意識。
除了《包廂》之外,雷諾阿又分別在1876年和1880年完成了《劇院裡》和《劇院的包廂》這兩幅包廂系列的作品。雷諾阿在《劇院裡》描繪了一位正沉浸於表演中的年方16或17歲的少女,在少女的包廂內還有一位女性同伴。按照當時的社會慣例,大多數中產階級或家教良好的女孩通常隻有到結婚之后才會去劇院,而沒有結婚的女人或女孩至少都會有一位同性的伴侶或監護人,因此,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年長女性可能就是少女的監護人。和《包廂》中盛裝出席的女性相比,少女在這裡一襲黑衣,不過由於畫家刻意以疾速的筆觸草草地勾勒遠處包廂中的人物,使得少女在畫面中依然是唯一的焦點。畫面下方包廂中的一個男性目光隱約地落在了少女身上,不過少女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正作為被觀看的對象。《劇院的包廂》原先是受法國美術副部長埃德蒙·蒂爾凱委托的家庭肖像作品,不過畫作最終並沒有被接受,1880年魯埃購下此畫並將其送去參加1882年的第七屆印象派群展。雷諾阿用深紅色的背景窗帘抹去了原本的男性形象,畫面中隻留下關系尚無定論的面向觀者的年長女性和低頭凝視的少女。兩人的衣著是一黑一白的純色對比,在時尚之都的巴黎,著裝不僅有場合差異的得體要求,也是階級和社會身份最外在的彰顯,對於資產階級女性而言,“越是正式而宏大的場合,女性衣服的袖口越短、領口愈低。” 我們在畫面中所看到的女性形象正是如此,低胸的禮服以一朵花點綴,她雖然面向畫外,卻沒有《包廂》中女性形象的拘謹和被動,而是呈現出安格爾筆下常見的優雅姿態,輕鬆地倚靠在包廂座椅中。縱觀雷諾阿的包廂系列,雖然畫家沒有具體交代畫中人物的身份、相互關系以及劇院場所地點,但是它們都是試圖再現資產階級休閑氛圍的典范,而且是透過一種不言而喻的男性目光。
包廂作品中
女性觀看角色的轉變
在德加和雷諾阿創作包廂題材的同時,卡薩特也開始著眼於對這一題材的表現,並在畫面中凸顯了有別於男性視角的獨特觀看模式。從早年旅居西班牙期間創作的《調情,塞維利亞的陽台》開始,卡薩特就有意識地改變兩性觀看的狀態。這件作品雖然和馬奈的《陽台》同樣選取了三角結構,但畫中的女性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活動中,無涉畫外觀者的存在,於是男性觀者的眼光被克制在畫外。卡薩特1877年的《歌劇院中的黑衣女子》是呈現觀看對立和矛盾的代表作。畫面前景是拿著望遠鏡觀看演出的女性形象,遠景的包廂內有一男子正拿著望遠鏡窺探前景中的女性,男性透過望遠鏡恰好與畫外觀者的目光相遇。畫面裡,卡薩特隻以白色手套、折扇以及珍珠耳環點綴一襲黑衣的前景女性,畫中男女有著某種共性,他們都穿著黑色禮服並配有白色袖口,男子是大膽進攻的姿態,女子沒有絲毫理會並使用望遠鏡鏡積極地觀看。兩年后,卡薩特在《包廂中戴珍珠項鏈的女子》裡展現了與雷諾阿在《包廂》中所刻畫的完全不同的盛裝女子。卡薩特描繪的可能是妹妹莉迪亞,她身后的鏡子反射出劇院燦爛奪目的歡愉景象,沒有面對畫裡畫外目光焦距的不安,她正隨意地倚靠並散發著迷人的魅力,似乎正在享受這萬眾矚目的一刻。1879年卡薩特還創作了兩幅包廂題材的作品《包廂裡》和《劇院》,畫裡女性展開的折扇和望遠鏡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觀者的視線,“對於在劇院裡正襟危坐的女人來說,扇子代表著一種運動,一個流動的帘布,它揭示著那些顯然隱藏的而同時隱藏那些顯然暴露的。”在卡薩特的包廂題材裡,女性不再是被動的觀看對象,正如女性主義美術史學者格裡塞爾達·波洛克分析的那樣:“無論是雷諾阿或德加的劇院包廂,女性都沒有在用她們的望遠鏡。但卡薩特筆下的女性不僅僅是男性觀者注視的目標,更是積極的觀看者。” 卡薩特忠實地記錄了劇院消費文化興起過程中女性所積極參與的部分,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男性主導的觀看慣例, 也通過一種融入到演出欣賞的狀態和對社交歡愉的專注展現了現代生活私密的片段。
就在雷諾阿創作《包廂》的同一年,一位現在並不知名的女性藝術家伊娃·岡薩雷斯也創作了一幅重要的包廂題材作品《意大利劇院包廂》,這件作品當時落選了1874年的沙龍,之后稍作修改最終在五年后的1879年沙龍上展出。雖然我們現在無法得知這兩幅構圖有些類似的包廂作品是否存在某些創作過程中的互相影響,但當我們將其並置對比時,畫面中所隱含的藝術家性別身份的對比就逐漸顯現出來。
關於女性藝術家的地位以及女性在整個藝術史長河中作為觀看客體的議題是包括琳達·諾克林、格裡塞爾達·波洛克和羅茲卡·帕克等女性主義藝術史家探討的重點。然而,早在岡薩雷斯的這件包廂作品落選沙龍后不久,法國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代表瑪麗亞·德雷姆斯就專門撰寫評論文章聲援這位女性畫家,岡薩雷斯在男性話語霸權的藝術世界裡堅定而獨立的態度同樣體現在了這幅包廂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和雷諾阿《包廂》中女性游離而曖昧不定的眼神相比,岡薩雷斯對女性神情的描繪顯得自我而果敢得多,她略微前傾的動作以及兩邊手臂不同的擺放打破了雷諾阿畫中女性封閉狀態的一種平衡。質地輕薄如紗的藍色低胸裙與右邊的藍色花束相呼應,有評論認為這前景的花束是岡薩雷斯向導師馬奈致敬,因為“據德雷姆斯所言,岡薩雷斯離開當時受歡迎的學院派大師查爾斯·喬舒亞·卓別林的畫室進入馬奈門下是一個關鍵的決定”。女性左手握著的雙筒望遠鏡已經不像是雷諾阿《包廂》中女性手裡的裝飾物,在雷諾阿的畫裡,望遠鏡和包廂欄杆的色彩彼此融合,而在岡薩雷斯的作品中,它與欄杆的紅色對比強烈,這種凸顯証明了這一觀看工具已不再是男性的特權。《意大利劇院包廂》裡的男性以側面造型刻畫,左手叉腰的姿態反而顯得有些不自然,觀者無從得知男性眼神注目的方向,男性和女性與畫外觀者的抽離態度是平等的,雷諾阿《包廂》裡隱約的從屬關系在這裡已經消失不見。卡薩特和岡薩雷斯的畫作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男性在觀看行為中的主導和優勢地位,她們以積極的女性視角呈現了光影交錯的時代片段。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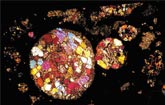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