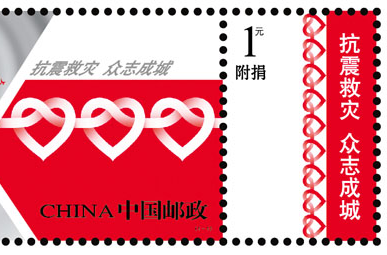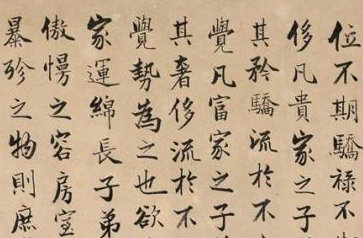1954年創作出版的《畢業了,參加農業生產去!》

哈瓊文創作的《做一顆紅色的種子》(1963年)

《廣闊天地 大有作為》(1970年)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務農的運動是中國農村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章,反映知青生活的美術作品與同時期美術中的農村題材和農民圖像具有緊密聯系。在革命的激進主義美術中,知青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農村青年的未來形象。他們所面對的世界和問題在一種非常奇特的相遇中變得相通甚至相同。
知識青年留在農村或回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這是從1950年代初期就開始提出的,到60年代初期就正式掀起運動,更多地號召城市的畢業學生到農村務農,規模逐步擴大。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達到高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務農的運動是中國農村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章,反映知青生活的美術作品與同時期美術中的農村題材和農民圖像具有緊密聯系。
1954年創作出版的宣傳畫《畢業了,參加農業生產去!》(1954年)應該是對1953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積極回應,這篇社論是公開地、大力地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源頭。畫面上描繪了一位身穿白襯衣、肩挎著書包、手裡握著書本的青年知識分子回到農村,人物形象很准確地表現出知識分子的特征。但是,與后來的農村知識青年和城市下鄉知青的圖像比較起來,這幅作品顯然是缺乏對勞動、鍛煉、成長等這些概念的准確表達,以至於畫面上的這位知識青年顯得有點文弱、過於書生氣。
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提出:“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52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2月)最后那句話日后成為上山下鄉運動的最著名口號,一直回響到1970年代末期。
從1957年開始,政府把號召知識青年回鄉和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列入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65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12月)
這就是此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知青下鄉題材宣傳畫的歷史背景。
“文革”前的知青在中國四十年的知青運動史上尚未被充分研究,在文藝創作中的形象也是處於知青文藝的邊緣地位。哈瓊文創作的《做一顆紅色的種子》(1963年)是早期知青美術中最有代表性、藝術性最高的作品。這幅宣傳畫描繪了非常健康、充滿理想精神的一位下鄉女知青形象,她手執稻穗、回首遠望,表現出遠大的志向。沒有以農村的梯田、田野作為背景,沒有老農的指引領導,也沒有扛著農具、戴著紅花,單純的一個青年女學生的形象,手裡執著的稻穗點化著題目中的“種子”,寓意著理想主義的播種、成長。與“文革”時期的知青題材宣傳畫比較起來,它顯得過於抒情或過於理想化了——或者說,后來的知青宣傳畫的理想化和抒情性是建立在更加激進的立場上。
《立志一輩子做農民》(1966年)的題目是當時流行的一句非常直白的口號,比“扎根農村一輩子”之類更加直接。從意識形態宣傳的動員功能來說,這種對轉換身份的號召有著多重的內在邏輯:第一,顯然這不是對農民而言的,農民的身份早已被城鄉戶籍制度所固化,“做”還是“不做”根本就由不得農民選擇,也就無需號召他們“立志”﹔第二,這種類型的口號也顯然不能套用在其他身份轉換上,比如說從來沒有號召人們“當工人”或“當國家干部”,因為那些明顯是人們會自動追求的身份,是從來都不需要動員的﹔第三,它強調“一輩子”,意思就是對身份轉換的可能性的否定。對於當時絕大部分迫於無奈而下鄉的知青來說,這套邏輯根本就無需思考,生活的語境早已使人們知道需要動員的東西不是什麼好東西。就像“勞動光榮”這個本來意義上是非常正確的口號一放到現實生活中就變得十分虛偽:壞分子都是被監督勞動的,而人們從小就知道在學校裡做了錯事是要被罰做清潔勞動的——所有的現實都使人們知道勞動是一種懲罰,何來的“光榮”呢?
因此,像《立志一輩子做農民》這樣的口號和宣傳畫在當時的生活中比其他的宣傳畫具有更真實的刺激人們心靈的力量,它把人們無法逃避的命運塑造為一種圖騰,接受著人們表面上的順從和心底裡的怨恨。畫面上這位笑容滿臉、斗志昂揚的女知青牽著牛、肩扛犁耙、手執領袖著作,走在廣闊的田野上,這種理想主義的圖式與上面那幅《做一顆紅色的種子》有著巨大的區別。關鍵就在於它把生活語境直接呈現出來,在這個基礎上生發出理想主義精神,而那一幅卻隱去了真實生活的必然道具和情境,使理想和抒情變得抽象化。因此,如果說意識形態宣傳都包含有說教成分的話,《種子》的說教是較為軟性的,《立志》則是赤裸裸的激進主義規訓。
到了“文革”時期,知青上山下鄉宣傳畫的圖式語言又有了重要變化。1968年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全國迅速掀起了上山下鄉的高潮。1974-1977年再次出現高潮,這期間全國又有7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此時的知青宣傳畫比較常見的是像《廣闊天地 大有作為》(1970年)這樣,以毛澤東的這句語錄作為核心口號,在畫面情景和人物形象上多以農民迎接知青為主,農民和知青分別作指引方向狀和斗志昂揚狀,這種圖式是最為流行的。農民作為指路人的光輝形象在這時大量出現了。
進入70年代以后,意識形態宣傳中對於知青上山下鄉的表述有了一套更完整、更有理論高度和激進主義色彩的系統化話語,很典型的就是:“廣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涌現出來的新生事物,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途徑,……在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下,廣大知識青年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深入批林批孔運動,狠批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孔孟之道,扎根農村,扎根邊疆,堅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他們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結合農村斗爭的實踐,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積極參加三大革命斗爭,經風雨,見世面。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革命的青年一代,正以堅定的步伐,沿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社會主義大道上闊步前進。”(見人民美術出版社在1974年編輯出版的《在廣闊天地裡--美術作品選》“出版說明”)
在上面這段話中包涵了定義、性質、學習、批判、道路、實踐、方向等等,這套話語已經成為一幅完美的語言圖騰,其中的詞匯、語序等等都不可移易。如果以它來看待和要求視覺圖像的藝術創作也能達到這樣的水平,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視覺圖像所擅長的是通過形象的塑造傳達出在這幅語言圖騰中所包含的精神實質和審美傾向,把所有的觀念轉換為一種以青春、朝氣、陽光雨露和成長為形象特征的視覺形象。
張紹城創作的宣傳畫《廣闊天地新苗壯》(1973年)可以說是非常出色地達到了這個目的,成為知青主題宣傳畫中最富有青春魅力和蓬勃生命力的一幅優秀之作。這幅作品以到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為素材,陽光初升的時分正是在橡膠林中割膠的兵團知青凱旋的時候。陽光洒在知青們的身上,勾勒著青春健美的身軀,一切都是那麼清新、充滿著朝氣。“新苗壯”是一個富有政治性意味的語匯,按其本來的修辭敘事來說,甚至可以說是充滿了先鋒激進的現代性光芒。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文藝的創造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創造出許多足以代表意識形態政治的自然物符號,如“陽光”代表黨和領導人、“葵花”代表忠心耿耿的人民等等,而“新苗”則是一種非常形象化的革命青年的身份符號,就像“根正苗紅” 的說法一樣,而又更強調了“新苗”意識中的血統論。新與舊,新苗與朽木,革命激進主義的進化論邏輯在某種程度上也契合著人類喜新厭舊的天性。
下鄉知青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農民形象的一種改造和發展。本來無論從身份、經歷、歷史傳統等任何方面來說,知青作為一種從歷史的長河來看是非常短暫的政治潮流的產物,與農民有著巨大的根本區別。但是如果把這個問題放回到那一段歷史的現實情景中進行分析,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知青與農民之間存在著某種具有真實意義的聯系。首先,從激進反智主義價值觀來看,知青需要的是改造為像農民一樣的人,而農民則因為有了知青而成為了提供“再教育”的老師,他們之間的身份轉換是激進主義的必然邏輯。其次,從實際生活情景而言,由於知青較為普遍的生活狀況已經與農民的生活狀況相混合,有些知青的形象已經與當地農村青年的形象產生趨同,在審美上的特質已經相互滲透。因此,在革命的激進主義美術中,知青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農村青年的未來形象。
因此,在宣傳畫上的農民與知青的形象雖然分別扮演著指路人和接受“再教育”者的角色,但是實際上他們所面對的世界和問題在一種非常奇特的相遇中變得相通甚至相同。(李公明)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