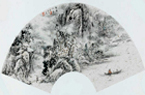今年8月11日,我参观了在新世纪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六届成都双年展。次日,本届双年展“因场馆有新任务”而悄无声息地关闭了,比原定展期提前了4天。我总算是搭上了末班车,12年来一届没落。
与隔壁需购门票、喧闹的3号馆举办的婚博会相比,免收门票的4号馆的双年展相当冷清,绝大部分的影像作品已断电,甚至连投影仪都撤掉了,门口再也不见前几届那样售卖作品集、纪念册的摊位。与上届官方号称3500万人民币的大玩法不同,据说本届又回归民办,预算自然也就“低碳”了。不晓得这届双年展是否连媒体和批评家也“低碳”了,至今也很少见相关的消息。本届的题目是“万有引力:十年集萃新人特展”,我不懂“万有引力”的意思,但还是看得出,这是将前几届双年展给年轻艺术家的福利——新人展,独立出来成为一届展览。会展中心有一家画廊,我发现里面的作品比双年展还好些,当得知工作人员居然没去过近在咫尺的4号馆,我说:“今儿下午就是最后的晚餐了。去看看吧,有没有你们物色的‘新人’。”他说,他忙着呢。
还记得2001年底的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开幕式弄在晚上零点,天气虽然阴冷仍然有很多人哈着热气来看所谓的新体制展览。策展人顾振清、刘骁纯,几大美术学院的负责人,谷文达、方力钧等艺术家,栗宪庭、李小山、王林等批评家都在。在体量巨大的成都现代艺术馆双年展(现已拆除)的门口广场,董事会主席邓鸿在明亮而寒冷的灯光中提到城市文化、城市活力、双年展等关键词,闪光灯不断。但是,从第一届双年展开始,各种问题和争论也就随之而来:关于策展人、展期、主题,关于个别传统国画作品不具“当代性”……或许,有“问题”的展览才是成功的。因为关注者众多,成都的“当代艺术之城”美誉也不胫而走。而今年的双年展却是如此冷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少新东西刚出现的时候,给人太多的想象空间,但是往往无需多少时光就变味了,如“大师”“画派”“当代”“学术性”“平行展”……
作为一种从威尼斯山寨过来的展览形式,双年展在上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当代艺术之风,接续了“星星美展”“85新潮”“89后美术”,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期有一定针对性,并逐渐形成一种与国家美展体制并行不悖的学术与市场体系。随着原先体制外艺术家商业上的成功,以及双年展在各地遍地开花,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某些双年展逐渐失去最初的前卫精神,也失去了双年展本身的艺术特色和学术主旨,而沦为各种“文化庙会”的附属物。某些反讽画风,在文化多元与包容的当下也逐渐失去了批判性。由于赞助方或策展人的个人意趣,某些双年展成为了朋友圈、利益圈的私人聚会,成为了某地、某美术学院、某批评家群、某风格(如卡通一代、颓废现实主义)的艺术聚会。一些早年成名的在野艺术家,不断在各种双年展上重复和强化自己的“一招鲜”,实际上也已经体制化了。
显然,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意识到双年展并非“洪水猛兽”,可加以改造和引导,同样可以为民众提供文化服务,也开始打造这种有装置、影像、声音等新媒体形式的展览。比如,一个可以动的、电子版的《清明上河图》,民众一定会感兴趣,而且也异于常见的书画展。但是,笔者还是更看重民间赞助的双年展。当然,除了要有雄厚的资金外,更需要专业的和相对稳定的策展团队,对社会、文化和艺术定位精准的展览,可以成为沟通当下艺术家和公众的一道文化桥梁,甚至引领一股与时代契合的新艺术风。在消费主义、电子游戏、娱乐八卦等裹挟下,民众的精神空气日益稀薄,新艺术应该与新时代对应。无疑,策展要考虑为当代和后来的艺术上留下了什么,不能有太强的甲方意识和功利目的,而应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则就会变成自说自话。
显然,策划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双年展,要比炒作个体艺术家更加困难,更需要有时代的敏感和未来的视野。如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展览机制——双年展,掺杂了太多的“杂念”,自然也就无人关注,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作者为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副教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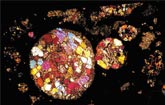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