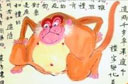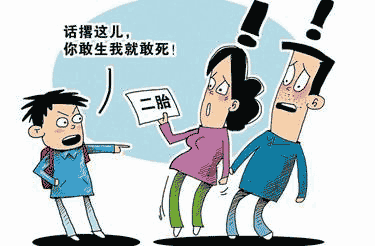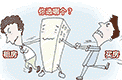“我画的不好”,这话我两年前常常微低着头对别人说,也常被人回复说谦虚,其实是真话。但这两年说的少了,因为说多了,自信有损,气氛也尴尬,衔接的话头和解释也麻烦。但我总是说不出“我画了一张不错的画”,不是不想,是无法出口。指望未来画出让人信服作品的心思当然有,但首先想弄清楚,所做的东西凭什么是一张值得称道的好画而不是一件垃圾。
可怕的是,一旦有了这种心思,心里就会惦记,画就无法天然而自信地画下去,就会出现许多的疑惑,许多的反复和折腾,没办法。有时候,看着屋子里放了一堆的画框,嘴里会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出“真是一种浪费”的话。甚至决定以后不再轻易画太大的画了。从环保角度看,画大画的方式确实很不环保。要砍伐树木做油画内外框,还要涂刷那么多的颜料,再搞不清楚自己画画的目的,确实是值得谨慎对待的事情。
这些略带悲观的情绪倒也不是常有。许多的时候还是会很开心地在琢磨着画画,幻想着有一天能画出有点意思,或者还比较过瘾的东西出来。有次和同事喻建辉聊天,说到将来也许能把自己的画当作给孩子的遗产,好像又找到了一个鼓励自己认真画下去的好理由。
回忆自己看似不短实际不长的画画经历,似乎有些东西是有趣的,值得自己琢磨的。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似乎也可以变成供参考和研究的材料,帮着自己一点点弄明白这画画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人生中最初有图像感的记忆仿佛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也许才一两岁的自己在一间幽暗的平房内,窗外树荫茂盛,枝叶竞发,但一切都只是梦般的不可印证了。
在可以确认的真实记忆中,最早的画画行为好像是在上小学前,应该是四五岁的样子,父母上班,兄妹不在,家中只有我一个人。也是在下午,混暗的房中,窗外明晃晃地射入一束阳光,只见空气中有无数的微小灰尘在漂浮游动。我坐在大大的床上(也许我那时太小),手拿着笔,在一个本子上画着连环画。只记得气氛安静,好像就有过忘我的体验(现在人喜欢说物我两忘)。具体画的什么内容不记得,应该是小人和故事,很可能是打仗,抗日战争之类的。现在想想最有意思的是那样的一个下午,竟画了整整一本的故事画。那时,我没有受过美术的训练,但不排除自己看到过一些墙上的涂鸦或其他小孩画画。如果这个回忆确实的话,是否可以这么说:至少有些简陋的画,是可以不用人教而自己想着画出来的,或者说,至少在起初,画画可以是人天生的一种自觉或说本能的需要。
其他的事情乏善可陈。既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可以证明自己有画画天赋的有力证据。当然前前后后也有许多的记忆。其中有一个景象,是自己站在简易楼的过道里,看着黑黑的天空上落下暴雨。有邻居家的大哥哥用白色粉笔在地上、砖墙上画小人,一个圆圈做头,几根线作身子,简单至极。不过在我眼里,却是活生生的,让我感到神奇。那感受至今仍有印象。于是也就学着去画这种“活”的小人。
小时候另外的一个怪癖是总喜欢自言自语,自己在脑中编排出一个个“逼真”的景象和故事,然后自己就做了导演,讲着故事,还配上音。以打仗的故事为多,古今中外都有。那时候上下学或者玩也总喜欢一个人。假如逆转时空回到我小时候的历史空间,一定会看到一个形单影孤,常常吊着个眉毛,苦着个脸的瘦瘦的小学生,在上学路上,在厕所里,总是嘴里叽里呱啦地在自说自话讲着故事,不时还夸张地发出“砰、啪”的枪弹声,或者“笃笃”的马蹄声。现在想想,也挺神经的。于是把这种故事画出来,编成小人书,也就成了自己的乐趣所在。
一个自我的世界是可以经过内心的想象建立起来的,而且,人可以独自在里面过的自在快乐,这是我小时候就知道的。后来,上了附中和学院,慢慢意识到,从幼儿开始的个体的人,从古至今群体的人类,绘画都可以帮助意识的主体进行自我的对话,形成一个更丰富的内心世界,还能让这种内心的对话更有趣,更形象。但究其所以,这个内在世界本身并不是依靠绘画建立的。
一旦正经学习画画,并把它当作职业,就发觉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内在世界有交集,也有很大的分离。特别是不明白绘画为何,何为绘画的时候,更是容易把画画当作外在于自己的一门技术。也就容易迷惘和失望。
小学之后,在初中美术组以及那些在西安美院附中、本科和研究生的日子,既给过我初学绘画进步飞速时的兴奋,也给过我在研究生毕业时渐趋强烈的那种画腻人体后对课堂写生模式的厌烦,堪称美好、苦恼与矛盾掺杂。这段求学过程暂且略去。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学院学油画时甚至没有感觉到调颜色的快乐,更多的是腻味,也是奇怪和遗憾的事情。
由于有对素描习作和油画人体写生的逆反心理,1996年毕业到北师大当老师的时候,我甚至想忘掉自己曾经学过的让我感觉不快乐和不自由的方法,看看能否重新回到轻松胡画或无知的起点。
但对艺术魅力的体会,却比在美院上学时还要强烈。当我第一次站在北师大的讲台上,面对非美术专业学生讲授公选的《美术欣赏》课时,看到的是一双双纯真的眼,特别是当我感觉到当幻灯机在荧幕上投射一幅幅名画时,这些眼睛里放射出了对艺术真正赞赏和感动的光华,我深为之震撼。第一次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学美术真的有意义,真的有价值。也第一次从心里感到,专业科班的未必一定能体验到艺术的好处,非专业未必就不能。
那时候不了解学问,更没有学科和研究的概念,一心觉得学纯绘画的如果去搞理论研究,就算是转行了,也完全没有必要。
读书太少,思想就狭隘,由此可见一斑。
毕业当年还是想画画的,于是在北师大集体宿舍里支起画箱,怀着去掉太多专业想法、回到零点的期望画些小画。但状态一直很不理想。于是持续地迷惘着。
期间,也曾关注和接近过当时的“前卫”和当代的自由艺术家。稍稍接近了这些哥们几次,却觉得他们的状态肯定不是我所要追求的感觉,尽管说不出所以然。于是重新回到孤单。
就这样在摇摆和迷茫中,渐渐地为了适应环境,改善生活,自己画的越来越少,杂事却越来越多。当时,北师大尚未招美术专业本科生,学科的边缘化也多少影响到自己的自信和动力。随波逐流的感觉越强,创作的指针摆动的频率也就越慢。
但这种相对停滞给我的好处是,当我缺乏画画的环境,才真正意识到画画对我有多么重要。终于,毕业两三年后,我不再腻味任何样式的画了,也不再期待忘掉曾经学过的任何东西。我感觉画画对我越发亲切自然了。绘画的缺失让我渴望画画,同时慢慢让我理解了有些在自己意识中生根的知识是不必要刻意去掉的。画画的快乐正在慢慢地重新回到身体里。
实际上,正是不间断的学习和思考帮助人在意识中建立起画画的意识,特别是美术史的知识,让学画者体验到绘画诸多的妙处。绘画历史的撰写,那些重要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素养。其次就是对绘画时一般要进行的连续动作,以及观察、表达的通行规则越熟悉越好。但这些基础毕竟还是由画家持久的个人心气左右着。
思想在岁月的流逝中继续一点点地变化。看西方大师们在美术史上留下的经典原作曾经是我心中的结。这个结从我上附中开始,就因为始终没有机会尽兴地看画册和画展,而深埋在心底。看大师原作,认真学习(最好掌握)西方艺术大师的技巧成了一个潜在的愿望。但这个心结却在我2006年夏天去希腊访学和欧洲考察的一年间也得到了化解。走过卢浮宫、乌菲齐、奥赛长长的廊道,眼睛扫过无数在心中神圣无比的画作,心里想的却不再是美术史,而是人。一种更强烈的感觉从内心生成:毕竟这些都是过去人画过的东西,画出我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从此,我开始懂得用平常的眼光去看这些大师名作,以及大师之外的无名画家。技巧褪去了神秘,开始变得更为亲切和有趣;大师少了些威严,越来越像朋友;美术史多了些人文性,变成了求证自己感觉,寻找与自己观念和感受类似的“我的知音”的好资料。与此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出美术史是怎样被人们凭着自己的主观认识,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观念结构,从浩如烟海的人类制成品中挑选代表作,组织、编排概念并自圆其说地描述出来的。
美术史心结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对大师们不再欣赏,相反,我觉得自己与他们贴的更近,更喜欢他们。但这种喜欢不再是崇拜。自己也不再期待成为一个能够写进美术史的“让别人钦佩”的画家。想到这里,自己都会开心地微笑。放下这种心结的轻松和愉快,以及这种愉快带来的对绘画乐趣的重新获得,是从前咬牙切齿、奋发图强地想要投身艺术,改变或创造新的美术史的自己所无法想象的。
到目前为止,自己是业余画画,职业教书。但内心的理想更盼着早日退休,这样能多一些时间和空间留给自己,心无挂碍地画画。给我安慰的是,中国古代很多的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原本都是业余画画的,或者说,不靠卖画生存。这样一来,又给自己找到了更多榜样,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在而独立地画下去。事实上,随着对中国画理解的加深,我对中国式“艺术家”(实际上,这些文人画家从来没有把自己当过艺术家)生活方式的喜爱在最近这五六年变得越来越强烈。
生物尚且提倡多样性,何况人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追求。而我所形成的个人对艺术的看法(说的更重一点是信念)毫无疑问更侧重人和生活,而不是为了追求艺术史上的英雄主义。但这种信念需要细节的完善来落实,才能让艺术玩的过瘾,玩的尽兴,活得开心。这些细节只有讲究文脉,品味传统,才能实实在在地有韵味,有嚼头。每个人的文脉和传统都可以不一样,只要注意观察,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学习和生活的机缘自会带每个人走向他该有的归宿,这就叫造化。
关注业余和自己的内心,并不意味着对社会责任的淡漠。现在越来越感到,人可以同时画出两种绘画,一种是很私密的,只为自己、知音和好友画。另一种则为社会和大众而创作(或者叫策划实施),前者重点在个体体验的过程,后者重点在观念与信息的社会传播和相互交流。我不再以成为成功而职业的艺术家作为目标。特别是渐渐领悟到,职业艺术家在当下时代中,需要舍弃相当部分的独立性,向市场、政治和其他非艺术因素作相当大的妥协。没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是很难把控的。于是,走入职业似乎比以前需要更多的修炼才行。
一个人一生可能始终只在画着一张画。一个人可能只真正相信他自己肉身所能切身感知的东西。既然一个人的寿命是一定的,一个人的肉体所占空间和感知能力有限,又何必着急,让上天决定最后的艺术命运岂不快哉。
与此同时,由于自己在近四年做博士学位论文的缘故,比之前更多关注艺术的媒体性。也启发我从“人的一种活动”去看待绘画。
把绘画看作行为的好处,是可以将人的动机、谋划、选择、步骤、制作以及最后的交流、展示、反馈,甚至一生所画的东西,坚持的追求,看作“一辈子的事”。也可以减弱技巧、材料、媒介与自我、人性的隔膜性,有利于从人性和自觉的感知或者说观念出发,考虑哪种技巧更适合自己。
画画理由充分,因为画是人的本能。快乐存在于画(整体意义上)的行为之中。而画的存在有任何的可能性。对我来说,作为动词的画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感觉的过程。作为名词的画,则事关个人趣味和自我的身份认同。画好之后的传播与交流则显示了绘画与社会的关系。我也需要改变自己很少交流的懒惰习惯,因为交流是必须的,同行者的意见和知音的寻觅是重要的。
有这样的上下文背景,关于为什么画、什么像画,也就渐渐有了一些想法。包括对现在的画坛时局,静静旁观的同时,内心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艺术家能更自觉地看淡西方艺术体制,减少拼命争一个“国际”名分、挣一点“世界”意义的习惯性愿望。当西方世界不再是唯一的他者,他者可以是反思的自己、陌路的同行、邻邦的小国,甚至野生的兽类时,中国的画家才可能会真正自信起来,用更沉静的心态体会自己和自己所在群体的心灵与情感,针对自己的情境,画自己该画的画。
读“石涛画语录”时,我很高兴,因为自我感觉他对画的感受与我相似。且不管他的“一画”原意是否是我的一画。我觉得石涛对个人自身感受的强调不止是一般意义的领悟。画画,只要没有失去感受,一切都有希望。
读黄宾虹的这段话,也让我心有戚戚焉:“士夫之画,华滋浑厚,秀润天成,是为正宗,得胸中千卷之书,又能泛览古今名迹,炉锤在手,矩矱从心,展观之余,自有一种静默之致,扑人眉宇,能令睹者矜平躁释,意气全消。” 深入我心!
最终,还是希望画出石涛一样自由而有丰富感受的画。
本来是为这本画册写个序言的,最后变成罗里啰嗦,夹叙夹议的一篇杂乱文字,始料未及却也有些意义。毕竟有机会静下来想想自己画那些画时的语境,对以后是有用的。
但要小心,因为说得越多,画的就越少。少说多做才好。
甄巍
2011年5月4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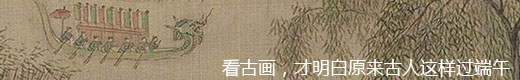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