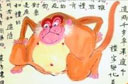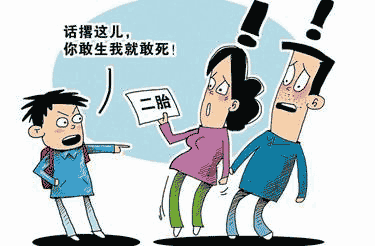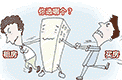米芾(音福),虽祖籍为太原老西儿,但其父搬至湖北,他出生在襄阳,应该算是半只九头鸟。米家祖上均为武将,太祖父米信是北宋开国勋臣,侍奉北宋初年的兄弟俩皇帝,在《宋史》中有传记。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怕手下的将军们再扶出另一位皇帝,就“杯酒释兵权”,改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武将地位一落千丈。米家老祖希望后人弃武从文,米芾就成为老米家成功转型的功臣,还是位历经五朝的不倒翁。《宋史》对米芾的艺术评价很高,称他“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襄阳米南宫,遇石便称兄”。米芾的名号很多,“米襄阳”是指他的出生地,“米南宫”是指他的礼部员外郎官职,但最有名则是“米颠”,也就是癫狂之意。史称,米芾喜欢穿着奇装异服,其实就是唐人的衣冠,招摇过市。米芾最喜欢搜集奇石名砚,每当见到珍稀的石头,都会高兴地向石头行礼,称兄道弟。其实也没有错,地球上的石头,哪块没有亿万年历史。
米芾之狂气在《宋史》中记载得十分传神。宋徽宗赵佶初次招米芾入宫,请他先在御用屏风上书写《周官》某篇。米芾奋笔疾书,完成后掷笔在地上,并大咧咧地声称:洗去二王所写的烂字,才能照耀大宋皇帝万年。要知道,艺术皇帝赵佶可是王羲之、王献之的天字第一号铁粉,狂士老米虽比皇帝小赵大卅一岁,但也不该随意消遣二王。听到老米的狂言后,悄悄站在屏风后面的小赵竟不由自主地走了出来,仔细欣赏他的书法。其实米芾得以在高手如林的北宋书法界称雄,得益于他扎扎实实的功底,从二王到颜柳,他都曾经一丝不苟地临摹和揣摩,尽得前辈精华。
米芾、黄庭坚、苏轼、蔡襄被尊为“宋四大书家”,而“米黄苏蔡”中的蔡,原为奸臣蔡京,后来因人废字,换成了蔡襄。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书中评论道:“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余子莫及。”由此可见米芾在北宋书法界已执牛耳。当时书坛公认,“(米芾)其体势俊迈,为苏、黄、蔡三家所不及。”米芾曾自称,他的书法其实是在于“刷”字,而刷的乐趣就是要“运笔迅劲”的快感。相比而言,苏轼“画”字,黄庭坚“描”字,蔡襄“勒”字,都没有米芾的大笔一刷来得酣畅淋漓。
第一山碑
遍布南北
中国享有“第一山”之名的大山不下廿座,其中立有米芾“第一山”石刻者有十余座:山东泰山、河南嵩山、江西庐山、湖北武当山、四川峨眉山、陕西终南山、浙江杭州吴山、江苏盱眙南山、江苏南通狼山、四川富顺钟秀山……
“第一山”三字是米芾的榜书杰作,千年来为世人所称赞,但屡遭翻刻。各地的“第一山”都有自己的证据,大家都在争抢米芾的知识产权,纷纷说自己真而别处伪。各地“第一山”碑石的共同点,就是将三个字放大,删去题诗,仅留米芾名款。
“第”字运笔极其流畅,一气呵成。远观,米芾豪迈的笔意在此尽显癫狂之态。细看,字体结构十分严谨、笔画间架极为得当、疏密配合恰到好处;“一”字则壮硕遒劲,多处露有飞白。米芾定是饱蘸浓墨,以快笔“刷”字而成。单单一横就变化万千,极显其笔下功力。三字中,笔画最多和最少的两字排在一起,但“一”字并不因笔画少而显得单薄;粗犷的“山”字稳重坚实,牢牢托起其上二字。
四川富顺是中国井盐的发源地,富顺英烈刘光第与谭嗣同等并称为“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六君子”先后在菜市口就义。刘光第拒绝跪下受刑,他的头颅落地而身躯“挺立不化”,围观民众无不惊心动魄,当场点起香蜡烧起纸钱为他招魂。富顺钟秀山最为刘壮士喜爱,山上也有“第一山”碑。清人陈祥裔在《蜀都碎事》写道:“富顺县治后山上文昌宫,有米元章题第一山三字,字大如轮,遒媚可爱。”据说,峨眉山的“第一山”碑就是依照富顺碑的拓片翻刻而成,而富顺碑是否也从别处翻刻而来,就无从知晓了。
“江苏第一山”原名南山,在江苏盱眙。宋绍圣四年(1097),米芾到涟水出任知县时,乘船从洛阳南下,经过洪泽湖畔淮河边的盱眙,九峰连绵的南山是他南下后所见到的第一座山。山虽不高,但他登临后仍诗兴大发,吟出《第一山怀古》:“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横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当地僧人顺势奉上纸笔,米芾挥毫录下了苍劲飘逸的诗篇。诗中的“第一山”三字被放大而摹刻到石碑上。这桩雅事,从北宋地方志和此后的文人笔记文学中均有详细记述。遗憾的是,原刻诗碑早毁。
盱眙南山现存碑刻,实为清乾隆帝命盱眙县令按照福州的第一山碑摹写翻刻而成,据说与宋原刻碑大不相同。宋刻米芾题写的东南第一山的字径约有六七寸,而且《第一山怀古》七绝在旁边。现“第一山”虽存,但题诗已不见。若原碑尚存,估计无山敢与其争。南山现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
朝阳洞秀 抗日军兴
武当山云雾缭绕层峦叠嶂,有秀丽的自然景观。七十二峰雄奇峻秀、三十六岩峭壁陡立、二十四涧飞瀑湍流、十一洞云蒸霞蔚、十石玄妙疏朗、十池平静如镜、九泉清冽甘甜、九井寒气逼人、九台清幽奇特、三潭深不见底。元人诗曰:“七十二峰接天青,二十四涧水长鸣”。由于地质构造变动,武当群峰均略有倾斜,朝向主峰方向拱卫环绕,形成“七十二峰朝大顶”的众星拱月、万山来朝之势。明代徐霞客留下“气吞秦华银河近,势压岷峨玉垒高”的诗句。武当自然也有许多关于“第一山”的诗词和传说,
酷爱奇石的米芾生在湖北,据说他身临鬼斧神工般的武当仙山幻境时颇有感触,便在山上朝阳洞前挥毫疾书,留下灵动鲜活的“第一山”三字。其动静结合的创作灵感来自三处:赏朝山美妇发髻盘起的秀美仪态,观山溪中水蛇款款游动的自在形态,见月下老道不动如山的静定姿态。百姓打油诗赞道:“美人绾髻不用簪,第字好像青丝盘。游龙戏水一最好,仙人打坐写成山。”
许多翻刻摹写的“第一山”,笔意和气场就弱得很。譬如,庐山变竖为横的黑漆匾额上,“第”字竹字头的连笔勾勒,被描得好似男人冠帽一般,全无“美人绾髻”的秀雅之气。最后一撇则更是败笔,短而无力,使整个“第”的间架结构出了问题,好像要向右边倒下去。古碑和拓片上,第字的末撇均为长撇,这是米芾挥刷运笔的风格。而支持庐山为第一山的江西人则辩说,武当“第一山”碑是雍正二年(1724)由武举人李柏龄延请工匠翻刻的,先在朝阳洞旁,后迁至玉真宫。
朝阳洞的另一批武人,也在两百多年后为武当留下了传奇。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捷次年,登临武当,勒石刻铭,并振臂高呼“振军经武”。“振军经武”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子姑整军而经武乎!”
在“保卫大武汉”失败后,日寇溯江而上攻陷了武当山下的军事重镇老河口。在均州的黄埔军校第八分校的学员兵们奋起抵抗,阻日寇于汉江边,进而确保鄂西北和陕南的安全。当年,驻守武当山抗日将士的军粮有玉米面做成的“黄金塔”,这形似窝窝头的尖形高庄馍馍也是朝阳洞道士的传统食物。
如今,瞻仰抗日先烈的遗迹已成不可能,因为拦汉江而修建的丹江口水库将均州全部淹没,甚至包括许多武当山宫观。连“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都要为“南水北调”让路,其他古迹的命运可想而知。若没有真武保护着武当的自然环境,北方人能喝上清冽的丹江口汉江之水吗?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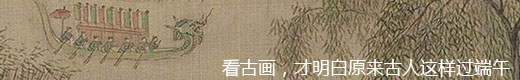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