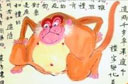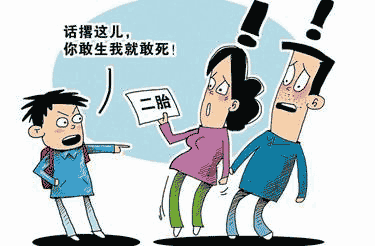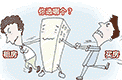作为桂林画家,户外写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甲天下的山水不仅仅丰富而充满魅力,更重要的是它遍地都是,有时候甚至推开窗,就可以看到让人陶醉的美景。可惜的是一如幸福的人没有故事,虽然如今的画家们十分努力,乃至沉溺于写生,但对写生的理解也往往会因拘泥于物象而无法提升艺术水平。这个艺术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以前晋简文帝说:“会心处不必在远”,一时成为隽语,但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写生还是必要的。只不过近代以来,由于写实风气的过于盛行,写生作为绘画学习、乃至创作的一个手段被无限推崇,从而使大家对写生的真正含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解。在科技主义思潮覆盖一切的时候,中国画界需要一些契合点来迎合西方艺术思潮,无论是反对传统的,还是捍卫传统的,都有一种明显的或者隐晦的文化自卑感,这就是对中国画写生产生误解乃至迷信西方写生概念的根源。
西方人写生是基于一种所谓忠实的和准确的再现自然,实际却是即不忠实也不准确。因为即使研究光的技法再高超,也不能把握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规律,就是变化。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西方哲人都说了,人一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那么,西方艺术家再努力,也不可能解决对象的流动状态,于是,他们的艺术形态最终会进入意识流,会进入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领域,在此他们试图完全摆脱形的束缚,以为以此可以把握艺术的真谛。可是,孔子早就说过:过犹不及。且不说这些所谓的概念艺术也没有完全摆脱形式,它们对世界的理解都是偏离了正确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艺术更不能说是高明的了。
不能否认的是,写生在中国画的学习和创作中,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从荆谷子“写松数万本”,到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董其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乃至现代诸位绘画大师,莫不重视写生,视其为不可或缺的绘画手法。这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理解呢?
让我们先从字义上逐步来理解。“写”,《说文》上说是输的意思,“生”,自然就是生机。于是,写生的真实含义在中国文化中就是输送、实际就是抒发对自然生机的认识。这个认识自然是规律性的,也就是总结性的、程式化的。脱离了规律的认识,显然不能明白生机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规律,这要求艺术手法要尽量简约,惟有去繁求简,才能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同时这个认识也是变化的,因为生机是活态的,而非静态的,它自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艺术创作要尽量内涵丰富,惟有外简内繁,才能令人流连忘返;更重要地是这个认识也是整体性的,不发生变化的,因为以“不异”的观点看世界万物,没有任何差别,这就要求艺术的主旨要尽量的稳定,不发生动荡,艺术的境界追求是恒定的,在中国画来说,就是“道”。
之所以强调“道”,是因为现代人写生,往往把“生”理解成生物,即把对象固体化,形式化,这就背离了生的本意,理解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是审美观的错误造成的,审美是一种情绪化的感情,不是科技技术,不能用透视、光线、比例等来衡量,虽然形的理解也很重要,但对于神的感觉还是要靠神来体会,不可能用形式能完全体会神,两个领域虽然有交叉,但却还是有一丝区别,区别就决定了一切,一如鸡和人的基因差别不超过百分之一,但就是这一点差别,人和鸡不一样。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写生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它是主观的。因为理解“生”只能靠来自内心的呼应,艺术家的精神是体会生机的最终工具,一如流水,水“止”才能成“鉴”,流动的水是无法照见人的影子的。于是,人的精神要能知其所止,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对于世界的认识要从道的角度切入,而不是物的角度切入。从这层意义上,就能理解古人为什么说画如其人了,因为一个人的修养高低决定了他对道的理解的程度,决定了他面对自然万物的时候能理解到什么,从而使其艺术表现能力的高低也显露无遗。例如人人都看梅花,每个人的认识一定是不一样的,至于那位“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的尼姑,她的感觉却是完全不同于常人,脱离了形式,脱离了声香味触法,直接理会到那一切生机盎然之后的推手,也就是“道”的存在。于是,写生就是抒发艺术家对“道”的认识,一如庖丁解牛之技,“非技也,实道也”。
所以,写生需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如果把自己当成照相机,复印机,以为非此不能展示对自然的真切认识,显然是自我作践,不能掌握艺术的钥匙。同时,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我们必须也认识到写生也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在大自然里熏陶,忘却了红尘滚滚,使自然天性真诚流露,当然也是一种提高修养的方式,而且更加直接和纯粹。从这个角度看,写生的前提:必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是否就显得多余呢?事实上,问题不在于前提的设置是否合适,而在于写生的时候,艺术家的心态是什么样。
无目的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没有目的性,请问你在写什么呢?求“道”就是最大的目的,忘“形”是基本的要求。于是,写生实际就是写意,写虚,写天地万物运行体现出来的汩汩生意,一枝桃花,一片山水,都给我们以精神的震撼,或者感慨美丽,感慨伟大,感慨力量,感慨生命,都是从这一片生机上展开的。有意思的是,这无限生机,要靠有限的形体来展示,艺术家写生的目的就是发现大自然用有限的形体来展示无限的生机的规律,从而用有限的绘画语言来展示无限的境界。
不过,写生中最大的问题却是出在艺术家有太多的目的。且不说那些很多掺杂了宣传和利益的写生活动,就是学校里组织的学生写生,也往往要求学生注意表现这,注意表现那,急于去表现和发现,却没有一个要求学生放松精神,先充分体会大自然的安逸,体会自然生机的。要知道画画本来就是艺术家内心的生机充沛,自然流露和表现的一种艺术形式,不能扭捏作态,不能勉强硬来。所以,写生最重要的是应该是补充和恢复内心的生机,而不是耗费精神和体力去描写和表现。西方画家往往在老了的时候,哀叹眼力不行了,看不到光线了,没有办法再表现自然了,这是由于他们把画画当作体力活。我想西方画家永远理解不了黄宾虹这样的画家,越老画得越好,甚至眼睛看不清楚了,画的一样好。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成熟的,是写意的,而西方的文化是年轻的,是写实的。
成熟的文化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从简,于是对“道”的理解就是“易”,尽量简单化形式,写生的目的也是洗尽铅华,淘汰一些多余的形式,体会出那个永远不会变化的“道”来;年轻的文化当然是求新求细,力求了解更多的未知,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把握一切。写生的目的当然就是尽量精确和真实。至于哪种方式更适合中国绘画,我想还是让历史来验证吧!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所谓的精确和真实究竟有多少意义呢?对于体悟大道来说,如果写生成了复制自然,也就不用指望这样的写生经历会有多少有益的帮助了。
从具体的技法上来说写生,实际不可能有人能完全说清楚,只能简单说些我的体会:在已经对既有的传统艺术技法和程式有了相当的了解的前提下,写生时应注意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则:
首先是要学会移景。就是把不同的风景集中在一个画面里,甚至一座山的不同侧面是来自不同的对象。移景的作用是要做到以我为主,放弃自然先入为主。
其次要学会简化。所谓的简化就是画出重点。不用把你看到东西事无巨细地体现出来,这就是规律性认识,一来明了结构的构成,二来把握和印证对道的认识。
第三是要放松心态,让自然融化自己的精神,才能体会到生机的运行。惟有精神上能放松,才能写出自己的感受,才能增强自己的修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三个原则不分主次,互相融合,如果机械地理解和运用,显然也是不对的,总之,就是把握好尺度即可。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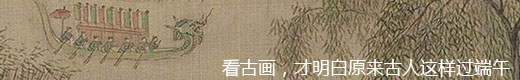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