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種幻象
2015年伊斯坦布爾雙年展的戶外展示現場2015年伊斯坦布爾雙年展的戶外展示現場
原標題:卡洛琳:藝術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種幻象
來源:東方早報 朱潔樹 李亞迪
卡洛琳·克裡斯托夫-巴卡捷夫是雙年展領域的關鍵角色,曾被譽為當代藝術領域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不久前在上海參加國際雙年展協會論壇時,她接受了《藝術評論》專訪,出乎意料地表達出對於藝術世界的悲觀情緒,“藝術講的是一種普遍性,或者說是人類共同的美學理想”,但是在現實中,由於文化、語言的隔閡,“這種普遍理想是無處安放的”。
卡洛琳·克裡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是雙年展領域的關鍵角色。她策劃過2008年的悉尼雙年展、2013年的卡塞爾文獻展、2015年的伊斯坦布爾雙年展。2012年,她曾經被《藝術評論》(Art Review)雜志評選為當代藝術領域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
不久前在上海參加國際雙年展協會論壇時,她接受了《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的專訪。出乎意料地,她表達出對於藝術世界的悲觀情緒,“藝術講的是一種普遍性,或者說是人類共同的美學理想”,但是在現實中,由於文化、語言的隔閡,“這種普遍理想是無處安放的”。
卡洛琳近年頻頻受邀參與中國當代藝術獎項的評選工作,對中國當代藝術家有不少了解,但她依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讀不懂中文的藝術雜志,也無法獲知中國當代藝術的真實情況,除非把它們翻譯成英語。”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清醒的意識,讓她習慣於時時換位思考,從不同的文化、族群的角度去審視世界,甚至超越人類中心的思想,“人們隻有逐漸放下‘人類中心論’的包袱,嘗試多樣視角並接受世界的多樣性,未來的世界才有希望之光。”
藝術評論:2015年,你策劃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伊斯坦布爾無論在地理還是歷史上都處在一個相當獨特的位置,因為它連接著東方和西方。在策劃雙年展的時候,你是否會關注社會與政治背景?
卡洛琳:我以語言為例來回答。比如我現在必須說英語,因為英語是藝術界的世界語言,但英語意味著誤解。我住在意大利,工作在意大利,日常語言是意大利語,但我和你們說話的時候需要用英語,而不是意大利語。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時候也要講英語。我認為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全部要說英語。這或許算是我的回答。
從語言的角度看,我們生活在一個統一化的世界,全球化的語言是英語,既不是漢語、俄語、意大利語,也不是土耳其語,甚至藝術界的通用語言也是英語。但是我們生存的世界又十分動蕩,政治上的紛爭此起彼伏。我們要思考的是,這個由一種語言統一起來的世界,同時又是破碎的、分離的、不穩定的,藝術世界亦是如此。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藝術就是一種幻象,它是不真實的,像一場夢。因為藝術講的是一種普遍性,或者說是人類共同的美學理想,以及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的討論,但現實中這種普遍理想是無處安放的。
比如英語,它雖然是一種全球語言,但它是虛幻的,現在雖然我們都在講英語,但你們不了解我,我也無法了解你們,因為我們的母語並不是英語。就像羅馬帝國覆沒的時候,從蘇格蘭、北非到土耳其,所有的人都在講拉丁語,然而沒有人真正理解拉丁語。他們用拉丁語交流,但是他們互相並不了解。這就是當今世界的現狀。
在中國,語言也很有意思,十幾億人口竟然全部講漢語,這也從側面証明了藝術世界的全球化其實是一種幻象,因為中國本身就有自己的漢語藝術世界,中國的藝術家們彼此十分了解,而我所居住的托裡諾市(Torino)居民則永遠無法深刻體會。我們讀不懂中文的藝術雜志,也無法獲知中國當代藝術的真實情況,除非把它們翻譯成英語。
我們生活的世界其實並沒有真正的知識交流,雖然進入數碼時代以來,迷信數碼科技的人們總宣稱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知識可以隨意流動融合。他們談論跨學科與多學科,但其實我們甚至不能在一起談論早餐,那又如何在一起談論哲學與科學呢?
我對世界的現狀並不樂觀,藝術世界同樣存活在虛無的理想裡。
直白點說,策展的時候我必然會考慮到當地的背景。比如2008年的悉尼雙年展,我定的主題是“倒置”、“革命”和“互換視角”(Revolutions - Forms That Turn)。澳大利亞位於南半球,水池裡的漩渦不是逆時針,而是順時針轉動的,因此這次展覽將會探討“倒置”的意義。同時,我也強調要以“倒置”的視角看政治。比如,我們一直是站在監獄之外看向監獄裡面,從來沒有嘗試過站在監獄裡面看外面的世界。受父權社會的影響,監獄外的人會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思考:我們必須保護犯罪的人,教育犯罪的人。那麼我在悉尼雙年展的構思——“互換視角”,便針對這一姿態提出了疑問:監獄裡的人是如何看待外界的?
這構思與澳大利亞的政治有關。眾所周知,澳大利亞的建國功臣其實是來自英國的罪犯。18世紀最初從英國來的罪犯,建造了自己的國家,又把罪犯關進了監獄。這涉及到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關系。黑格爾曾在奴隸主的問題上提到過同樣的身份調轉關系,即奴隸主原本是受虐者,成為奴隸主后便成為施虐者,弗洛伊德和拉康也表達過類似觀點。此外,雙年展與社會背景有關是因為有許多當地的藝術家參與其中。
我在土耳其主持伊斯坦布爾雙年展時,常常會想到這個國家的過去。它曾經是個馳騁東西的帝國,就像古代中國一樣,奧斯曼帝國的疆域非常遼闊,從巴爾干半島、非洲北部一直延伸到敘利亞。然而輝煌的帝國一日崩潰,最終萎縮成一個小國。之前土耳其國內有龐大的希臘群體和亞美尼亞群體,后來希臘人被遣散,亞美尼亞人遭到了屠殺。
這是一個偏執與妄想的故事:當一個國家失去了外部的疆土,就開始害怕內部的敵對勢力,社會內部關系就會變得非常緊張。所以伊斯坦布爾的雙年展是關於綜合征的,我策劃的雙年展從來不直接與當今有爭議性的問題關聯,它們總是回顧過去的政治和歷史,努力吸取歷史教訓作為當今政治的前車之鑒。而且我認為歷史是重復的,當今的局勢都能在歷史上找到類似的圖景。我擅長以考古學的方法來看當今世界,因此當你提到現今局勢,我會用過去來回應,因為在我眼裡過去與現在是一體的。
另一種常用的手法是心理分析法。心理分析是關於成年人與剛出生時原初混沌狀態的關系。四五歲之前,我們尚未成為有意識的主體,隻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當時是什麼心理狀態,我們自己無從得知。我們隻有在與這種混沌狀態的聯系之中才能構建出自己的主體性。這種論調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有關,而我在實際策展中也會十分注重混沌狀態的表達。
此外我認為中國本土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家,比如汪暉,他提出了“齊物平等”的觀念。據我所知還有位中國女詩人,在“文革”中受過壓迫,她用英語寫作,現在非常有名。或許我們應該收回向外的目光,關注我們所立足的土地。
藝術評論:中國現在約有13個雙年展,分布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如果邀請你來擔任策展人,你會有什麼建議?
卡洛琳:首先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精力,因為做了太多雙年展,現在有些累了。但我喜歡到處旅行並學習。通過學習與當地建立互動,才能找出與當地文脈、當地人群之間的聯系。我覺得中國藝術界很有意思,我受邀擔任過不少中國藝術獎項的評委,例如前不久的AAC藝術中國獎項,我把獎項頒給了劉韡。參與這類評選的時候,我會接觸不少中國藝術家,所以我對於中國藝術界算是小有了解。在我看來,徐冰是非常優秀的藝術家,他是年長一代的藝術家,也是很重要的藝術家,最近他的作品尤為精彩。我知道他最近正在利用監控攝像頭拍到的影像進行創作,這些影像被上傳到網絡上,就像是互聯網的垃圾,他會將之重新組合,形成自己的作品。我最近拜訪過他,非常喜歡他這件作品。另外我也很欣賞彭禹和孫原,當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在意大利結識了蔡國強,還有宋冬,他的作品《白做園》(Do Nothing Garden)也非常優秀。我還認識很多年輕的藝術家,有名氣較大的曹斐,還有更年輕的一些。
藝術評論:現在中國有些藝術家堅持傳統藝術,不與國際交流,幾乎不為外人所知。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卡洛琳:這種現象很普遍,從倫敦、巴黎到紐約,到處都一樣。大部分藝術家只是埋頭做自己的藝術。假設紐約有1萬名藝術家, 那麼大概有9900人都在從事傳統藝術,而其他地區的人對此一無所知。國際策展人在策展的時候不與他們聯系也是正常的。中國的策展人也會這樣。
藝術評論:另外一些當代藝術家,他們的藝術似乎更容易在國際上引起反響,而非當地。你認為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卡洛琳:這是一個誤區。如果街頭的群眾不懂數學或物理,人們覺得很正常,但如果他們不懂藝術,人們會覺得奇怪。人們普遍認為藝術是一種見仁見智的感性存在,不需要專業知識,這其實是不對的。藝術、文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需要專業知識。
最好的文學家,比如英語世界的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和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他們的小說在他們自己的時代是無法被理解的。我想說的是,高雅藝術就像自然科學一樣,有足夠的准備和積澱才可以理解。如果無法理解,那就需要學習和研究,就像需要學習數學或物理一樣。
藝術世界有不同的層次,每個層次有不同的編碼或者公式,而藝術就像語言,有精通者也有入門級,隻有達到一定高度(例如藝術家)才可以用藝術說話。普通人可以理解傳統藝術,因為傳統藝術已經出現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但當一種新的藝術出現的時候,人們會覺得突兀,無法接受。
回到雙年展的問題,雙年展就像一個分裂的怪獸,它一方面用高雅的藝術語言發聲,但迫於資金問題,又需要面對大眾,融合大眾可以理解的藝術,讓更多人參與其中。
我可以平衡好二者關系,部分源於我是一個母親,我會經常反思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關系。我教孩子讀書認字,但他們教我如何理解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基本關系。這一點對我的策展很有啟發性。假設孩子隻有桌子的高度,他們的視角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教我去思考人類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在當今藝術世界,藝術家們受社會或政治的影響,更傾向從種族或經濟發展角度去思考,卻極少去反思不同人(像兒童、老人或殘疾人)的心理狀況。我常常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整個世界,從貓、狗甚至蜜蜂的視角去體會,世界上物種如此多樣, 每一種生物都有自己眼中的世界。但是西方文化長久以來都以人為中心,認為人站在地球生物的頂端,統率全世界,這種觀念實在荒謬﹔東方文化受禪宗影響,較早懂得萬物有靈以及慈悲心理,因而謬誤或不如西方嚴重。
人們隻有逐漸放下“人類中心論”的包袱,嘗試多樣視角並接受世界的多樣性,未來的世界才有希望之光。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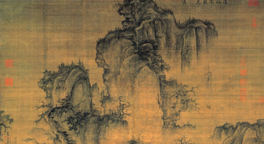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