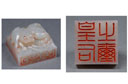絲玉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那些活躍在其中的策展人與藝術家、畫廊、媒體等處於一線的力量,同時面對著中國當代藝術全面資本化的大時代。身在其中的“第三代策展人”在接受著大大小小、重要或不重要的展覽時,面對的最為核心的拷問依舊是:作為策展人,是否可以推動藝術史的發展,是否可以在展覽的自身系統中有所作為?
對新一代策展人而言,技術問題逐漸成為被批評的對象,在完成技術批評的那天,或許才能迎來人們對這個行業真正的尊重。從栗憲庭、費大為、高名潞等第一代策展人,到皮力、邱志杰等第二代策展人,中國當代藝術經歷了整整30年的時間。當我們把目光聚焦當下時,“第三代策展人”這一概念的提出卻遭到了質疑。比如,劃分的依據只是根據年代和時間,便沒有了針對策展人本身的問題性﹔如果根據年代來劃分,那活躍在其中的策展人卻依然有年齡懸殊的現狀。於是,“第三代”的提出,好像除了把當下的策展人整體化之外,還提前在歸納總結中結束了這個時代。在深入策展人的工作內部,並呈現問題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實則是他們對藝術的見解,於展覽的專業程度,以及人的品格、性情和氣質對展覽產生的作用。
從2014年美術館層出不窮的策展人扶持計劃開始,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策展人愈發的關注,實則是對現狀的不滿。由於近幾年展覽的過度商業化,以及大部分的展覽並無作為,以至於早在前幾年便已有人宣布了策展人時代的消失。當我們試圖談論“第三代策展人”的作為時,首要談論的還是策展人在職業化進程中面臨的種種。職業化,是策展制度形成后對以策展為生的策劃人的描述。在極度商業化的中國當代藝術中,策展人對“職業化”的談論卻是相當謹慎。
當策展成為一種職業時,其中最難處理的便是如何以此為生,但又不淪落至市場的附庸者?面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現狀,每個人都很難置身事外地給予什麼意見。如果職業化在今天並非問題的矛盾中心,那麼如何做一個專業的策劃人卻是正中要害的提問。
比如,從展廳之內對地板、燈光、牆面,以及整體視覺的控制和把握,到展廳之外,宣傳、講解和各種關系的調和,是否可以在每個展覽中都做到精益求精?除了這些需要親力親為的執行事項,是否可以寫出一篇沒有邏輯錯誤、語言簡明、准確且有深度的策展手記?單單這一項,就足以把許多以玩弄文字、濫用概念的策展人拒之門外了。
當然,我們與策展人談及專業化的時候,並不能從他們的表述中得知這些“專業化”能夠在真實的展覽現場實現幾成?對展覽一分一毫的用心謹慎,不在於策展人是否專業,而在於一份專業的態度,如果這個態度裡還有一絲對藝術的敬畏之心和對展覽本身的念想,即便沒有100分,也在去往100分的路上了吧。
今天,我們還需要策展人嗎?這是一個縈繞在我腦海裡近兩年的問題。兩年前,我和友人在談論未來的“策劃人”該何去何從時,從藝術家的需求、藝術生態的狀況、策展人的作為三個方面分析,悲觀地得出一個結論:在遍地都是策展人的今天,那曾經屬於策展人的榮耀卻在不斷消失。這種榮耀,曾幾何時也隻在前輩的言談中感受到一二,無論是談及“85美術新潮運動”時理想主義的熱情,還是說到上世紀90年代當代藝術的步履維艱,藝術家、策展人和一同走過的那些展覽,都印証了中國當代藝術向前邁出的每一步。
有策展人調侃道:“策展人的理想狀態是導演,實際狀況是包工頭。”這的確是許多策展人不斷抱怨的現狀。一個好的展覽,從思想的出現到感覺的爆發,策展人在其中從來都是不遺余力、全力以赴的。隻要你投入其中,便是博弈和斗爭的開始。在力量的角逐中,有些人為名,有些人為利,有些人則為藝術家、為藝術、為展覽。所以,能夠獨立在商業之外,像大師一樣純粹地做個展覽,應該是這個時代不可為,卻一定要努力讓之可為的事。
理想很偉大,現實很殘酷。除了自己,沒有人還會真的在意你是否擁有高貴的品格和對藝術基本的尊重和道義。那些冠冕堂皇的話,說多了也是無益,語言和行動的縫隙間是越來越職業的表白,帶有表演性的勤奮和越來越沒有進取之心的虛偽和懶惰。過眼煙雲般的展覽,浪費了太多這個行業裡的資源,它們既不能為好的藝術家打開一扇門,也不能對藝術的發展有一絲一毫的推進。當代藝術領域中,大部分策劃人的展覽最終隻能也僅能成就個人的歷史,而無法為藝術的發展或藝術史的發展給予真正的推動力。
在今天,一個好的作品,在一個錯誤的空間,最終也隻能成就一個無效的展覽。如何實現作品的“在場”等於藝術家的“在場”,同時又能讓展覽的“存在”成就藝術家和策展人同時的“不在場”,是一個好的展覽最難把握和控制的地方。
當我們完成展覽的技術批評的時刻,或許才能迎來人們對這個行業真正的尊重。而在展覽之外的空間中、在當代藝術生存的環境中,這些策展人的態度和作為依舊承擔著讓整個生態有所好轉的責任。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