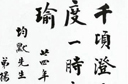漫畫中的黃永玉(資料圖)
本文摘自《文星街大哥》,劉一友 著,漓江出版社,2007年9月
與永玉交往,所得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的雄強尚義和幽默通達。這既是他鮮明的性格,也是幫助他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雄強尚義,是鳳凰人的普遍性格,這與城區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關,更與當地數百年間都是大湘西一座軍事重鎮有關。沈從文曾將這種性格直呼為“楚人性格”。鳳凰這地方並非滿城武俠小說中那類整天東游西蕩,找岔子打群架的男女,鳳凰男子大都是戰士,社會要求他們具有楚辭《國殤》中所提及的“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的勇士性格。
永玉的雄強,除家鄉傳統影響外,也與他獨特經歷有關。童年時代漂灘鑽洞,打架逃學,待到外出謀生,顛沛流離,艱辛備嘗,再之后,則長期在政治運動狂濤中過日子,種種折騰,養就了他不畏艱險,遇事沉穩,寵辱不驚的氣概。他說過:“我們鳳凰人,面臨大事時反而安靜下來了!”他不見風駛舵,唯唯諾諾,惹翻了,拍案而起,“不為瓦全”。
永玉不像當地祖輩那樣結成團伙,去打英國鬼子,打日本鬼子。他從事藝術,孤身一人,去打誰呢?打擊小人,又常常下不了手。愛打獵,也不曾遇過老虎豹子。因此,他的雄強,在主動進攻敵人方面乏善可陳。倒是遭人打擊,被動抵抗的機會甚多。曾經有那麼二十余年,屬於知識分子經常挨打受罵,飽受欺凌的時期,也就在這種場合裡,永玉的雄強有了充分表現的機會。
一次,受“四人幫”鼓動起來的外來的造反學生,到中央美院來看大字報之后,決心要通過觸及永玉的皮肉來觸及永玉的靈魂,當眾對他進行一番羞辱,用皮鞭??啪啪地抽打他。永玉任他們打,就是不叫喊,不求饒,不掙扎,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都浸透了,他仍然頑強地站著,默默記著鞭子落下的次數,二百二十四下!回憶這事的人說,這真是一種震懾人心的雄強。那年代,對知識分子來說,活下來真不容易,一些人就活不下來,著名的“人民藝術家”老舍,被拳打腳踢之后,便投北京太平湖自殺了。人們道路以目,永玉偶爾與沈從文在東堂子胡同相遇,誰也不敢停下來說話,怕被人見及檢舉,惹出是非於對方不利,只是擦肩而過時,沈從文匆匆講了三個字“要從容”!這就是我們湘西人、鳳凰人在危機面前的態度。永玉則把當時十分流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一口號改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用以激勵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千萬不可因活比死困難時,一時軟弱,死了,讓別人開心,還可為你加上一條“自絕於人民”或“畏罪自殺”的罪名,隻能是“不怕活”,活下來等待“第二次解放”。“四人幫”倒台后,一次永玉同廖承志一起吃飯,廖問:“說說,你怎麼跟‘四人幫’進行斗爭的?”永玉答:“沒有,我只是沒有求饒。”
永玉尚義,不過這義的內涵太寬泛了,根本一點,義至少是“利他”的。前面提及的鳳凰人鋤強扶弱、知恩必報,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應當都屬一種古典義行的表現。
在朋友間,義有著廣闊的展現空間。有人問永玉,這輩子有何特別的感想。他回答:“遇見了許多好人”,“也錯過了許多老人,因為動亂,自顧不暇”。他因對曾幫助過自己的長輩和朋友不能一一報答而深感不安。幾年前,他得到六段從原始森林中弄來的巨大楠木,如此珍貴材料,用作什麼好?最后決定在上面刻了《詩經?大雅?生民》中一小節詩,寫的是后稷的傳說,后稷生下來后,被拋擲於陋巷荒郊,多災多難,幸得牛羊飛鳥和伐木者喂養庇護而得以成長。永玉用這比照自己幸得師友諸多關愛而有今天,他要以此方式對他們表示深切的感念。這六段巨柱,現如屏風般並列於北京萬荷堂的正中。
至於仗義的事,可說的也就太多了。且說近期一件,1969年,中山大學八十歲的國學大師陳寅恪,“文革”中不堪數年的欺凌折騰,心力衰竭去世,骨灰一直寄存在廣州火葬場,三十余年過去,仍未能歸葬故裡江西。兩年前,永玉得知此事,憤然為之呼吁奔走,還拉了過去在江西作過領導的一位朋友參與,不久前總算有了結果,陳終於歸葬廬山。陳寅恪的女兒見永玉如此熱心,還以為永玉曾是自己父親的學生。其實,要說有什麼關系,其一是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光緒初年在鳳凰任過辰沅永靖兵備道的道尹,后來又當了湖南省的巡撫,推行過新政。其二我想永玉對陳寅恪提出的一個學人應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張大約深表崇敬。如此而已。
最近永玉幾次談及故鄉長輩對“賤貨”嗤之以鼻的事,認定也是對孩子的一種教育,給了孩子一把十分牢固的道德尺度,做人一定不能做“賤貨”。何謂“賤貨”?我想無非也就是鳳凰人常說的“不值價”,沒分量的人。它的對應面當然就是雄強尚義了,試想“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何“賤”之有!
雄強尚義確是好事了,不過,它也有兩重性。雄強尚義的人坦坦蕩蕩,見不順眼的事就要直說,一直說且要說完,無所遮掩,這就不免落得個“脾氣丑”的壞名聲。永玉的干爹朱早觀將軍,當年在延安被組織上分配到彭德懷的司令部去工作,彭德懷自己脾氣夠“丑”了,還嫌他“脾氣丑”,不要。幸得王震在湘西待過,知道湘西人脾氣“丑”是一種直率,其深處是一種忠誠,因此把他收留到三五九旅當了參謀長。
永玉不是也常被人在背后說“脾氣丑”嗎?這“脾氣丑”一旦落了個“抗上”或“抗革命造反派”的罪名,其危險也就可想而知。
更何況,雄強尚義,坦蕩直率,如遇上陰柔小人,他可以很容易摸清你的底細,而你以己量人,認為別人再壞也不會那麼壞,豈料他恰恰比你想的更壞,這種情況下,你就得受到他穩、准、狠的打擊了。這方面,永玉吃過許多次虧,隻因稟性難移而屢教難改。東漢一則民諺有雲:“直如弦,死道邊﹔曲如勾,反封侯。”湘西人,特別是鳳凰人值得警惕!
關於自己的性情
與永玉的一次談話:
你提及鳳凰人的游俠精神,雄強尚義。講義氣,是種真誠,實際包括施恩和受恩兩個方面的態度。受恩必感恩,則是“滴水”和“涌泉”的關系。
我們湘西人,鳳凰人,別人常憑直感認定可靠。
我不是黨員,平日也不大與人來往,可是,“文革”中,被關在牛棚裡的老人家,有要傾訴的,常找到了我,包括常任俠、吳作人、劉開渠這些老藝術家。那時,我說自己患有傳染性肝炎,造反派隻好將我另外關在一間教室裡。吳作人在美院附中地下室被斗爭時挨打,回來告訴我,要我記住,如果他死了,要我作証。又,有造反派中的一派逼劉開渠拿了一筆錢,另一派要劉交代實情,以利於攻擊對方,劉開渠掃地掃到關我的教室窗戶邊,悄悄問這兩邊擠壓如何是好?我說,你立即把實情告訴不得錢的那派,讓他們去出大字報就成了。一天,李可染告訴我,有個學生上台斗爭他時,得意地附在他耳邊說了句:“現在,是我報恩的時候了。”他們把自己的難處和委屈對我講,因為認定在那種特殊情況中,我是可信賴的。
肖離、肖鳳夫婦,家裡遇到什麼事,如房子問題,犯難時,便說:“找永玉幫忙考慮。”我不知道自己還有著這方面的本事。
“文革”中,在干校時,有一派常想找我麻煩,我有時眼睛也橫一下,引起一造反派成員警惕,在背后對人說:“黃腦子不動尚可,一動麻煩就多了。”我們湘西人,一般情況,常常是硬碰硬,但要採取大點行動時,反安靜了。我這是受王伯影響的。我在《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中寫那個王伯,你知道的,他說打不贏就跑,有了辦法再來對付他。
我不打牌,不賭,我也不喝酒,隻讀書。我們在小學時已談詩論道了,談柳宗元、韓愈,到嚴復、梁啟超,抱負從這裡就萌發了。到廈門集美學校,懂得用圖書館了,接觸到更多的新知識,后來,參加了魯迅領導過的木刻協會,同“左派”的新文化挂上了鉤,從魯迅思想那裡得到勇氣,在信念上,抱負上,都出現了新東西,保証了自己不墮落,不腐化。參加過不少進步活動,但沒有入黨,沈從文不懂,弄不清如何入法,我黃永玉也不懂,心情倒是真誠的。
我也不曾被劃為“右派”,鳴放時,沈從文的看法是:“自己寫不出東西,怎麼能怪人家‘黨’呢?”我則認為,雖然生活困難,待遇低,比過去好嘛,另外,我也認為藝術創作是自己的事,不必去怪別人。
我也曾有情緒激憤的時候,有人勸我多考慮,不要弄壞了關系,他們不懂,對仁義的是非判斷是很快的,赴義難道還要考慮幾天幾夜嗎!
塞林格的《麥田的守望者》裡有一句話:“……聰明人為真理屈辱地活著。”馬克思說:“為了真理,要善於忍耐和等待。”原話可能記得不清,你可去找馬列專家查一下。
隨波不逐流,這並不容易。
藝術家和政治家的關系,尊重對方,也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人格,朋友就是朋友,不為自己私利和親友找別人幫什麼忙,讓別人為難。
面對使自己不快的人事,沈從文完全是忍耐,讓時間去作結論。我則講究寬容,我事多,領域也大,沒時間。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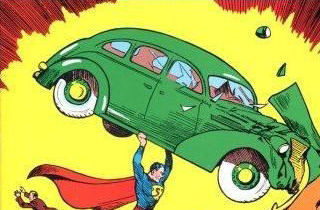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