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自述——我画山水
山水于我,看似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实则与我的性情和艺术取向很近。我性不具体,对于细节很少观察,只是在迫不得已情状下,才发现细节的意义。宏观的、永久的和散漫的思想状态正好指向山水。
我读硕时的研究方向是工笔重彩人物,到新单位后没有条件画人物,讲授的是山水画,于是改画写意山水。很快我发现,画山水比画人物并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还要难——山水画传统太深厚,不易突破;山水形象造型单一,在架构上难以出新意;不如人物画与现实生活结合得紧密,等等。好在我不知难而退,自认为能够入道,而且,我越来越认识到山水在中国画史中何以后来居上的原因。它所涵容的中国文化精神之深和艺术价值之大进一步坚定了我画山水的决心。题材不应该成为羁绊,惟新语言才是艺术再生之根本。于是,我一边探察艺术本质,一边研习传统、观照当代,这样不但不会构成障碍,还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超越程式和他人。我信奉董其昌所说的“一超直入”,也相信通过理论和实践两条腿走路会使这个时间段缩短。2003年伊始,我踏上了山水画探索之路。
开始,我全力地、综合地调动起已有的各种资源——感性的和理性的,逆向的和顺向的,临摹的和创作的。手段尽量地多,目标归结为一点,就是传统图示和传统精神如何与当代视觉经验结合,如何生成具有现代感的新的山水样态。首先从被大众认为“极像”的那种山水样态中跳出,从意象的组织方法上,从惯常的笔墨结构关系中跳出,祛除山水画空泛的、程式化的样态。先破除成见,清空非自我、伪传统的东西,从个人的、对艺术而非对“山水”的感受入手。不怕不成熟,就怕太熟悉、太老套。当然,新的山水形态必须建构在美术史演进的链条之上。
辩源流、定格调、选方向很重要。对于山水画流变史,必须清晰明了。我旨在从历史演进的形态中发现与我设想的现代山水有启示作用的元素。造境和笔墨是山水画的核心,两者密切关联于画家的修养。而修养外显为对山水画史洞见所涵养的“胸中丘壑”的营构之清新程度上。我力求把握形式流变的几个关键时期、关键人物和几种关键形态,把握住它们,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就显现出来了。从五代的荆、关、董、巨到北宋的李、范、郭,从南宋的李、刘、马、夏到元代的黄、倪、吴、王,从明四家、清四僧直至近现代的黄宾虹、李可染、陆俨少、傅抱石、石鲁等大家,乃至当代优秀山水画家的作品,我尽可能心存其影、胸留其魂。研究他们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领会他们的语言创造和中国画传统精神的关系,比较他们的成就大小、格调高低和历史地位,体察他们的艺术素养、人文关怀甚至生活状态等一系列问题。当时并不显赫和著名的画家也并非没有研究的必要,一些早期不成熟的作品亦可涉猎,虽其“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但稚拙和简约的造境却有启发,尤其对当代那些画得熟练却近乎油滑的画家而言,不失为一剂良药。
要有问题意识和学术品格——它让你具备了方向感以及集中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能力。当代山水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陈陈相因,缺乏现代感,缺乏学术价值。在创作过程中,我也感到有些矛盾和问题确实不易解决,比如,传统山水审美惯性和当代视觉经验之间的矛盾,画家观念革新与画种规定性之间的矛盾,程式化的传统语言与写生情形下自然形态的转换,个性语言的受众度与认可度等等。解决复杂艰深的问题,非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文化使命感不能为。我之所以采取先跳出传统重围再回归传统的办法,旨在以破求立,以变求常,以虚空求创造,经过几番综摄整合,它已不再是传统形态,而是在中国画核心精神诉求之上的现代形态了。
兴趣的广泛和价值取向的宽泛使我不能长期固守一个阵地,我因此常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也发现了其中的张力和广阔空间。把这些缺点转换为优势,可以实现跨越式进步。至少我认为,在寻找的过程中确立,全面观照和审视各种因素,进进出出,能够增加高度和挖掘深度。不要吝惜体力和精力,尽可能多地进行大胆的实验和探索,让画面具有更大的包容量和文化内涵——具体讲,要有笔墨意味、有形式创造、有明确思想、有核心精神、有自我个性。我对中国画现代性问题考虑比较多,试图从传统中拉出一条能够不断延展的线索,发掘其中最本质和最高妙的东西。中国画的博大精深会使这个过程变成马拉松,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这些动作和实践不是漫天撒网、无所边际的,我在一个设定和觉悟到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尽管是在探察山水艺术的多种可能性,却须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从2003年到现在,我的认识是在变化中,画面也存在不满意的地方。至于画得欠精微或有败笔,我认为先不要把它看作大问题,建立起大的框架,然后完善它、深化它,比缩手缩脚重要得多,也见效得多。胡适先生治学讲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此法亦适用于此。我不相信一幅画会画坏,甚至,我有时故意打破习惯和有把握的方式来画,进入到陌生和无助,所谓绝处逢生是也。超越就是不断否定和修正。但无论如何变异,我基本是围绕一个核心展开,大致的思路是:力求达到一个朴厚、鲜活和清新的境地。在道与艺之间,在物与我之间,在中与西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严谨与放达之间,在沉凝浑厚与灵透秀逸之间寻找恰当的结合点。具体从用笔、使墨以及对笔墨结构的解构和重组中展现新的视觉效果和新的意境,还考虑到山水形象,意象组合,构思构图,意境表达,图示特征,以及黑白灰、笔墨结构的处理方法,等等。
最近,我作画的思路日益具体和明确——将意象融入黑白灰布局的色度变换中,注意留白,凸现传统“计白当黑”之法则,并区分物象间的界限。早期恣肆的用笔逐渐转化为凝滞舒缓的形态,将积墨和渲染渐次置换为具有平面和构成意味的“当代性”,以失掉山水弥漫感、虚迷感等自然特征为代价换取画面语言的结构化,山水之苍茫浑厚转化为清丽简逸。或者说,由客观再现进入语言营构、纯化,关注语言自身的价值。此类似于西方印象派之光色生动的写实性进入到后印象派塞尚分解、结构画面,艺术语言大于现实状态。这样的路径正是西方绘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标志和分水岭。而中国画之语言独立呈现尚未完全,有空间可挖,有文章可作。我坚持的原则是:借鉴西方,但不同于西方。我之语言变异是在亲近中国画传统中简约整体的现代因素(如倪云林作品就极为简约而具现代感),疏离过于程式化的传统外壳的同时,保持意境、诗意之营造。将构成意味的现代感与自然物象有机融合,将丰富的笔墨关系纳入到整体黑白灰关系中,将传统笔墨形态归纳到点线面的节奏组合中。中国画在早期就注重从自然中提取符号和图示,具有很强的图示意识(与同时期的西方比较应该是“高端”和“先进”的),但同时兼顾了图示语言与自然对象的对应、协调与平衡。赵孟頫、倪云林、董其昌、清四僧直至黄宾虹、李可染、陆俨少等人莫不如此。其中黄宾虹在还原自然和观照语言两个方面都走到了极致,所以这两方面决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合无间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不想囿于一个模式。我强调因心造境,因物造境,因材料造境,这是在一个框架内的随意生发,以此寻求山水画重新阐释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虽然我相信要有个人阐释的角度和方式,但我更要求我的表现形式要有可延展性、弹性,就像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立定一个根本,而我越来越发觉这个根本不是现成的形式,更不是固有的模式,而是散落的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的不同构成与组合是形式演化的内在动因,当我们发掘到其内部生长机制后,就可以进行解构、重组和创造了。它充满活力,而非一潭死水,它藏而不露,却可感觉、可驾驭。
我想,不缺少林泉之心,便能够进入林泉之境。一步一步,我会渐次接近自己心目中的审美理想和山水架构。
2006年于北京清华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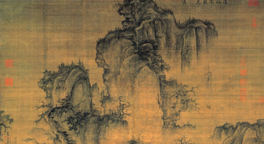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