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墨纵横——陈振濂榜书巨制特展·前言
 |
| “大墨纵横”陈振濂榜书巨制特展展览现场 |
一
“榜书巨制”,是一个复合的概念。
“榜书”大字古已有之,从三国韦诞题榜一夜须发皆白的记载开始,唐宋元明清代不乏人。宋人黄庭坚有诗云:“大字无过瘗鹤铭”,知当时书家心中的大字,与案头小字尺牍相比,《瘗鹤铭》已是大字典范。而米芾善题大字,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明清以降,像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吴昌硕等,皆有许多题匾榜书杰作。近世则如沙孟海师题灵隐寺“大雄宝殿”,并以此驰名于世,即是一例。
“巨制”书法则古并无之。若硬说有,则如北朝《泰山金刚经》或可勉强算之。此外各朝摩崖书也皆可予以论列。但相比之下, 一是这些摩崖文字当时墨书和放大镌刻的关系尚不明晰;二是当时“巨制”之所以会出现, 是基于书法以外的因素如宗教; 三是当时“巨制”在我们心目中的尺度也很难把握。比如相对于尺牍小札或长卷横轴,秦汉碑刻即可算是“巨制”。但与《泰山金刚经》相比,则碑刻又算不得“巨”了。而与秦汉碑刻相比,唐人的“题壁书”如张旭、怀素在寺院酒肆中笔走龙蛇,动辄高墙大壁,又应该算是更大的“巨制”了。另外,“巨制”是作为结果的“巨”,而书写时是否即是原寸的“巨”,又是一个尚难考证的内容。有些大字,明显是写小样再放大镌刻的。不比今天我们写“巨制”是在地上铺大纸写原寸大字。有的每写一笔,要走三四步。这样的方式,恐怕与碑刻、摩崖、“题壁书”之类的形成过程又相去甚远,而很难以一概论列之了。
二
从古代到近代,陆维钊先生与沙孟海先生,是“榜书巨制”书法的卓越实践者。他们的努力,使“榜书巨制”作为一种创作形态走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峰。
陆维钊先生的书论文献传世很少,缺少关于“榜书巨制”的直接论述。但陆维钊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在于,他创作了一系列“榜书”作品,给我们提供了“榜书巨制”的极为珍贵的范例。比如他的对联“天地乘龙卧,关山跃马过”“同心干、放眼量”“齐踊跃、肯登攀”“冲霄汉、起宏图”“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等等,“心画”“第一湖山”等条幅,这些作品其实论绝对尺幅,并不特别巨大,有的也就是四尺、六尺而已。但以陆维钊先生的凌历笔势和沉雄浑厚的气度,在有限的空间里却展现出广阔宏大的墨象。无论是速度、力度、空间尺度,都让人误认为作品至少是丈二丈六的大尺寸,也即是“榜书巨制”的格局。或许更可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榜书巨制”,其尺度当然不可能如今天艺术繁荣时代的尺度。但陆维钊先生正是以他的卓绝才情与深湛功力,为当时十分冷落萧条的“榜书巨制”创作立一标杆、下一转语,从而为那个时代的书法创作史提供了极其难能可贵的一抹亮色。遍观近百年书法史,这一亮色几乎是唯一的、无法取代的,在当时并没有匹敌抗衡者。
沙孟海先生于“榜书巨制”,有一篇名文《耕字记》叙其始末,让我们在研究沙老的大字书法时,有一个极好的文献依据的支撑。与陆维钊先生限于条件又善于“小中见大”的特点不同,沙孟海先生的大字榜书则是“以大写大”,舞如椽大笔,在数丈大纸上,步、腰、臂、肘、腕协同,健步如飞,运斤成风,弯弓蹲马,迅捷优雅,以广大制精微。在当时的书法界,像沙孟海先生这样,以“榜书天下第一”而驰名于世的,亦是绝无仅有,只此一例。
以陆维钊、沙孟海先生为代表的上世纪后期“榜书巨制”书法创作的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世纪初中期的水平,不但是认识水平,还有实际的创作成果水平。
随着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腾飞国家开放,书法中“榜书巨制”创作又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与艺术目标。比如说:陆维钊先生当时住房条件落后,他的挥洒空间只是一张小画桌,而我们今天却可以在礼堂、体育场里纵情挥洒。又比如说:沙孟海先生当时写个丈二斗方“龙”字,提如椽大笔,已是弥足珍贵,在物质上已是尽了最大的极限;但今天我们的“榜书巨制”,可以用五支、十支大楂笔捆绑在一起,以几十米长的尺幅作整堂大书,在物质上也已是不困难而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故尔,今天我们谈“榜书巨制”,其实所赋予它的内涵,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当然也就有了“与时俱进”的问题。亦即是说:今天我们看巨幅作品创作,其尺度与心理期待肯定已不同于以往。但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对古代名家与前贤的时代贡献与宏伟业绩予以高度肯定与评价,并明确指出他们的探险与求索,应该是今天进行“榜书巨制”大字创作在理论上、意识上与实际形式技法上的先导与源头。他们作为传统,正在影响我们今天的创作选择与判断。
三
——不筹备大型展览,本来不会想着要去创作超大规模的“榜书巨制”。
——没有近十年来对当代书法走向“展厅文化”时代的学术认同,当然也不会想着去为展厅量身订做、创作超大规模的“榜书巨制”。
从2007年开始,我已在大字书法创作的“榜书”方面作了长达几个月的尝试。但当时的作品尺寸,最多就是丈二匹,或两张丈二匹衔接的水平。像《实者慧》《射天狼》《屠龙术》《天行健》等作品,就是在那时完成的,数量约在15件左右,但可以看到的是,当时这批大作品,书写方式还较单一,技巧娴熟,表现意识却相对较为平实。它可以被我们看作是一个前奏,一次热身。
2008年10月,鉴于紧锣密鼓的大展筹备进程,我们组成了一个创作团队赴河南郑州进行了主题性“榜书巨制”集中创作。五天时间,创作了《桃花源记》(草书)八屏,《将进酒》(魏碑)六屏,《老子语》(篆隶)八屏,以及《斩钉截铁》《人中龙》《泰山压卵》《听雨》《怀抱》及《一匹狼》系列等。与2007年时的大字创作状态不同,在郑州的大字创作过程中,我不再是会什么写什么,而是先提出一个相对较难的创作原则:“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一作一面貌”。在创作过程中的不断自我挑战创作能力极限,强调尽量不重复,不平庸,使这次创作的许多作品,在形式与技法语汇表现方面大大丰富了原有的固定样式。而我也在完成后写了一长篇《巨幅书法创作手记》计二万言。可以说:这次郑州之行的收获是在于,第一次从理念与创作原则上,从实践的笔墨技巧与形式发挥上,又从事后的理论思考与经验教训的梳理总结上,全面提出了一整套“榜书巨制”书法创作的目标与实施步骤方法。即使对于我这几十年书法创作生涯而言,它也是十分新鲜的,因此必然是具有挑战性的。它提供了一种范式与模型的价值,为今后的再出发提示出许多极有学术含量的关键点。
2009年11月,在北京书法大展的展厅已确定而展期也已迫在眉睫的特定时期,我们这个创作团队又借浙江美术馆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榜书巨制”创作活动。鉴于这次创作,是对中国美术馆四个大展厅作“量身订做”的补充性创作,以超大件创作为主,主要是对“巨制”部份进行大规模创作,而对“榜书”部份不作补充。在三天时间里,共完成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20屏、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第二十八》11屏,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18屏,《前赤壁赋》36屏。除刘勰一组作品为金文外,其余均为草书。动辄20屏、30屏的整堵墙式的大创作,挥洒笔墨,对我这个创作者而言,也是一次极大的、平生未有之考验—是意志与毅力的考验,是智慧与技术的考验,更是气度与胸襟的考验。
三轮“榜书巨制”的超大幅书法创作,尤其是第二、三次集中创作,终于使我意识到,其实书法不仅仅是我们学写毛笔字时的案头功夫,也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尺牍挥洒、条幅纵横,它还可以从物质空间上“惊天地动鬼神”,以超大的黑白关系震撼观众提示后来者,它是地道的“表现主义”式的现代性格,而绝非我们长期已习惯了的老夫子形象。当我们体验到每写草书线条,必须拖着一捆毛笔蘸着十几斤重的厚墨汁,在铺地的宣纸上走三、四步才能完成一笔线条时,它已经绝不是写毛笔字这样简单的事了。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它所体现出来的张力与表情,不但是寻常的书法所无法想象的,也是足以令其它许多艺术如交响乐、舞剧歌剧、历史题材油画、标志性建筑、纪念性群雕、影视大片等和长篇历史小说、史诗等等为之钦佩折服的。它摆脱了长久以来书法过于卡拉OK、自娱自乐的尴尬境地,把书法放置在一个历史语境中进行定位与阐释—过去我曾经从“意义”“主题”出发,倡导“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讲究主题来完成这种愿望。现在,“榜书巨制”创作实践经验告诉我:还可以从扩大表现空间、“大墨纵横”的角度来完成线条、浓墨对汉字的“超常”阐释。这种阐释,是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是融入到我们每个创作主体,和每个观赏主体的思想行为中去的—对当代书法的“展厅文化”时代特征的提示,则是我们得以“超常”表现的最重要的、必不可缺的载体。
曾经有观众对这样的“榜书巨制”式创作表示不理解,认为写字根本没有找这样巨幅的必要,显然是作者写不好字,故尔有“哗众取宠”之嫌。有朋友问我应该如何思考并回应这样的质疑?我回答曰:首先是技术难度的问题,是伏于书案上写尺寸适当的小字容易?还是弯腰蹲踞拉开马步写一笔要走三四步容易?前者显然是还在你的习惯模式之中,而后者却要调动全身心的力量为之,原有写大楷一笔厚实还是薄削、藏锋还是横生圭角,你马上可以判断;而现在写“榜书巨制”,你一笔下去到哪里收束都不知道,更无法掌控笔力与线质,只能凭既有的积累与感觉,你觉得哪个难?更加之,这样的“榜书巨制”,必须调动全身心包括腰、臂、步、肘、腕……全部围绕一个也许是点是横,对创作者的精力、体力、判断力、掌控力都会提出极大要求。稍有不慎,满盘皆输。那你又觉得哪个难?做这样一种选择,是挑战自我—用我自己的提倡说,是追求不断焕发创造活力的“反惯性书写”,又岂能仅仅以一个肤浅的“哗众取宠”来贬视之?
其次,是从展览的现场效果也足以验证之。北京“意义追寻”大展,“榜书巨制”占10%,在200件作品中不超过20件;而题跋、尺页、竹木简牍等等,则有180件之多,占了90%。但展览之后,社会上大多数舆论与媒体报导,皆是对着这个“榜书巨制”而发。赞成的说它“震撼”“大墨淋漓”,批评的说它眩人眼目,误导书法界。我曾打趣地说:你们为什么对180件小作品视而不见,却对这20件“榜书巨制”如此青睐有加?你们的“有色眼睛”各取所需,其实不正证明了在今天这个书法的“展厅时代”,“榜书巨制”的出众效果与卓绝的视觉冲击力,是最能打动观众的心灵甚至也牢牢吸引住反对者的视线吗?既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去责备“榜书巨制”创作的正当性和是否必要?
四
西泠印社第五届国际印文化博览会要办出不同于前四届的特色,引进与设置了三个特展。一是“上海世博会万国印谱艺术展”, 5月14日在上海中国画院举行开幕式, 轰动一时,成为世博会的一大亮点。二是“上海世博会参展国政要金石印像展”,6月18日在上海举行开幕式,万头攒动。这是篆刻艺术在世博会上的两次精彩亮相。将之引入第五届西泠印社国际印文化博览会,当然是十分出彩。但印文化博览会本身是名石名品荟萃之所,田黄、鸡血、青田、巴林各大名石隆重登场,而两个“世博会”的特展,也是以印石印蜕展示为主,尚缺少一种覆盖全面的“气场”。于是主持者与策展方来找我,希望能提供一批曾在北京“意义追寻”大展中的“榜书巨制”大件,做一个特展。以铺天盖地的大墨淋漓之象,来映衬出印石的精致与优雅。既以“大”(榜书巨制)来衬“小”(印石); 其实反过来也是以“小”(印石)去衬“大”。而同门中诸君也认为:通过这个特展,也顺便总结一下陈老师“榜书巨制”书法创作的经验,理出一条线索来,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提供出发点。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并且在学术上很有挑战性。虽然只是一个辅助性的附属展览,但要做得精彩完美,倒还真不容易。几位门生子弟们一凑,确定了展览名称,叫“大墨纵横·陈振濂榜书巨制特展”。选出了三次大创作的一批作品,构成了这次展览的清晰的专题性与独特的基调。
曾经也有书界好友提醒和表示不同意见,这么一批精心创作、几年探索心血所聚的大作品,为何要替篆刻去做配合性的附展?岂不可惜了?它本来完全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展的内容。单独办一个主题展岂不更好?但我认为,我在西泠印社工作,配合已有良好品牌声誉的印文化博览会,努力满足展厅中“以大衬小”的办展需要, 本来也是我应有的工作职责。且大小互相辉映, 也很难说是谁主谁次,应该说:如果仅仅是一批超大作品,没有精致度,也会产生视觉上的问题。而通过这样一个附属性的特展,梳理新的书法创作理念,研讨从古代到近代陆维钊、沙孟海两位大师的辉煌业绩,再到我们当代的历史责任,以使在今后有机会办独立展时,有更充分的学术准备,应该是个很好的学术选择。
今后的书法艺术创作,一定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边界越来越不重复。如是,则“榜书巨制”一定是我持久努力的一个主要目标与方向。与其它我曾有过的努力目标如十几年前的“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和“简牍”“古隶”“行草手札”“题跋”, 乃至近年来身体力行倡导的“阅读书法”等等相比,“榜书巨制”书法创作,集中凝聚了我对书法技法创造与书法胸襟塑造的双重梦想。我以为,它是一个最令人着迷的所在。它会成为我的书法人生的一个最醒目的生命符号,相伴终生,以致久远。
向所有为本次“大墨纵横”榜书巨制特展付出辛勤劳动的同道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2010年8月1日于西泠印社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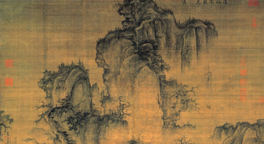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