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刘蟾 整理 本报记者 龚丹韵
作为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小女儿,刘蟾小时候并未学画。虽然上班后在父亲身边得到一些指点,但系统地学画却在51岁以后。彼时父亲已经去世,但他留 下的精神财富,让刘蟾至今记忆犹新。采访时,她娓娓道来自己与父亲的故事,大半天都未谈到学画,以至于几次问她:“那您是怎样学画的?”她都报以微笑: “听我慢慢说。”
家书
与古为新、蝉蜕龙变。辛酉孟夏,书给蟾儿。刘海粟年方八六。
解读
当时父亲86岁,我还在父亲身边练习画画。他鼓励我创新,画画胆子要大,格局要大。甚至说:“你要像我刘海粟的女儿,画画不能缩缩缩。”可惜的是,我后来还是画传统画多一点,我的性格可能还是不够胆大。 (刘蟾)
家训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
人物小传
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号海翁。汉族,江苏常州人。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 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1949年后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早年习油画,苍古沉雄。兼作国画,线条有钢筋铁骨之力。后潜心于泼墨法,笔飞墨 舞,气魄过人。晚年运用泼彩法,色彩绚丽,气格雄浑。历任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1981年被聘为意 大利国家艺术院名誉院士,并被授予金质奖章。
1918年刘海粟起草《野外写生团规则》,亲自带领学生到杭州西湖写生,打破了关门画画的传统教学规范;1919年响应蔡元培之号召,在美专招 收女生,开中国男女同校之先河。他在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创造的数个“第一”,至今仍有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已超出美术史本身,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社会告别传 统走向现代的曲折里程。
父亲很威严
有种不怒而威的气场
我生于1949年,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从小父亲很忙,时常上海和无锡两地跑。我常常见不到他。家里雇了佣工和保姆。父亲回来,佣工就帮父亲磨墨。偶尔我们会在边上看。有时候他为油画打框,我也手忙脚乱帮一下。
父亲很威严。坐在那里不出声,让人害怕。其实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但就是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场。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怕父亲。平时在家里很皮,走 廊上放了一个陶马古董,我们就骑在上面玩。但是大家一听到大门钥匙在转的声音,就知道父亲回家了,连忙跑到楼上躲起来。当时小学里有学习小组,课后几个人 一起做作业,每次轮到小组到我家来做作业,同学们都怕我父亲,不敢哇哇吵。其实父亲没看着我们,就是很有威严。
我们家很讲规矩,见到长辈要叫人。父亲时常有客人或学生上门。他们在客厅,我们几个孩子都不声不响,走楼梯轻手轻脚。吃饭也不敢出声。父亲不拿 起筷子,我们不能先吃。尤其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先要把菜给客人吃,随后几个孩子才分到一些。正式请客有一桌子菜的话,孩子都不上桌。
父亲从小就主张,要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父亲当年就是靠自力更生,来上海创办美专。1929年,经蔡元培先生申请经费,父亲可以去法国进行美术 考察,他带上了我的大哥刘虎。父亲在法国很用功,把大哥送到寄宿学校念书。大哥从小一个人在法国,自己生活。他念书很好,考上很好的学校,此后没有随父亲 回国,长大后在联合国工作,一辈子都靠自己。
父亲常常以大哥为荣。有时候,他会把大哥小时候的画拿出来给我们看,说:“你看,这是虎儿画的。”
小时候,母亲让我学钢琴,我其实坐不住。同学会在窗外叫我的名字,让我出去一起玩。我哥哥看见就说:“不要乱叫,她要弹钢琴,叫她干嘛!”我每 天在客厅里弹钢琴,心里一直不耐烦。妈妈常说:“我们赚钱也很辛苦,出了钱给你学,你要好好学。”仿佛我是为了他们在弹,听着听着我就流泪,觉得委屈。
但是每当父亲回家,他在客厅画画,无形中就管住了我。他其实知道我坐不住,就对我说:“傅雷教育孩子是打傅聪,我不赞成他的教育方法,这要靠自觉。你喜欢你自会好好学,你不喜欢打也没用。”
当时我年纪小,听不懂。只觉得坐在那里很冤枉,泪水直往下掉。
蜗牛爬到脸上
他笑说这是法式蜗牛
被打成“右派”后,父亲中风,右半边身子瘫痪。母亲始终没有放弃,与父亲共同度过艰难困苦。生病期间,父亲的手无法画画了,但是他对画画的爱好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让母亲把画挂起来给他看,继续琢磨研究。
那时候家里气氛凝重,几乎没有声音。父亲从一级教授降到四级,各方面待遇下降,但他需要补充营养,家里看上去排场很大,开销也大,一栋洋房要付 房租,当时一个月工资也交不起房租。我母亲很不容易,她哥哥在香港,寄来很多粮油糖,她就拿这些东西去换钱,给父亲买补品。那时候我读书也受到影响,老被 人说出身不好,平时夹着尾巴做人,一般同学不搭理我。
“右派”脱帽后,父亲心情好了,病也好了,又要出去跑,出去写生。我又看不到父亲了。之前母亲一直帮父亲推拿瘫痪的半边身子,父亲很坚强,病好了以后,不仅可以画,可以走,还活到了98岁,你说是不是一个奇迹?
我初中毕业,家里过了几年平平安安的日子。但是我考高中还是受父亲影响,不能上太好的学校,只能到职业学校,学纺织印染。录取后的一天,班主任 来家访。我们家很洋派,有沙发、地毯、钢琴、油画。这次家访完后,班主任就在学校到处讲,说有些学生家里怎么怎么豪华,说得我很难受。
“文革”时,我家房子被封,留下一间客厅,父亲、母亲和我们几个人打地铺。家具只有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全家生活费只有20元。除了父亲有一瓶牛奶之外,一日三餐都是青菜辣酱下饭。之后我们又被扫地出门,那时父亲已经60多岁,全家搬到另一处小地方居住。
但我父母从来没有唉声叹气。他们很乐观,还互相开玩笑。冬天,我们冷得要命,申请去原屋拿衣服。佣工很好,偷偷拿点笔、纸和画册,送到我们的住 处。父亲依然在画画。我们居住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天井,可以洗衣服,后面是暗暗的厨房。我们睡的地方特别潮湿,常有蜗牛爬过。父亲睡在最外面。晚上,蜗牛 就爬到父亲脸上,父亲还在呼呼大睡,睡得很香,忽然感觉不对,手一拍,脸上怎么黏答答的。他讲笑话说,这是美食法式蜗牛。
家里再有钱
堆成山也没有意义
我自己也没想到,反而是那段日子,我一直陪在父亲身边,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
父亲一直跟我回忆在法国的留学生涯。他说,当时的时局不稳,留学的资金有时会发,有时没有。他就去卖画。每天去卢浮宫,一边写文,一边写生。 “留学时间有限,这么好的机会,我自己学都来不及学,一定要好好珍惜。”父亲说。所以他那时很用功。最后实在没有钱,他就从市里的阁楼房里搬到了法国郊 区,租了间房子。
父亲每天早晨学法语,慢慢地就能和邮差对话了。法国邮差告诉他:“今天很高兴,儿子来看我,我儿子现在是法国文化部长。”父亲惊讶地问:“儿子 已经是部长,那你可以不用做邮差了呀?”对方说:“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为儿子骄傲,但我喜欢这份工作,不会因为儿子怎样,就不做自己的工作了。”
父亲对我感慨:家里再有钱,堆成山也没有意义。孩子自己没本事,只能坐吃山空。一定要靠自己,这是谁都夺不走的,是自己的财富。
那段日子,他常常和我说起这些。以前我看到他就怕,觉得他离我很远。人家女儿可以与父亲撒娇,我们家却不行。反而是这段岁月,拉近了我和父亲的 距离。他对我讲了很多道理。一家人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很开心。只要能画画,父亲就很高兴。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不相信现状会长久下去。
只有一次,抄家时有人烧了他的收藏。父亲很担心,说这是文物,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四旧”,烧了就没了。他一急,打电话给市领导,希望有一个人来处理这些收藏。后来终于有人来,说不要乱烧,终于保留了一部分收藏。
父亲一直对我说:“这些收藏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我只是把它们收起来,作为研究资料,将来捐给国家,让大家看,让爱好美术的人看,才能发挥它们的价值。”父亲从来没有把这些收藏当作财富,他认为,它们是精神的财富,不是钱财的财富。他一直叮嘱我,生存要靠自己。
字要写大字
画要画大的
家里孩子没有人学画。父亲的教育理念一贯是,喜欢就学,不喜欢就别学。我们也没人主动提出学画。后来我们看到父亲因为画画受累,大家都怕死了,更加不会提出学画。
就在“文革”的小屋里,纸笔有限,父亲每天会睡午觉。母亲整理家务,随时挡人。母亲原本也画得很好,她为了父亲放下自己的爱好,挺可惜。
我闲着无所事事。有一天,母亲忽然对我说:“你反正也是闲着,这么多学生老大远跑来请教你父亲,现在你就在父亲边上,怎么不学点画?”可我还是 怕父亲,不肯学,推说怕被父亲骂。母亲说:“你怕什么?你要画得比你父亲好?那不可能吧?”我想也是,画坏了也就是一张纸的事。我整天看画册,每当学生偷 偷摸摸来请教父亲,我就在边上听。听了许多,对画画并不陌生。
于是我就开始画了。起初拿张小纸画,用钢笔临摹画册。父亲下午睡觉时,我就在那里画。一察觉他要起来,我就停笔。母亲说:“别停,画下去。”我说:“爸爸醒了,我怕。”母亲说:“怕什么,画。”我当时手抖得要命,大树画得只有一点点大小。父亲看了看我,不出声。
一段时日过去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忍不住说话了:“你要画大画,不要老是缩缩缩。缩得格局太小,没气魄。一张画主要看精气神。你是我刘海粟的女儿,怎么画画格局那么小,要有大气魄!”他指着我画的树说,这样不行,要用大笔画。
父亲没有手把手教我什么基本功,他就是关键时点拨几句。他的教育风格就是不干涉你,先看你的路子走得怎样。我怕他,他在的时候越画越小。后来他 拿了一张大纸教育我:画和人一样,出来的气质不同,个人风格也不同。但是气质是可以磨炼的,一个人念书,学音乐,气质会变好。他教我用毛笔画松树,先给我 说松树的道理,要求我画出松树的气质和精神。
他说:“重新来过,字要写大字,画要画大的。胆子放出来,格局要大。”
要创新
但不是放弃传统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家里也有大卫像。父亲说,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画大卫,要把他的性格表现出来,而不是画得一模一样。有一次,一名学生到家 里来学画大卫,父亲一看,画得很大气,就觉得好。父亲满意地说:“你不要细描细绘,要画出大卫的气魄。”所以,父亲的教法和现在的美术教学不一样。他甚至 不同意我用铅笔画。觉得铅笔容易画小了。他说即使是素描,也不是表现块面,而是神。写生更是,写的是人的生命力。他会讲道理,但不会让你这里擦掉,那里擦 掉,这种细活他从来不教。他说:“大胆入笔,不要怕。”他还告诉我,学国画一定要学书法,特意让我练习写大字。
父亲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平时自己练。他主张,自己学会欣赏和自学。比如,我喜欢文徵明的画和笔法,那就自己研究。他会在旁边指点几句,文徵明用什么手法,怎样画出那种风格的画,但他不会具体到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自己领悟很重要。
有一阵子,父亲喜欢带着我们去复兴公园散步,那里有个荷花池。我们走半天一定会在荷花池边坐下来。我们以为父亲只是走累了,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在观察,研究荷花的光影。那阵子他画了很多荷花,有重彩,也有泼墨。
白天,桌子给父亲画画。有一次画完他睡着了,我就用隔夜的墨,临摹他的画,画了一朵牡丹。第二天他起得早,看到我画的牡丹,激动得不得了,在我 的画上题字。我确实没有临得一模一样。他和我说,这幅很好,像雨中牡丹。朋友来了也拿出来炫耀。可惜当时我还不够用功,在印染厂上班,三班倒,没办法全身 心练习画画。
有一次,父亲说你要学会拉线条,建议我临摹 《朝元仙仗图》。当时正值夏天,我每天画一点,两个多月才画完。画的时候,用毛巾把手臂包起来,不让汗水滴下来。
外人误解,以为父亲就提倡创新,抛弃传统。其实父亲传统的根底很好。父亲说,我们要留下这个时代的艺术品。老祖宗的作品,学得一模一样没意义。 我要创新,但不是放弃传统。即使画油画,也是中国意味的油画。为的是创作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留给后人的作品,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所以,父亲并非只知创新,不要传统。恰恰相反,他告诉我,要了解古人,学习古人。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都得会。母亲总批评我眼高手低,别人的画看不上眼,自己又画不出来。我们三人一起互相开玩笑。
那段岁月,让我对父亲母亲的了解更深了。
仿佛回到
父亲在法国的留学生活
改革开放后,母亲觉得我在厂里翻三班对身体不好,让我去香港。父亲处境变好了,到处有人邀请他,他很开心。而我则在香港为生活而忙碌。那时候通信依然困难,电话费很贵,也不太打电话。
父亲曾说,去了香港也别放弃画画,他觉得我天赋可以,应该继续努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不在,我心态不好,总是没耐心画,还生了一场病。我是1979年去香港的,此后我在香港结婚,一直到父亲1994年过世,这15年间我都没有再拿起画笔。
1994年3月,上海市政府打算给我父亲过生日。我当时恰好回上海,父亲没问我还画不画,母亲说了几句,但是看我工作特别忙,也无可奈何。父亲 说,自己一生只有一件事未了,就是自己的创作和收藏想捐给国家。“希望我捐的东西,能够常常展览,给美术爱好者参观。”父亲说。后来政府部门的人回答,准 备为他建立一座美术馆。
同年,刘海粟美术馆建成。听母亲说,他坐着轮椅去看了新美术馆,拍了照,很满意。父亲心事俱了,就在这之后去世了。
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要画画,不然太可惜。我就去南京艺术学院进修。那是我父亲呆过的学校。当时我已经51岁,但很用功。每周一去南京,周五回上海看母亲。火车来回4小时。一直学到2004年,身体变差,走不动路,才改为每两周回上海一次。
在进修时,曾有一位老师说我:“你是刘海粟的女儿,应该有傲气,你父亲是大师呀。”我说:“这是我父亲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我有什么可以傲气 的?”借着父亲的光,我傲不起来,反倒觉得自卑,因为与父亲差太远了。也有人说,进修4年后,你也可以当一名教师,但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
我认认真真学了四年画。学油画,也学国画。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不大敢说我,可能因为父亲名头太响,其实我不会介意。那段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父亲以前教我的场景。靠自己领悟,靠自己勤奋,多看画展,多练写生。时光仿佛回到几十年前,父亲在法国的留学生活。
我看到很多,学到很多。
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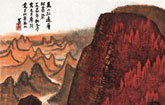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