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回大唐話開放

望野博物館藏唐灰陶蓮瓣形三足硯

彩繪陶樂舞俑
開放、包容,無疑是唐王朝屢屢被貼上的鮮明標簽。那麼,其開放程度到底若何,恐怕惟有彼時生活在唐朝的人最有發言權,尤其那些“漂”在異鄉的外國人,感受更真切。
最近,長沙博物館、廣東鬆山湖望野博物館線上、線下同步推出“粟特人在大唐——洛陽博物館藏唐代文物”“踏波東來——遣唐使的回憶”兩大特展,再加上國家博物館網上展廳的“大唐風華”,不約而同地通過那些或長或短駐留唐朝的異鄉人之眼,帶人們夢回大唐,了解繁華背后的諸多故事。
“粟特人在大唐——洛陽博物館藏唐代文物”特展呈現的文物,多來自唐定遠將軍安菩夫婦墓,其中的安菩墓志,被視為該墓出土文物中最珍貴的一件。據墓志銘記載,安菩是來自安國的粟特人,父親曾是安國的“大首領”,唐滅東突厥后,率部歸附唐朝。安菩“同京官五品,封定遠將軍”,曾受命率部從唐軍北征“北狄”,“以一當千,獨掃蜂飛之眾”。
漢初,匈奴破月氏,月氏棄故地河西昭武(今甘肅臨澤),進入中亞粟特地域(今澤拉夫善河流域一帶),形成諸粟特城邦,包括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畢等國,統稱“昭武九姓”,唐朝稱他們“九姓胡”或者“胡”,西方則稱之為“粟特”。安菩之妻何氏為何國人。
安菩的墓志銘雖僅400余言,但信息量巨大,其中還記載了安菩的兒子安金藏在母親何氏去世后,“痛貫深慈,膝下難舍﹔毀不自滅,獨守母墳﹔愛盡生前,敬移歿后”,以及安菩嗣子“游騎將軍胡子、金剛等,罔極難追,屺岵興戀。”安金藏又於公元709年遷父親安菩尸骨往洛陽與母親合葬,建造了安菩夫婦墓。此次展出的大批唐三彩陶俑,即是該墓出土的陪葬品。父母去世后,安金藏均按中原禮俗進行安葬,由此可見其漢化之深。
展覽中還有一件出土於洛陽李樓鄉的大秦景教石經幢,此經幢來自“安國安氏太夫人”墓的神道,反映出安菩家族急切漢化的同時,另一部分粟特人仍保持多元宗教信仰的現象,體現出唐代文化的包容景象。
安菩家族的漢化或許有深層的時代背景。來唐“使節”常常是來華貿易的商人。唐王朝對他們無一例外給予交通及住宿的優待,當他們要返回本國時,鴻臚寺和典客署還要歡送,並贈予數量相當可觀的禮物。
對於已經歸附的胡人,唐朝規定“不得入蕃”,也就是說,來了唐朝就是唐朝人,別想再回去了。由此可見,對於已經歸附了唐朝的安菩家族,擺在眼前的路隻有一條:加速融入大唐。
從出土文物看,安菩家族融入唐朝的過程相當有聲有色,十分歡樂。展覽中有不少彩繪樂俑、舞俑、三彩伶俑、三彩騎馬俑,甚至還有羅馬金幣,反映了安菩、安金藏生活的唐代社會,胡樂胡舞等西域藝術的流行。可以說,粟特人是奏著胡樂、跳著胡舞,馬球場上瀟洒奔騰著,甚至沐浴著舊邦的宗教信仰,是在唐朝人“胡姬美如花,當壚笑春風”的欣賞與追捧中融入大唐的。
國家博物館“大唐風華”展中的韓休墓壁畫《樂舞圖》,更是直觀展現了唐代的對外開放程度。《樂舞圖》上,一邊是胡人男樂、一邊是唐朝女樂,兩支樂隊各派一人合樂起舞,與其說是聯歡,不如說是在斗樂、斗舞。一邊是橫抱琵琶,一邊是笙管齊鳴,女舞衣袖款款,男舞眉飛色舞,儼然是唐代的中西樂舞比賽。東土與西域,在樂律舞影中交流互鑒,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各得其所,日漸交融,共同創造了一座唐代文化的高峰。
“踏波東來——遣唐使的回憶”也展出了一塊墓志原石,即首次展出的日本國朝臣備書丹、褚思光撰文的鴻臚寺丞李訓墓志原石。墓志石落款為“朝臣備書”。朝臣備,一般認為即先后作為留學生和遣唐使來到唐朝的吉備真備,曾入唐留學18年,與阿倍仲麻呂為同學。墓主李訓擔任主管接待外國人的鴻臚寺丞,而鴻臚寺又是吉備真備長期學習的地方。也就是說,唐代的外交官的墓志銘由來自日本國的使者來書寫,不管是不是墓主的遺願,都讓人看到了日本遣唐使與中國士大夫的互動之深入。正如阿倍仲麻呂與李白、王維等人同樣結下的深厚情誼,均照見了唐朝對外開放的心態與格局。兩國民眾是否心靈相交、生死相牽,可以從側面佐証一個時代開放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亂之后,由於安祿山、史思明的粟特人血統,唐人認為此前胡風大行其道,實為不妥,由此出現“排胡”傾向,不少粟特人因此加速漢化。這一動向也體現在墓志的變化上,安菩墓志銘中,並不諱言家族粟特人的身份,墓石蓋書“唐故陸胡州大首領安君墓志”,對家族世系記述甚詳。而安史之亂后,粟特人墓志普遍諱言出身,很多康氏粟特人巧妙地稱自己是“會稽人”,不熟悉的人還以為是江南會稽,其實是河西粟特人聚居的瓜州地區也有個同名的地方。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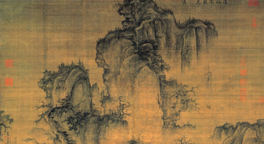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