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本余事 風規可銘心——學海堂與晚清嶺南文化

梁於渭 《柏樹桃花圖》

伍學藻 《重開學海堂對酒感賦詩意圖》 畫上題跋為陳璞《重開學海堂對酒感賦》
“同治壬申七月,同陳朗山、呂拔湖、劉稻村、劉萸溪、梁芷卿集學海堂玩月。余夜半歸,諸君皆宿堂中。翌日,朗山以詩來,因次韻二首,諸君皆繼作。萸溪同年屬(囑)為圖,並錄詩於后,亦以志一時清興也。古樵陳璞並識於綠槐軒紫藤架下”——這段話,題寫在廣州藝博院一樓關山月藝術館正在展出的“問學余興——院藏清代廣東學海堂學人書畫精品展”中,陳璞作於1872年的《學海玩月圖》上。
畫面中,四五座依山而建的房舍,林籠竹繞,映照在穿越雲層洒下的月光中﹔庭院內,有五六人相向而坐。這個“山月涼”“醉醒適”的嶺南月夜,於廣州而言,不過萬古中之一瞬﹔而對“學海堂”來說,卻是少有的,如“寫真”般的真實記錄。
“嶺南”與“江南”,“新移民”與“士紳大族”的交織
1820年,兩廣總督阮元為將江南最新的經史之學和文學潮流引入廣東,提出創辦學海堂。學海堂是清代廣東最具影響力的書院之一。有別於同時期廣州城中的其他書院,它不以補習科舉考試為目的,而以考據學研究為底色,設置經史、詩、古文詞課程,不設山長,設立八名學長評定課卷。自1820年至1903年關閉,結集出版《學海堂集》四集,清代廣東精英文化景觀為之一變。
展覽策展人,廣州藝術博物院副研究館員、博士黎麗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關注學海堂,特別需要關注它的成員構成與“本地”之間的關系,也需要把它放到當時廣州城鄉結構的整體環境中去觀察。
“嶺南”與“江南”是兩個相距遙遠、差異非常大的文化區域。即使在社會和文化已經高度融合的今天,短時間將一種帶有強烈“他鄉”色彩的學術體系引入一地,也會激起震動。可以想象,阮元的學術實驗,在廣州因對外商貿的優勢地位而富足和繁榮的環境中,在當時“以一種生機勃勃的文化而自豪”的廣州和珠三角地區的文人群體內,必然帶來諸如觀望、疏離這樣的情緒。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如美國學者麥哲維在《學海堂與晚清嶺南文化》中描繪的那般的情景:“選擇認同於學海堂學者的核心群體,大致上是由來自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都市化家庭和居住在廣州城的來自本地區之外的旅寓者或移民構成的。相反,聚居於廣州之外珠江三角洲西江沿岸一帶的根基深厚的士紳家族的子孫,則廣泛對這所新書院採取忽視的態度”。
這種兩個群體間的心理距離,鮮明地體現在兩位齊名的學者陳澧和朱次琦身上。雖然以學生和教師的身份都曾被邀請到學海堂,但出身西江邊九江鄉望族的朱次琦,拒絕了讓他擔任學海堂學長的邀請﹔此外,即使他在學術方面與陳澧有不少相通之處,但他對學海堂的學術批評也是直接而尖銳的。這似乎說明,相對於陳澧在理念上強調自己的“江南”根源,實際上是立足於廣東省城的自我定位,“九江先生”朱次琦對於深厚的地方性資源的依托與認可,顯示出更強烈的“地方意識”或“地方特色”。
學海堂學人群體呈現既鬆散又密切的共生生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來看藝博院中正在展出的《問學余興——院藏清代廣東學海堂學人書畫精品展》就有一番別樣的味道。如展覽前言所說,展覽中涉及學海堂創始人及學長、學生中,阮元、謝蘭生、儀克中、張維屏、譚瑩等的行楷書,延續清代帖學的傳統,又參以各法,自成一格﹔黃子高、陳澧等不僅是其中的佼佼者,更對廣東書風大有影響﹔謝蘭生、熊景星皆其時之畫壇名宿,秀琨、梁於渭、黎如瑋、伍學藻等亦以畫名重於時。從藝術角度來說,這些人代表了那一時期廣州地區文人書畫創作的水平。我們在展覽中看到,雖然很多人的創作仍更多地採用那一時期的普遍題材,並非刻意追逐本地“風物”,但他們的創作,又與地方性密切相關。因而,學海堂諸人的藝術創作,與他們對於建構由自我主導的學術體系和評價機制的過程,具有共振性。
學長黃培芳的《江山秋靄圖卷》,描繪的是深秋山林景色,畫面設色淡雅,筆墨蒼潤,意境超遠,是其中晚年的精品。上款的“寄庵宮保大人”,據黎麗明的考証,為1833至1838年間任廣東巡撫的祁貢。黃培芳曾充其幕客,“學海堂學長不僅是本地著名的學者,他們還是熱心地方事務的士人,在不少地方事務中均能見其活躍的身影,儼然如其時高級官員的智囊團。他們與地方督撫大員關系密切,日常的書畫應酬也充分反映這一點”。同場展出的陳澧《行書詩十六首》八聯屏,上款是曾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亦是例証。
這種交雜的網絡,呈現出的正是圍繞著學海堂而形成的一個既鬆散又密切的群體的共生生態。如中山大學教授程美寶指出的那樣,興辦學海堂的主力,包括提供捐助的行商和部分學長,很多出自原籍在江南和福建,在廣東省城定居隻有三四代的家庭。與他們形成對照的,是更早扎根於珠三角的大族。明清之際的沙田開發、水利與漁業的爭奪、商業市鎮的興起等綜合因素的作用,不可避免影響到當時學人的治學。無論新移民、老移民還是更早來的“土著”,在這個變動劇烈的時期,都存在著一個“成為本地人”的身份建構,或者重新認知的需求。
如是說來,我們今天看學海堂,就不能將之視為單純的學術機構或者“學校”,而更應將其看做一處“在地方層面為文化資源和聲望競爭的工具”。他們與長期掌握著本地文化資源的士紳大族,實際上是競爭關系。從空間形態上看,學海堂諸人主要聚居於城市,世家大族則掌握著鄉間。這種城鄉之間的界限,並非學術理念和方法的截然分野,更像是一種“話語權”和“傳播力”的博弈。
從筆墨余興中一睹廣州文化的繁榮
“城市文人在宗族門第上的欠缺,由學海堂以學術和文學上的資格憑証給予了補償”,麥哲維指出,“因此,當學海堂成為地區同化與社會進步的整套戰略的一部分時,寓居的文人和城市化的移民家庭對由外地引進的新型文化學術作出極其踴躍的響應。”許多學海堂學者甚至對周圍所見的“俗氣”的商業文化持有明顯的批評態度。
但這並不代表學海堂諸人對商業文化的好處視而不見,實際上,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后,學海堂的學長“更像精明的投資人和經營者,他們購買沙田,收取租金利息,建立惠濟倉”,並以這些收入重修學海堂,重印他們曾經深度參與其中的道光《廣東通志》和《皇清經解》等重要著作,並且刊行新的《學海堂集》。
經由這一系列的操作,學海堂的地標意義和學術位置再度鞏固,其模式也影響到主要為商人子弟而設的應元書院,以及陳澧所主持的菊坡精舍。到清同治年間,鼎立於越秀山上的三座書院,已儼然成為一個學術集群。
展覽中伍學藻繪於1898年的《重開學海堂對酒感賦詩意圖》即是這段時事的反映。英法聯軍攻佔廣州時,位於越秀山的學海堂被侵佔,院舍毀損嚴重。同治元年(1862)學長領款重修,無奈七月因風災毀圮,次年(1862)再度重修。新修落成后,周寅清、譚瑩、陳澧、陳璞等幾位學長置酒宴聚,以示慶祝。陳璞寫下了這首《重開學海堂對酒感賦》。黎麗明認為,“繼任學海堂學長的伍學藻,對前任學長、對學海堂的歷史一定熟悉,對這首詩所飽含的情感也一定是感同身受。”
在忙於建構身份認同和學術體系的學海堂諸人看來,或許書畫只是繁忙問學及工作之外的“余興”,但浸淫於傳統中國文人學術體系之中的基礎訓練,讓他們具有了相當高的創作水准。另一方面,包括書畫雅集、研討在內的各種活動,本身也是學人社交、問學的一部分。
黎麗明指出,這些問學之余的筆墨游戲,“是他們交游唱酬的傳情再現,是他們學術趣味與人生理想的優雅表達”,暗含了理解19世紀廣州城市文化精英物質與精神世界的種種細節。
許多畫作具有強烈的趣味性,比如熊景星40多歲時作的《仿各家山水圖冊》,共六開,每開一景,仿元吳鎮、明盛茂燁、清惲壽平等諸家畫法,尺幅雖小,筆墨精到,畫風清新雅逸,是熊氏畫風參研各法、自成一格的體現。
又如容庚先生舊藏的伍學藻冊頁,山水、花卉、草虫等題材皆有涉及,筆墨或蒼秀精妍或疏放寫意,與“二居”等的作品對比來看,就更好理解廣州藝術創作的不同風貌。黎麗明指出,對地方傳統文化之梳理,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希望觀眾透過這個展覽,對清代廣東文化的繁榮,以及清代廣東文人書畫的盛況有所了解。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學海堂作為一個“案例”,同樣具有其局限性。在關注它的時候,也不能忘記與之並行的其他學術、文化、藝術群體。正是這些互不相同,甚至相悖的群體,共同組成了豐富的文化拼圖,為今天的廣州留下了寶貴的遺產。(文/圖 記者 卜鬆竹)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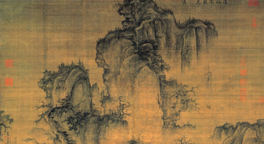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