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男人自愧弗如?歷史上的女書家

蔡玉卿書法
女性書家,史籍可考者,第一位是西漢楚王的一位侍者,名喚馮嫽。但《漢書·西域傳》隻說她“能史書”。這到底是不是寫書法,似乎還難以確定,可是馬宗霍《書林藻鑒》已逕行將之歸入書人行列。大概此時書法藝術剛剛興起,所以甄錄較寬吧。
同理,章帝時德竇皇后、和帝時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史傳都隻說她們“年六歲能書,親家奇之”“六歲能史書,家人號曰諸生”“少好史書”。這也許都隻能表示她們喜歡書翰罷了。真正談到創作書法藝術的,是和帝時的陰皇后,《本紀》雲:“后少聰慧,善書藝。”
書藝雲者,指明了書法在漢時已被視為一種技藝。如元帝,《本紀》說:“帝多材藝,善史書”,足証史書雲雲,應該也就是指寫字書史的藝術。故《后漢書·宗室傳》說北海敬王睦“少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史書,就是指其書藝,頗為明確。考其名義,蓋因“史”字本即象人握筆之形,所以把寫字的藝術稱為史書。《后漢書·清河王傳》說王之姬人(即安帝生母)“善史書”,就是這個意思。故若以此為據,則以上所舉各位,被視為女性書家,地位應是毫無疑問的了。
這個時期,女性書家見於著錄的,都是后妃之流。原因也不難索解。這門藝術方在萌芽階段,一般女性,縱或工書,亦不易見稱,唯有后妃之德,載入史傳,乃獲流傳。
當時女書家之非后妃者,以蔡琰、皇甫規妻為著。兩女善書,均記於《后漢書·列女傳》。蔡文姬據說得傳蔡邕筆法,黃山谷對她所寫的《胡笳十八拍》非常贊賞。皇甫規妻子,《后漢書》說“不知何氏女,善屬文,工草書”。到了唐代,張懷瓘《書斷》卻明確地說她姓馬,工隸書。不知何所本。但《九品書人論》將馬夫人行隸列入中品中,似乎當時確有書跡可考。現在則難以稽查了。
蔡琰,乃名父之女。魏晉而后,此類女書家也不少。例如安僖王皇后,是王獻之的女兒,善書,為《書斷》所稱﹔謝道蘊,為王羲之侄女,《書后品》謂其書“雍容和雅,芬馥可玩”﹔甚至王獻之的保母李如意,據《保母磚志》說她都“能草書”。可見王謝家族中男女俱擅書藝。而此類名門大族女子之以書藝著稱者,則又以衛夫人最為重要。
衛夫人是衛恆從女,東晉著名書家,王羲之曾隨她習字,故《翰墨志》雲:“夫人善鐘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
但王羲之隨她練過字是不錯的,衛夫人的字到底如何,恐怕甚難具體說明。因為說她“善鐘法”就很可疑。鐘繇字,依衛恆《四體書勢》載,凡有三體,最好的是銘石書,二是章程書,三是行狎書。所謂銘石書,應該是指他的正書。可是鐘繇當時的正體,因“去古未遠,純是隸體”﹔至衛夫人時,楷法不可能仍用此種體段。其次,陸行直曾評鐘繇“高古純朴,超妙入神,無晉唐插花美女之態”,《書斷》也說鐘氏“真書古雅,道合神明”。然而唐人評衛夫人卻說她“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若唐人所見之衛夫人墨跡果真如此,又怎能說她“善鐘法”呢?
因此,衛夫人是史上第一位完全以書藝名世的女性。她不像皇甫規之妻,隻能代她先生“答書記”,也就是代筆做秘書﹔也不像蔡琰,名頭和筆法均有沾溉於其父之處。她雖出身名門大族,但純以書藝擅名,也以此授徒,而且還教出了一個書聖王羲之。可是這位足以作為我國女性書家冠冕的奇女子,其藝其實仍是個謎。一方面,《書后品》說:“衛素負高名,正體尤絕”,似乎呼應著《翰墨志》的講法﹔一方面卻又有人以仙女舞姿來形容她。依前者,衛書應是清勁古拙的,因為鐘繇即以瘦勁古雅見長。依后者,則她應是流美妍媚的。一偏陽剛、一偏陰柔。到底哪一種才是衛夫人的真正面貌呢?
世傳衛夫人另著有《筆陣圖》。這是流傳極廣的書法訣要,也是“永字八法”的前身。由這篇文章,不難看出她的筆法主張。但是,這幅圖也是個謎,作者究竟是不是衛夫人,頗有爭論。或題為王羲之,或雲為六朝人偽托。大抵是因她名高,又曾教過王羲之書法,所以這篇教人如何寫字的文章,大家就都說出於她之手了。但假若此圖真為衛夫人所傳,或屬於她這一脈的筆法,則衛夫人就隻能是剛勁的風格了。
因為此圖將書法寫字比擬成打仗,要持筆去破敵陣,故筆鋒即刀鋒,一點如高山墜石,一鉤如百鉤弩發、一折如勁弩筋節、一撇如陸斷犀象。一刀斜劈,要能斬斷犀牛大象,那需要多大的氣力?因此她說:“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可見這完全是講力道、極雄強剛勁的書風。此圖又稱為“筆陣出入斬斫圖”,正可見其用心之所在。
在衛夫人以前,書藝確實也是以雄健為主的。蔡邕之前的王次仲,《書斷》說他“奮斫揚波”“交戟橫戈兮氣雄逸”﹔張芝,羊欣說他“精勁絕倫”。蔡邕的字,《述書賦》說他“啟戟彎弧,星流電轉”。魏晉間名家,如韋誕,梁武帝說他“龍威虎振,劍拔弩張”﹔皇象,羊欣說他“沉著痛快”﹔晉元帝,《述書賦》說他“如發鉶刃,劍客得志”﹔索靖,則自稱他是“銀鉤蠆尾”﹔又傅玄,唐人評為“如項羽投戈,荊軻執戟”。凡此等等,俱可見論書重視骨體、氣勢、力道,是漢魏兩晉的主流。據《書史會要》雲:“王曠與衛氏,世為中表,故得蔡邕書法於衛夫人,以授羲之”。衛夫人之法,無論傳自蔡邕抑或鐘繇,遂都不能不是雄強的。從這一方面看,衛夫人以斬斫論書,也可說是淵源有自的。
然而,在大潮流中也不是沒有小支流。在雄強的書風之外,也仍有一些表現為柔美的作家與作品。例如張芝的弟弟張昶,風格就與老哥不同。《書斷》說他“雖筋骨不及,而妍華繼之”﹔《書后品》說他“西岳碑,但覺妍冶,殊無骨氣”。這顯示此時也存在著一種妍媚的書風。其后有劉德升,據說是行書的創始人,《書斷》亦謂其書“豐贍妍美,風流婉約”。這也是妍美的。大抵勁健之書,強調筋骨﹔妍美之書,則有肉感。所以用“豐贍”來形容妍美,而說此類字的筋骨較弱些。
妍美之書,亦因此而較肥﹔勁健之字,因此而較瘦。瘦硬顯骨力、豐潤見姿態故也。衛覬是瘦勁的,羊欣說他“草體微瘦”,《書小史》也說他“草體傷瘦”。鐘繇亦瘦,羊欣雲:“繇與胡昭俱學於劉德升,而胡書肥、鐘書瘦”。由此可知其時肥與瘦、筋骨與肉、剛健與妍美已漸漸形成一種對比了。
衛恆的字,似乎就是偏於妍美的。袁昂書評,謂其“如插花美女,舞笑鏡台”﹔《書后品》說他“縱任輕巧,流轉風媚”。若如此,衛夫人由此淵源而得柔美之風,也非不可能之事。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看,書寫,本來就具有男性的意象。筆,仿佛陽具,在無抵抗、滑如女兒膚的紙張上進行書寫,而且展現雄強、剛健、勁力等雄性特質,對女性書家來說,乃是本質上不公平之事。所以女性若能發揮其女性特質,改變這種陽具書寫的性質,轉換成一種女性書寫,體現出陰性風格,才能稱得上是獨立的女性書家,而非僅在模仿男人、或學習男性書風的格局中討生活,把自己馴化或改造成一位“入陣斬斫”的刀鋒戰士。因此,從這個觀點說,衛夫人若真能展現出“插花舞女,低昂美容”之姿,反而是值得稱道的。
當然,傳統書論者不會這麼認為。傳統書論不見得都是大男子主義,但書法這門藝術是以線條為其基本構成元素的,線條講究剛、雄、有力量,是其基本要求。為什麼不以軟線條為主,而要強調線條的硬度呢?因所用之毛筆本是軟毫,軟毫寫在軟紙上,當然會以勁健有力來表現其工夫。線條無力就不會好看。唐太宗批評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說他無筋骨(見《王羲之傳論》),就是據此而說。其次,字被擬象為人,一個人若骨架子不佳,站立坐臥也均不會好看,所以論字以植骨為先,強調骨體、骨法,也是很自然的。在這種情況下,書法的評價標准,往往就會重陽剛而輕陰柔。衛夫人入陣斬斫之說,廣獲推崇,即由於此。
那麼,我們要贊嘆衛夫人以一女子而傳雄健斬斫之術,為百代宗師呢,抑或要遺憾她未另立一宗,以陰柔妍媚自別於刀戟斬斫之隊?還是要惋惜她畢竟是個女人,寫字仍不免於柔婉?或者,索性要稱揚她的柔美?
在此,顯然吾人極難予以論斷。不過,也許這是個有意義的矛盾。衛夫人書,既有人認為它剛勁,也有人覺得它柔美,她徒弟王羲之的情形不也一樣嗎?
梁武帝曾說王羲之“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唐人書評,謂其“如壯士拔劍、壅水絕流。頭上安點,如高峰墜石﹔捺一偃波,如風雷震駭”,也特別指出它雄強的性質。但陶宏景即曾說過羲之《樂毅論》《太史箴》等“筆力妍媚”。后來傳世書跡,確實也偏於秀美,以致韓愈批評“羲之俗書趁姿媚”。《書斷》也說羲之“真行妍美”,《書議》更說他草書“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不足貴也”。這不也如衛夫人一般,既有人說它雄健,亦有人指它為妍媚嗎?
也就是說,王羲之與衛夫人的字,可能同時兼有兩種相互矛盾的素質,故或見其妍媚,或見其雄奇。古來論書,以“中和”為最高之境界,衛夫人造詣固然不逮王羲之,但體兼文質、格備剛柔這一點,或許與右軍相仿。女性書家,具此書品,足以俯視群倫了。
可惜后來女子學書者,少有衛夫人般的氣象,或不免為男子之附庸。如唐高祖時,竇后“善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舊唐書·本傳》)﹔太宗女兒晉陽公主“臨帝飛白書,下不能辨”(《舊唐書·本傳》)。史乘以此諛之,不知實為貶之。這樣的字,且不說是否為男子之附庸,模仿了另一個男人,它本身就缺乏自己的個性。
后妃字既已如此,欲求真正的女性書家,即不能不求諸野,尤其是方外人士。像著名女道士魚玄機,《宣和書譜》雲其:“工行書,得王羲之筆意,清勁不墮世俗之習,飄飄然有仙風道骨。”又,西山吳真君女兒吳彩鸞,也是道教人士,世稱吳仙,歷來均盛稱其書藝。如《書史會要》說她所書《唐韻》:“字畫雖小,而寬綽有余,全不類世人筆,當於仙品中別有一種風度”,虞集也說:“世傳吳仙所寫《唐韻》,皆硬黃書,紙素芳潔,界畫清整,結字遒麗,皆人間之奇玩也”,並有詩詠之雲:“豫章城頭寫韻軒,繡帘窣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人間第幾篇。”這是能在書法風格上自開一天地者,未必依循世俗或男性書法的法則,而以自己的身份與性情,創造了特殊書風,所以特為人所稱贊。
另有一類,則如入陣斬斫之衛夫人,能突破本身性別的屬性或限制,與男子競其雄強。如薛濤,身為名妓,但“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宣和書譜),可稱為奇女子。又如房璘的妻子高氏,歐陽修《集古錄》說她所“書安公美政頌,筆畫遒勁,不類婦人所書”。
唐代以后,婦女作書,類不出此數種形態:一者字畫婉媚,有女性之特質,如宋洪內翰侍人翠翹,《書史會要》即說她“字畫婉媚”。清朝董小宛,《閨秀正始集小傳》也說其字“落筆生姿”。詩人王芑孫的妻子曹貞秀,據《鷗波漁話》載,其書“氣靜神閑,娟秀在骨。應推本朝閨閣第一”,亦屬此一類型。一般說來,女性書,以此為本色大宗。
第二種類型,則是女性特質不顯,以學習古人時人筆法而擅書名者,如前面談到的晉陽公主之類。宋代仁宗曹皇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老學庵筆記》)﹔詵蔡之母徐氏“學虞世南書”(周必大語)﹔明代婁妃“書仿詹孟舉,楷書千文極佳”﹔楊妃“書法趙文敏,頗得筆意”﹔馬問卿“書法蘇長公,得其筆意,頗與魯南相類”﹔邢慈靜“善仿兄書”(均見《列朝詩集》)﹔徐范“十二齡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珊瑚網》)﹔清王淑端“天資高邁,楷法二王”﹔王圓照“書法歐柳”﹔郭文貞“工大草,揮洒奇妙,殆可追仿板橋”(均見《閨秀正始集小傳》),都屬此種。以學習、模仿為主,藝精者甚至可以亂真。如《藝舟雙楫》說劉墉有姬人黃氏“筆勢極似,唯工整已甚,韻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真書竟自莫辨”。這種模仿丈夫筆法的作風,與唐代竇后、晉陽公主是一樣的。書乏個性,尤其缺乏女性的性質,女性書家中,這一類也不少。
第三類,則是在書法審美典范已經形成確立后,在雄肆的標准下與男性爭鋒之作。筆勢剛勁,不讓須眉。如清《墨香居畫識》說鐘若玉“書法蒼古,一洗閨閣纖弱柔媚之習”,《墨林今話》說她:“以粥字自給,婉力老蒼,不類閨閣人書”。姜淑齋,號廣平內史,漁洋《池北偶談》雲其“筆力矯勁,不類女子”。明朝金陵名妓楊宛,董其昌說她“非直娟秀取姿,回腕出鋒,絕無媚骨”。葉紈紈,《列朝詩集》雲:“書法遒勁有晉風。”宋朝楚州官妓王英英亦是如此。學顏真卿書,梅聖俞曾贈詩贊之曰:“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畫蠶頭魯公體”,又說:“先觀雍姬舞六幺,妍葩發艷春風搖,舞罷英英書大字,玉指握管濃雲飄。風馳雨驟起變怪,明鰩晝飛明珠跳”,以雨馳風驟來形容,其書殆以氣勢見長。這就有如入陣斬斫的衛夫人了。
歷來書評,確實也常以衛夫人稱許這類書家,如施愚山說黃媛介“小楷筆意蕭遠,無兒女態”,《檇李詩系》便說她“書法鐘王,以衛夫人目之”。姜淑齋筆力矯勁,不類女子,朱竹垞題其詩卷亦以衛夫人為說,雲:“三真六草寫朝雲,幾股玉釵分。彷彿衛夫人,問何似當年右軍。郁金堂外,青綾帳裡,小字訝初聞,門掩謝池春草,書遍雙鬟練裙。”
但這些書評,以“不類女子”“無兒女態”“一洗閨閣纖弱柔媚之習”等語來稱贊女性書家,感覺彷彿是在說因為她們不像個女人所以才好。恭維個人時,恰恰貶抑了群體,顯示整個書壇不太看得起柔媚的女性化書風,同時也看不起寫這種柔媚書風的女人。
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書家,要麼就巾幗不讓須眉,刀戟上陣,成為樊梨花、穆桂英、楊門女將、十三妹,令男人低首下心,自愧弗如。雖為女子,斬斫之技,更勝男兒。要麼就由女性柔美的特質,向上超脫,為凌波微步之洛神、如真誥憑虛之女仙,直造男性書人不到之境。清朝時,會稽女子商婉人工楷法,曾仿吳彩鸞寫《唐韻》二十三先與二十四仙兩部,沈芳題詩雲:“簪花舊格自嫣然,顆顆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鸞真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見《香祖筆記》),書格如此,男子又何敢藐視?后之習書者,當於此取鑒焉。
(作者為北京大學特聘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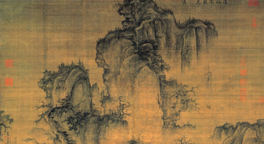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