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展覽裡最為重要的裝置作品《金梯子》,小野洋子希望參觀者能通過攀爬這些梯子,反觀自己的生存之梯——如何沿著梯子向人生高度攀爬。
在美國先鋒藝術圈,身形瘦弱的她風頭甚至蓋過了日本的村上隆、中國的蔡國強,她就是日裔美籍先鋒藝術家小野洋子。不過,盡管擁有眾多頭銜,82歲的她最多為人們提及的還是約翰·列儂遺孀,以及列儂曾經給予她的那句“世界上最著名而不為人知的藝術家”的評價。
前天,在世界各地辦過眾多展覽的小野洋子首次將個展搬到中國——名為“金梯子”的展覽亮相798林冠藝術基金會。盡管展出作品隻有9件,但不少為“大體量”。昨晚,她來到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與青年藝術學子暢聊人生與藝術。她將這次來京不僅僅視作一次簡單到訪,“而是終於到了我心靈棲息了82年的地方。”
聊女人
再給我十年,我會更加不受束縛
昨晚,當頭頂紫色禮帽、戴著墨鏡的小野洋子快步進場時,早已擠滿人的央美報告廳頓時騷動起來。盡管之前已經特意提示不讓拍照,人們還是紛紛拿出手機記錄下與巨星同場的時刻。
她首先在准備好的背板上來了場行為感頗強的“繪畫藝術”,隻見她操起碩大的毛筆在紙面上用中文刷刷寫下幾個大字“世界人民團結福福福福”。正當人們屏息凝氣等待她坐下開講時,她卻拿起話筒突然來了一段長約數十秒、高分貝的吼唱,是一段沒有歌詞的調子,隻能隱約分辨出“啊、哦、咦、唔”。這也讓不少競猜她會如何開場的人們,拼命鼓起掌來。
“我想大家想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小野洋子解釋說,之所以有這樣一段“強壯”的聲音,是因為她小時候曾聽家中仆人談起過女人生孩子的喊叫聲,“那是一種非常恐怖又強悍的聲音。只是男人不喜歡聽到這種聲音,而是喜歡女人唱歌時溫柔的嗓音。”話音剛落,她又來了一段同樣高亢的曲調,並且定定地盯著一旁的翻譯。直到他也模仿著發出同樣的聲音,她才滿意地將頭扭轉過來。
“我也愛男人們,因為他們很可愛,他們理解我說的什麼話,我也很願意跟男人在一起。”這位被外界封為“女權主義者”的女人說,她其實常常稱贊男性,“就像你有孩子的時候,老得去哄這個孩子。”在她看來,這個世界總是存在很多的偏見,比如種族、性別,“如今還有一種年齡偏見。”也正因如此,很多人是受限的,就像她本人曾經就是一個被限制得很死的女人,“但是,當我逐漸成長,我會去掙脫這個束縛,我現在變成了一個不被束縛的女人,但我做得還不夠好。我相信,如果再給我十年,我可以變成一個更加不受束縛的女人。”
話中國
《西游記》告訴世人該如何幽默
與大多數來中國辦展的外國藝術家一樣,小野洋子此次展出的作品也融入了不少中國元素。在《我們都是水》這件作品裡,小野洋子在每一個瓶子的標簽上都用中文手書一個名人的名字,諸如秦始皇、老子、李白、鄧麗君、曹雪芹,也包括列儂和小野洋子。
“中國是被全世界所尊重和愛戴的國家。”小野洋子說,她本人和中國很有緣分,在她10歲以前,一開始讀的中文書就是《三國志》,“我讀的那一套書,由12冊組成,那時候每當我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就讓仆人拿來第一冊,用不了一天的工夫,就能把12冊都看完。”她說,《三國志》幫助她很多,“我從來對血、戰爭、和暴力是不感興趣的,而是關注《三國志》裡那些君王是如何思考、決定一些事情的。”
另外,《西游記》更是讓她扭轉了一種偏見,“它是特別了不起的書,裡面有很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幽默感。很多人認為,中國人乃至亞洲人沒有幽默感,《西游記》教會人們怎麼去幽默。”
盡管行程安排緊湊,前天小野洋子還是抽空去了趟長城,而這趟旅程也讓她對長城多了一分敬畏。“你們可能會覺得我是在給自己的作品做廣告,但的確我以前的一件作品與長城很相像。”據她介紹,那是一件用玻璃做成的裝置作品,當選擇站在玻璃牆兩側的時候,人們就決定了自己人生的一個立場,“一側是防守者,一側是進攻者。”
談藝術
頂級藝術家也不能教別人什麼
這些年,小野洋子在世界各地舉辦了不少展覽,她想讓人們更多記住她的藝術家身份,而不再只是列儂遺孀。
她的作品主題也始終離不開“愛與和平”。而此次北京個展對和平的憧憬,從展廳外的作品《願望樹》花園就開始了。花園裡種植著代表中國君子之道的“歲寒三友”——鬆、竹、梅,藝術家邀請公眾寫下他們的願望,然后挂到樹上。當展覽結束時,這些願望簽將被送往小野洋子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想象和平光塔”,與自1996年以來全世界數以千萬計的願望簽匯聚一處。
緣何有這種藝術理念,小野洋子說:“我們要讓自己變成有創意的個人,首先要肯定我們自己,愛我們自己,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去給予,而當我們能夠去給予時,才是藝術的最大意義——藝術就是給予。”在她看來,很多藝術家會問自己能給予這個世界什麼,“他們不少人會害怕,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一些藝術家認為,自己應該去掙點錢,這的確比做一件好的藝術作品更容易,但實際上當我們決定去做一個純粹的、值得信任的、美麗的藝術家的時候,整個世界會像花兒一樣開放。”
不過,她並不認為自己的理念能為更多人所借鑒,“我想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藝術家應該教別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最頂級的藝術家也未必能教我們什麼。我從來不喜歡做別人的導師。”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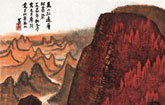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