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赞谈“六法”:六法精论 万古不移

北宋 李公麟(传) 维摩天女像
绢本水墨 156×105.2cm 日本东福寺藏
从顾恺之首创《维摩诘图》以后,陆探微、张僧繇直至北宋李公麟,均有《维摩诘变相图》问世。此件作品在用笔上也具有极高的水准,继承了顾恺之、陆探微的密体画风,对于张僧繇、吴道子的疏略画风也有所继承,从而确立出了密丽披拂而又率略简易的用笔格调。
自谢赫创建“六法”以来,一直被奉为中国绘画品评标准的“金科玉律”,影响深远。中国美术学院王赞教授对“谢赫六法”有着新颖见解,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在此,我们对话王赞教授,进行一场有关“六法”的专题性访谈。
问:王赞老师您好,能否详细谈谈您对“六法”的阐述?
答:南齐谢赫“六法”首先是关于人物画的法则,然后推及山水、花鸟及其他等画科。“六法”中的每一条法则都最直接地、本质地以人物画的要求和标准表现或者衡量绘画作品。我们说法则确立的意义首先是规定了范围;其次是明确了方法;再次则是方便了学习。
“六法”自古以来,就被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阐释,丰满了其内涵,其中,可能存在一些曲解和误读,需要慎重分析。有人说,六法并非都有用处,只需其中五法、三法即可,这也是不对的,每项法则都有意义。我主要纠正的是其中三条——传移模写、随类赋彩、经营位置,尤其是传移模写,涉及到历史上由于绘画载体变化所带来的含义转换,因此,我把所有法则放到绘画的过程中,去探究它们最本质的含义。
问:“六法”之“气韵生动”作为品评的最高层次,您是如何理解的?
答: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中谈到:“……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其然而然也。”“气韵生动”,显然增加了权威的砝码和学习的难度。
因为气韵问题涉及人品人格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技巧的学习,而是包括心灵的涵养。士大夫主流文化人不仅要修炼自身的品格,还想要表达出文化背后的思想情感。刘邵的《人物志》,就是考评士大夫主流文化人人品人格的一本专著。
从字义谈的话,“六法”之“气韵生动”的“韵”字用“和谐”之后仍然“有余”感觉的意思最为贴切。此外,“六法”之“气韵生动”的标准与印度文艺思想理论有非常接近的地方,季羡林先生的论述印度文艺理论关于“韵”字的理解,值得我们参考。
士大夫主流文化人想得到说不出的是为“韵”,“言不尽意”、“言外之意”都是士大夫主流文化人所烦恼的问题。清初王士祯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的让人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
问:“传移模写”是壁画人物画造型法则,请问您是如何推断出的?
答:我推断“六法”为壁画人物画法则的重要判断是依据“传移模写”的实际应用,“传移模写”实则是人物画超大尺寸绘画以及寺庙宗教壁画题材为内容创作时由小稿子(画样)放大到壁画稿子的重要过程。佛教、道教内容都是以寺庙壁画的形式展示和宣传的,几乎所有著名的人物画家都参与了佛教、道教题材壁画的绘画,其中,吴道子最具代表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六法》中提到:“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吴道子的壁画画作“六法”齐备,显然,“传移模写”这一法则的运用也相当高妙。“传移模写”只有“遂恣意于墙壁”方能穷极造化。吴道子虽然不是魏晋时期的画家,但是,他继承了魏晋佛教绘画的传统,他的许多作品都完成于寺庙墙壁。
此外,谢赫“六法”的“传移模写”,是人物画家在大尺寸画幅或大型壁画高难度“写形”过程中切身之感受,从而确立为一条绘画的“写形法则”。
然而,张彦远说过:“至于传移模写,乃画家末事”,我认为这一句话从古及今解释的谬误最大。我个人提出两种说法仅供参考:一种说法为,这里的画家并不是今天所指画家的概念,而是指画工或画匠。“乃”作副词“只”、“仅仅”解。对于“传移模写”仅仅是那些画工才会认为是不重要的事情。另一种说法为:“乃画家末事”的“画家”两字应该分开解释,“画”指画壁的画家,“家”为“一部分人”,即:画壁画的那些人(今天的“画家”一词单指个人,并不指“画家们”)“乃”不作判断词“是”、“就是”解,而作副词,“竟然”解。对于“传移模写”,竟然会是画家们不重要的事情?张彦远以问句的形式设问。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与下文连接更加紧密。同时,该句尾设问句与句首“彦远试论之”句子前后呼应,即:张彦远从“彦远试论之”是“竟然会是画家们不重要的事情?”这是一倒装句式的设问与回答。张彦远一开始谈“六法”,就已经将画壁画和大画“移其形”就是“传移模写”的法则与其它五条法则的相互关系结合起来论述,并且,关于“移其形”的重要性“此难可与俗人道也”,即:一般人都不能够理解。谢赫“六法”首尾相应,“传移模写”既是“六法”的最后,又是绘画行为的开始;“气韵生动”既是“六法”的开始,又是绘画行为最终的评判。同样,张彦远以诘问的方式完成对“六法”的全面理解。如果,将“乃画家末事”的“乃”字理解为判断词“是”、“就是”,那么,“六法”的这一条似乎确实变得无足轻重了。
南齐谢赫“六法”法则首先是人物画的绘画规定和品评标准,更毫无疑问的是壁画人物画的法则,随着山水、花鸟画逐渐从人物画背景的状态中分离出去,“六法”的标准才逐渐普及开来,也只有“传移模写”作为学习阶段的临摹手段加以认识,“传移模写”的法则用在一幅卷轴人物、山水、花鸟画,其法则的意义明显减弱。产生认识偏差的关键就是“传移模写”在人物画“造像写形”过程中,大、小画之间形与神的把握中有着巨大差别。
创作大型壁画“传移模写”在绘画过程的作用,人物画大型壁画不仅仅在小稿子上需要“画样”严谨,更重要的是放大到壁画上需要考虑人物形象的结构、情态、透视和比例等诸多问题,曹家样、张家样及吴家样等等佛教题材的画样只是一个样本,需要对“传移模写”的法度进行规范,同时,还会在“传移模写”的过程中出现“线条粗细”、“行笔意味”和“视觉感受”等等问题。所以,“传移模写”是大型人物壁画重要的造像写形法则问题。“传移模写”之法则在卷轴画、手卷画、册页画(含人物、山水、花鸟)的小尺寸画中的确显得无足轻重。
问:您将“六法”中“随类赋彩”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理”相联系,把绘画理论提升到哲学层面,您能否据此做些拓展说明?
答:依据宗炳《山水画序》中的叙述:“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这与“随类赋彩”在“类”字的用法上相同,其“类”字不作“类别”、“若”或“大抵”解,而应该看成:“夫应目会心为理者”的思维方式赋以色彩。
自然之神的本质往往找不见端倪,只有自然之神栖息于物象之形方能感受到“类”(即“天理”),当“理”进入到绘画物象的形迹之时,才能真正地获得绝妙的描绘,也才能够达到绘画的最高境界。显然,在这样的一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自然之神与绘画之“类”是人的绘画行为一方面接受感悟,另一方面描绘精神而进入“天理”的两个方面。
所谓“理”或“天理”亦或“道”,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认为的宇宙自然之规律。对于“道”和“理”的把握在于清净和无为,以恬淡之情养性,而清净;以混漠之态处神,而无为。
显然,根据宗炳《山水画序》:“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的“类”字意义判断,结合《淮南子》所论“道理”的理解,以“道”之无形而演化为无色而五色成而为“理”之规定,它为“随类赋彩”的“类”字作了注解。
按照谢赫“六法”之“随类赋彩”的法则意义应当是:随着“道”之“无色而五色成”,进而为“理”的色彩理念步入绘画的“赋彩”领域,那么把握“随类赋彩”的法门除了清净无为的心态之外,还在于懂得“类之成巧”之于“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文心雕龙》中对“章”字有所解释,“赤与白谓之章”,章字代表色彩之间的时空交替,同时,还有对“杂四时五色之位”的“五行”、“四季”、“五色之位”等色彩观念的理解。即真正的能工巧匠是能把五种正色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间色和谐地布置于画面,这两者都是绘画之时不可或缺的能力。
中国传统“四季”与“五行”的运转是按照“道”的运行轨迹而产生变化,每一季节之中的“孟、仲、季”与每一方位的“五行”都有着色彩的运用和规定。
“四季”不仅与时辰、位置、五行、音乐、数字、气味有关,而且与色彩中的“青、赤、黄、白、黑”“五色”相匹配。同样,周代典籍《周礼·考工记·画缋》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信息,我们在考量它的价值之时尽可能地将我们的目光和思绪投放到那时的时空范围内,并且以画家的身份体会感受绘画色彩的应用。
懂得了“随类赋彩”的一个“类”字的道理才能理解其法则的真正意义。最终水墨画中黑与白的意义也就顺理成章地突显出来,黑与白的色彩价值就在“五色”之位的运行规律之中,黑与白在西方的色彩理论中不作为色彩的认定,而在中国,黑白却是五色的重要环节,“墨分五色”的本真意义源自“类”字的“理”之境界。更为有意义的是,西方科学色彩观所认定的红、黄、蓝“三原色”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宇宙世界观,及其相关的“五行”中的“青(蓝)、赤(红)、黄”的基本色彩何其相同,然而它们发生的时空作用差距又是何其大矣。
中国传统绘画依据的色彩理论是“形而上”的,主客观领域的色彩观,这样的色彩观已经越来越远离我们今天的认知范围。我们今天的色彩观念是以眼睛的感官认识为依据,“眼见为实”的感性“真实”为基础,更有西方科学色彩观为佐证,这让我们更加难以理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的传统色彩观。
问:提及“六法”之“经营位置”,人们大都认为是指绘画构图,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答:“经营位置”的内容并不是这么单一的,刘勰《文心雕龙》中有提到关于文章位置的安排,文章亦强调其位置的作用,绘画的处理更在其形象的位置安排,可见谢赫“六法”之“经营位置”一定十分重要。
我们还是从壁画谈起,但这次来谈谈壁画的基础——建筑给予的承载空间。根据谢赫“六法”之“经营位置”的壁画人物画要求,这一法则的基础画面是建筑寺庙和道观的墙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记述绘画基于明堂空间而产生的功能,除绘画的功能之外,云台、麟阁、汉明宫殿、蜀郡宫殿都是绘画得以展示的场所和空间。然而这些场所和空间的建筑又都按照“理”的规定布局,阴阳是宇宙的根本,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总规律,因而在古人的建筑营造之中必然遵循太极阴阳的布局安排,同时依据建筑所给予的空间划定出绘画墙面的起、承、转、合,从而使绘画内容与建筑阴阳卦象的“理”结合形成“图载”的综合性功能。因而,壁画墙面的尺寸和壁画内容的组合安排都在其经营位置的筹划之中。
显然,谢赫“六法”之“经营位置”不能仅仅作为画面内容的构图解释,而应该考虑它所处于《周易》六十四卦象体系中象、数、理、占四大要素的规定范围,以《周易》八卦的世界图式分配于四时、四方、阴阳、五行,融壁画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方式”之中。
每当我们步入古代石窟和殿堂欣赏壁画和造像之时,往往更多地关注壁画的内容和绘画技法,甚少体会石窟和殿堂的建造方位、尺寸、比例以及它所蕴涵的阴阳、象、数、理、占的结构关系。但是,作为古代壁画创作的画家,一定需要懂得壁画展示提供的基础位置条件和经营画面内容的道理。
我们不妨以永乐宫壁画的建筑方位、结构形式以及画面内容来见证“六法”之“经营位置”的法则意义。永乐宫三清殿的建筑特点是按照“理”的卦象位置建造的。殿内的尺度、方位、阴阳、卦象是大型壁画理应遵循的外部条件和所承载的绘画要求,我们将永乐宫三清殿的墙壁方位结构即“位置”与壁画图载即“经营”的谋划结合起来理解“六法”之“经营位置”。
无论是永乐宫壁画以道家题材表达了图理卦象的“理”之“经营位置”,还是魏晋以来佛教石窟壁画的题材,一种总体对称性的、阴阳协调性的位置概念,始终围绕绘画经营之道展开。“图载”的本质含义因“经营位置”的图理卦象之“理”凸显出来,我们理解的绘画构图方式只能归类为“图载”之三的图形范围。显然,“经营位置”之图理卦象所占有的空间一定是绘画构图的重要脉络。
问:有关魏晋玄学与人物画的形神关系的问题,您是如何阐释的?
答:魏晋玄学的研究方向是黜天道而究本体,不复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就魏晋玄学本身而言,王弼之学“贵无”,而郭象之学“崇有”,“本末有无”是其讨论的中心问题。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论证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规范的合理性。“贵无”派把“无”作为“万有”的存在根据;“崇有”派只承认“有”是唯一的存在,因而说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有关“玄”,从古至今有诸多注解,其中,据庞朴先生论证,将“玄”字表意作“旋涡”解,以及他将太极图形与水的旋转联系起来解读耐人寻味。由此而引起我对“形神”、“形意”关系的认识。
形神关系一直是人物画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是“六法”之“应物象形”的核心问题,是人物画家绕不开去而又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王弼的“贵无”和郭象的“崇有”,始终围绕着形与神的虚实问题全面展开。究竟“形”是“实”还是“虚”,抑或“神”是“实”还是“虚”?玄学旋转的意义从根本上解决了虚实的外在形态,虚实是旋转的动力之源。形象看起来是实,神采看起来是虚,其实不然。翁方纲在《神韵论》中说:“其实神韵无所不该,有于格调见神韵者,有于音节见神韵者,亦有于字句见神韵者,非可执一端以名之也。有于实际见神韵者,亦有于虚处见神韵者,亦有于情致见神韵者,非可执一端以名之也。”由此看来,神采可以是实,形象也可以是虚。旋转的魅力着力于运动的转换。
从理论上说,庖丁解牛确实达到了形神统一的境界。问题是庖丁如何做才能到达形神的升华。即庖丁在了解牛的骨骼、肌肉、以及骨骼之间间隙的过程所需要“实”的程度,如何才能转化为精神的“实”。这里牵涉到形神之同质的问题。晋人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关于形神关系的论述,是从画画的角度看待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我个人的理解,首先是句读的标注是否可以改为:“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这句话的意思为:如果运用以形写神的法则而不实实在在地面对形象,只采用得意忘形的方法会产生不协调的感觉,传神的发展趋向将会失去。“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晤对之通神也。”这句话意思是:不实实在在地面对形象那是大大的失误,摹写过程素丝斜纹没有对正摹本只是小失,不可不注意大失与小失的问题。一个形象精神的明亮和精神晦暗的程度,关键是要面对实实在在的形象,才能达到通神的境界。
顾恺之“以形写神”的关键仍然是形象的“实对”。形象与神采总是相互依赖与相互独立的,形象的表达从来不会影响神采的丰满,神采的灿然必定依赖于形象的塑造。由于中国哲学“言意之辨”和“形意之辨”的命题关系,形与神的问题似乎也变成了一对矛盾。然而,形与神是太极图的两个极点,是旋涡转动的两个动力之源,玄之又玄的本质是矛盾的统一。他们矛盾的焦点是形与神表达程度的高低或形与神暂时的虚实转化,而不是形的消失和遗弃。对待形与神的看法有两条完全相反的思维路径,一条是由形的表现进而神的再现;一条是由神的引领完成形的升华。两条思维路径方向不同,其结果必然不同。由形及神是绘画的初级阶段,由神及形是绘画的高级阶段。对形的把握程度取决于对神的认识高低。只有对形“游刃有余”的精湛表现,才有“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踌躇满志”。反之,只有对神的充分认识和精神的品格追求,才能真正地完成对形的自由取舍,达到“动刀甚微,如土委地”。领略“道”之境界,达到“玄”之目的。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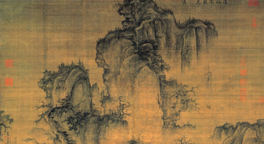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