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生涯如何影响11位画家的中国画创作
原标题:留日生涯对他们艺术的启示
华天雪
在留日画家中,有11人在中国画改良方面有突出成就,他们是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朱屺瞻、陈之佛、丰子恺、关良、方人定、丁衍庸、傅抱石和黎雄才。
上述11家中,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和方人定、黎雄才为两代的“岭南派”,艺术根基均直接间接地得自“隔山派”的居廉。居氏在题材上以状写岭南风物为主,通过对景写生、潜窥默记、剥制标本写生等方式,将写生察物推至令人惊叹的程度,形成了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写生方法。又创“撞水”、“撞粉”法,对光照感、滋润感、质感等均有更“写实”的特殊把握。居氏画法掌握起来相对容易,授徒多经一年勾稿临摹、一年写生即可出徒。居氏自1875年在“十香园”设帐授徒至1904年去世,三十年间门徒数十人、私淑弟子近百,风格流韵主导广东画坛达半世纪之久。可以说,居派的“审物”精神和写实追求,不仅不期然地契合了之后的科学主义,也与日本画坛“日洋融合”中的主流倾向不谋而合,这是广东画家尤其是“岭南派”画家能够更容易地接纳和融合日本因素的重要原因。
高剑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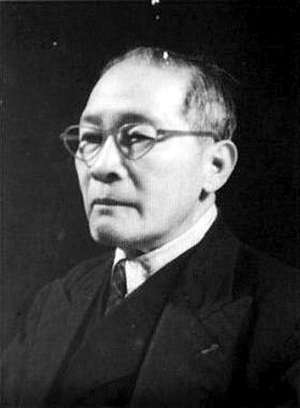
高剑父
高剑父(1879-1951)与日本画的关系复杂而密切,所谓“其得名,缘乎此;其为人诟病,也缘乎此”。他自1906年东渡日本游学,又于1908、1913、1921、1926年间多次到过日本,先后在“名和靖昆虫研究所”及“太平洋画会”、“白马会”、日本美术院等美术团体设立的“研究所”学习过博物学、雕塑、水彩画和日本画的一般知识。而赴日之前,他已从居廉处学得地道的小写意花鸟,又曾在伍德懿“万松园”遍摹历代名迹和在澳门格致书院接触西画并拜师学习炭笔素描。

高剑父《昆仑雨后》
在1906年的游学期间,高剑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即在他留日接触新绘画之初,就兼具了画家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于是,用政治革命思维来思考艺术革命方案就变得顺理成章,他的“拿来”甚至“抄袭”也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画学”问题了。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游学之于他的意义首先在于,日本画坛的改良带给他推行国画革新运动的样板,让他找到了与政治革命理想相匹配的艺术革命的方向和可能性。而他对日本画坛的具体借鉴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的扩展,他的那些令人惊讶的用中国画所画的残垣断壁、战场烈焰、飞机、坦克、骷髅头、十字架、乌贼鱼等等,堪称是百无禁忌的,无疑直接受启发于日本画坛;一是画法的融合,他在居派写生法、撞水撞粉法基础上,对四条派的空气感、光照感、宁静而深邃的诗意境界,圆山派的状物模形、流畅优美,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吸收,又进而融合浙派笔墨的淋漓、奔放、外张,碑派书法的苍劲、雄健、奇险,创立了霸悍、恣肆、峭硬、豪迈的风格面貌,这是一种富有时代精神气质的面貌,也是对以淡逸、浑融、内敛为主要追求的传统审美的一种突破。
高剑父一生致力于教育,门生众多,在他直接间接的带动下,很多人赴日留学、游学,景象颇为壮观,连同他所做出的那些“融合中日”的大胆尝试和最终立足于笔墨的创造性风格,均可看作是他为中国画改良做出的贡献。
高奇峰

高奇峰
高奇峰(1889-1933)一生追随四兄高剑父,所学所宗、立业成名均离不开四兄的栽培、扶掖和影响。其绘画大致有两部分根基,一是由四兄传授的居派写生方法和写意花鸟技法,一是日本画坛田中赖璋、竹内栖凤等人的方法,其中田中赖璋为其直接授业的老师,而对竹内栖凤等圆山、四条派画家的学习和关注则更多受四兄的影响。目前可知他曾两次赴日,即1907年夏至冬、约1913年《真相画报》停刊后到1914年秋,时间均不长。实际上,对于已经有状物写生能力和熟练掌握了撞水撞粉法、没骨法的高奇峰来说,“拿来”一点田中赖璋或竹内栖凤的技法无需太长时间。

高奇峰《猛虎图》
与四兄一样,高奇峰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改良,努力将“西洋画之写生法及几何、光阴、远近、比较各法”,与“中国古代画的笔法、气韵、水墨、赋色、比兴、抒情、哲理、诗意”等“几种艺术上最高的机件通通保留着”,融合在一起,以响应孙中山“向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的口号。艺术在他绝非“聊以自娱”或“徒博时誉”,而是要本着“天下有饥与溺若己之饥与溺的怀抱,具达人达己的观念,而努力于缮性利群的绘事,阐明时代的新精神”的。但他的现实关怀并不表现为直接将飞机、坦克画进中国画,也甚少涉猎人物画,而主要是借助翎毛走兽花卉等形象,在相对传统的理路上作间接表达。他“融合”的具体表现主要是两种,一为背景的渲染,一为形象的写实刻画。背景的渲染尤以月夜、雪景为典型,将传统层层烘染的手法和借自日本的水彩技法相融合,增强空间感,情景交融。而在其鹰、狮、虎、马、猴等代表题材中,多将传统的“撕毛”笔法与西画的明暗光影法相结合,极富质感和写实感。此外,尤重营造意境,但其意境不是传统文人画讲求的诗意,而是有日本气息的雄强、孤清、沉雄、皎洁、感世伤时之类的境界,以革命理想为支撑,充满英雄气质,拓展了翎毛走兽花卉类绘画的精神寄寓性。
陈树人

陈树人
陈树人(1884-1948)于1900年拜师居廉,1907年赴日,1908-1912年入读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绘画科,1912-1916年入读东京私立立教大学文科,滞留日本凡9年,是11家中在日本学习最久的人。陈树人
就读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前后,正值“日洋融合”实践的盛期,其代表人物竹内栖凤、菊池芳文、都路华香、山元春举等均先后任职该校,即陈树人“实际上也就是进入了当年京都日本画坛的核心氛围之中”。

陈树人《淡黄杨柳舞春风》
陈树人的绘画风格成熟于1930年代。形式感是其绘画的突出特征,尤其在其花鸟画中,常以直线分割、交叉、排比甚至十字形来构成画面,画面形象也常以“截取”式或特殊视角造成新奇感,这种“形式”主要来自日本画的装饰性和西画的现代构成,极具现代感,辨识度极高。陈氏线条也非一波三折的书法用笔,而是一种偏于日本画的匀整流畅、富于装饰感和韵律感的线条。陈氏花鸟用墨少、用色多,但不追求色彩的微妙而丰富的变化,对居派塑造体积感的撞水撞粉法也极少使用,而是把“自然界丰富的色彩进行弱化、温化的处理”,既有文人画式的淡雅,又有水彩画的明快和透明,其情调渊源也主要是日本画的。花鸟之外,陈氏山水也自具面貌,最大特点就是空勾无皴,勾法主要来自山元春举的折带状短线,用墨用色也同样不求丰富而求简洁、单纯,山水结构多被概括为几何形,构图中适当将透视法融进传统山水图式,背景多留白,气质“清劲”、“峭拔”,是介于中西或山水画、风景画之间的一种样式。
总之,作为画家的陈树人,虽在画学出身、学画经历、艺术主张等方面,无疑属于“岭南派”,但从画风到行为都有不为流派所掩的疏离、淡逸、特立独行的气质。他在风格成熟之前,虽然也有诸多对日本画的临仿,甚至也能找到对山元春举《落矶山之雪》、望月玉泉《芦雁图》等的几近相同的抄仿之作,但其成熟期的中国画却能在个性和修养的统驭下,将诸种摹仿痕迹消弭、转化,极富创造性地确立出自家面目,为中国画改良提供了一个相当别致的个例。
方人定

方人定
方人定(1901-1975)于1929年赴日,此前跟随高剑父约6年,无论山水、走兽、翎毛、花卉,“跟足当时新派画的一贯作风”,其间他于1926-1927年作为“新派画”代言人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论争,不仅令画坛瞩目,也直接促成了他的留日——抱着一探日本画和西画之究竟,弄清“二高一陈”是否抄袭了日本画,以及决心从高氏不擅长的人物画入手走出自家面貌等目的,方氏于1929-1935年间两度赴日,先后在川端绘画研究所、二科会骏河台洋画校、日本美术学校等处,研习“西画及人体写生”,并着意研究日本画人物画,是中国留日画家中在人物画上下功夫最大、作品最多的人。从方氏这段时期的作品看,他所掌握的西画造型是日本画坛简洁粗犷一路的造型风格,这也是丁衍庸、朱屺瞻、关良等人所掌握的风格,即“抓大结构、大关系”的近代风格,而非徐悲鸿式的精准的古典造型。这个造型基础对于后来转向写意的丁衍庸、关良、朱屺瞻等人来说或许是有利因素,但对于要在写实人物画上继续发展的方人定来说,就多少会在人物表情、动态的生动性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等方面,稍嫌力不从心。但无论如何,得自日本的造型能力成为他转向人物画的保证,其一生的造型特征未离这个基础。
方氏“在日本很重视资料的搜集”,沿着日本画在题材上广泛开掘的道路,从城市生活、农村生活、抗战生活到历史故实,从人体、城市女性、农妇、农夫、画家、逃难者、乞丐、盲人、酒徒、客途者、失业者、猎人到新社会的劳动者和古装人物,题材之广在20世纪画坛几乎无出其右者。
方氏人物画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35年之前为融合高氏、居派和西画、日本画方法时期,有工笔、半工写、纯色彩、墨彩等多种尝试,大多在细勾轮廓线后将光影法和平涂法相结合,单纯、明净,比日本画厚重,比高氏秀润,有些画面色调及形象呈现类似高更的原始风及稚拙感,有些画面弥漫着日本式的静谧感。主体人物多被处理成“浮世绘”式的静态、近距离、特写式,占据画面绝大部分面积,并因这种“拉近”而有更细腻、丰富的面部刻画,这个特征在其之后的创作中一直保持着;1936年后逐渐减少矿物色使用,淡化日本画式的雅致、恬静和装饰感,更多笔墨语言的加入,写意成分增多,并呈现出“苦涩凝重”气质,真正进入所谓“吐露人生”、“批评人生”、“表现人生”的境界,是20世纪前期人物画家中在现实主义方向上做出最多尝试的画家;建国后转向以歌颂为主调的明朗欢愉,色彩再度变得浓丽、唯美,但已不再是早期的日本画法,而主要是传统的勾勒填色方法,工写结合,属于有新年画特征的新人物画,并将这些画法运用于花鸟动物画,向传统适度回归。
黎雄才

黎雄才
黎雄才(1913-2001)被认为是“高剑父所提倡的‘现代国画’主张最忠实、最富于实绩的实践者之一”,他与日本的关联也最先藉由高剑父。他艺术上早慧,16岁便被高剑父收归门下,悉心栽培,又被推荐到何三峰在广州创办的烈风美术学校学习素描。从他赴日前的作品看,他对焦点透视、时空再现、素描与笔墨的结合,以及转自高氏的日式水墨渲染、湿润朦胧的氛围等等,均能把握得很到位,在“折衷中西”的道路上已经有了不少切实经验。

黎雄才《云南曲靖沾益道中》
1932-1935年,黎雄才在高剑父资助下赴日留学,入日本美术学校学习日本画。与师辈们不同的是,他没有“革命”的激情和重负,而主要是个潜心于艺术的纯粹的画家,兴趣点主要在艺术“语言”。他选择了与高氏不同的“朦胧体”横山大观、菱田春草等为主要学习对象,着迷于由“没线”、晕染营造的空间气氛和迷蒙境界。尽管在风格确立后,“朦胧”气息逐渐淡化,线条再度被强化,但在他最典型的画面中,那种“苍莽淋漓的色墨效果,仍然使人想起大观、春草飘渺空灵的‘朦胧’氛围”。20世纪40年代,他用大约十年赴川蜀、西北旅行写生,在大自然中寻找“范本”,再度体悟“真实”,“作风一变而成为气势恢廓,沉雄朴茂”“以气蕴清遒雄健见胜”,完成了取借、消化到创造程式的过程。
朱屺瞻

朱屺瞻
朱屺瞻(1892-1996)之于中西绘画的经历极为特殊。他出身于好书画、富收藏的儒商之家,中国画启蒙很早,且一直自修不辍,但自21岁决心投身画坛时,选择的却是西画——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木炭画和铅笔静物写生。从此,中西两种绘画就一直并行在他的艺术中,几乎不分伯仲,他可以晨起练书法,继作铅笔静物写生,授课之余或作油画或作室外风景写生,晚上画山水、花鸟,直至88岁还有多幅油画问世,90岁还表示要“闭门重温习一些油画,以待进一步作中国画之新探索”,可以说,他穿行于中西间无丝毫障碍。

朱屺瞻《杜鹃花》
1917年初夏,朱屺瞻赴日入川端绘画研究所师从藤岛武二学习素描、油画及西洋绘画史,原拟投考东京美术学校,故学习极为勤奋,除参观画展外几乎足不出户。数月后因家事匆匆回国,被问及日本风土人情皆茫然不能对,但对东京博物馆中所见凡·高、塞尚、马蒂斯的作品,终生不忘。即日本对于朱屺瞻来说,是西画中介者加转译者,所“转译”的是日本老师所理解的注重“大结构,大关系”的造型理念。
回国后他一面画后印象派、野兽派式粗犷、豪放一路的风景和静物,频频以现代派油画家身份亮相于各个展览中,一面置身于与以黄宾虹、王一亭为核心的上海传统中国画圈子,在中国画方面亦不断精进。1953年62岁时试作毛笔写生,开始凭借写生将石涛、徐渭、金农、方从义、李复堂、吴昌硕、齐白石乃至凡·高、塞尚、马蒂斯相融合,在70岁左右初具面貌。又在1973年“文革”中,以82岁高龄,凭照片和印本,遍临历代名迹五十余帧,不斤斤于形似,从气势、意趣、笔法诸方面悉心揣摩,终创雄壮、苍劲、浑厚、朴拙、恣纵、古厚的大写意面貌。他的这种以笔墨为根本,以几乎从未停歇的对中西绘画的并行研习为方式的尝试,为“融合中西”和“中国画改良”提供了独特的经验。
陈之佛

陈之佛
陈之佛(1896-1962)于1919年以官费生资格赴日,先从水彩画家三宅克己学水彩画法,又到白马会洋画研究所学素描,安田稔画室学人体素描,于1920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为中国留日学习工艺图案第一人,而由图案改画中国画,恐怕也只有日本画坛能够孕育这样的可能性。装饰性、色彩感以及绘画与工艺的无差别性、融通性,是日本美术的特征和传统,故有17-18世纪的装饰画派宗达-光琳派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日本审美趣味,这是陈之佛能够“在工艺美术与工笔花鸟画之间游走”的重要原因。
另外,据研究推测,日本大量的以花卉鸟兽为主的画谱也应该是陈之佛转向工笔花鸟的重要凭借,影响面极广的狩野探幽的《草木花写生图卷》、尾形光琳的《鸟兽写生图卷》、渡边始兴的《鸟类真写图卷》、圆山应举的《昆虫写生贴》等,很可能也是学习图案的重要参考,而且也不难找出与陈氏花鸟造型的渊源关系。
陈之佛工笔花鸟画首次亮相于1934年9月的中国美术协会第一届美展上,距留学归来约十个年头,这期间他有机会观摩到宋画原作及印刷品,也做过临摹,但对日本花鸟画更丰富的图像积累,在其工笔花鸟画初期还是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包括在树干、树枝、树叶、湖石及禽鸟羽毛上常常使用的“积水法”(宗达-光琳派常用技法),常以锈色、暗花青色为统调的色彩效果,以及日式沉静、典雅的意境等等。当他在多年研究图案、造型和色彩规律以及花鸟写生的基础上,综合了宋画、日本花鸟画、水彩画等多种元素,笔线质量大为提升后,“日本气”逐渐隐去。工笔花鸟难在工致而能生动,只有像陈之佛这样,笔线达到细而不弱、柔中见骨、紧劲中有松活、工整中含虚实,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另外,工笔花鸟大多重写实感、色彩感及程度不同的装饰感,创造风格的余地相对有限,风格赖以成立的主要因素是精神性,陈氏作品所营造的高洁、静寂以及建国后的喜悦与昂扬等境界,背后支撑的实为传统文化修养和不凡人格,这些内在的东西最终化解了外在的技法,实现了融合后的创造。
丰子恺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的“中国画改良”最为独特。他于1915年考入浙江一师,受图画老师李叔同影响,从石膏模型的木炭素描和风景写生开始,确立了学习西画的志向;又得国文老师夏丏尊的悉心栽培,在文学上大为长进,为其日后源源不断的画题文思打下了基础。
丰子恺于1921年春至冬赴日游学10个月,以在画塾练习素描为主,并偶然“发现”了日本乡情漫画家竹久梦二(1884-1934)。梦二式“漫”画不属于滑稽一类,实为用笔简约却能生动传神的简笔画。丰子恺所理解的梦二,有“简洁表现法、坚劲流利的笔致、变化而又稳妥的构图,以及立意新奇、笔画雅秀的题字”,“其构图是西洋的,其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是东西洋画法最好的调和,并认为像自己这样有一点西画基础,又无心无力作油画、水彩画且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最适合从事这类漫画的创作。梦二“画中诗趣的丰富”常能引丰子恺想到古人诗句。他自小喜欢诗词,诗话、词话一类书籍常随身伴读,常因某诗句的触动而酝酿画面。可以说,梦二指引了丰子恺的绘画方向,而从取之不尽的古诗文中寻找“画龙点睛”的画题,则成为他很快摆脱梦二痕迹,发展出具有中国精神意蕴面貌的重要因素。无论古诗词意画、儿童相、学生相、民间相、都市相、战时相、自然相还是护生系列,俯拾即是的日常生活均可因其独运之匠心而诗意隽永,对中国画的意境做出了极大的拓展。
丰子恺没有学过中国画,但能诗、能书、能治金石,尤其在书法上下了长久的功夫。其书以索靖为基础,又得益于《张猛龙碑》,沉着而飞动,活泼多姿,古拙多趣。以这样的笔线作画,虽不是一波三折、墨分五彩,没有皴法、描法,甚至构图也是西画方式的,但依然是“地道”的中国画。总之,丰子恺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认知选取了有别于常人的摹借对象,又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体悟,充分调动自己所长,完成了一次别具一格的“中国画改良”。
关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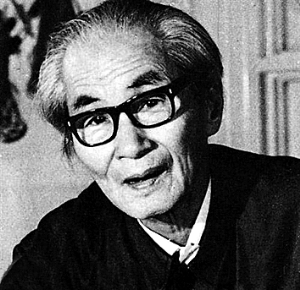
关良
关良(1900-1986)于1917-1922年赴日留学,先后在川端绘画研究所和太平洋画会研究所学习古典素描和糅合了印象派的写实油画,但对日本洋画界追摹的西方现代派更感兴趣,偏爱高更绘画的构图、笔触、装饰性和朴素、宁静的意境;偏爱凡·高对形体、色彩的夸张,以及如烈焰般的热情和表现力度;也偏爱马蒂斯单线平涂一类作品的宁静调子、装饰味和浮世绘式的东方情调。他曾说:“上述三位大师对我的影响都是‘终身制’的”。
留日后的关良长期中西画并行发展,即一面教授和创作西画,一面约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画领域探索,而且一开始就将这种探索立足于笔墨;同时有意识地与京剧界琴师、名角、名票交往,将其探索题材锁定在“至善”且“尽美”的京剧人物上,1935年甚至正式拜师学老生,后在杭州又得以长期向武生盖叫天求教,对种种手势、身段、台步均有深入领会。他的京剧人物是从一出戏的千百个表情、动作中反复推敲而来的一瞬间,因此极为传神和耐人寻味——它们不是剧照,是竭力调动的所有细节的“凝集”,是对戏曲舞台的再造。其造型常常借助几何概念,故能简练而明确,且有儿童画般的稚拙与率真;笔线紧密结合形体、色相,准确而精简,虽非一波三折的书法用笔,但“钝、滞、涩、重”,意味淳厚;用墨浓淡枯润相宜,层次分明,厚重、深秀、朴素;用色明朗、强烈、不细琐,有扣人心弦的表现力。他的这种抓住一个题材不断求深求精的探索方式,他的广采博收又不露痕迹的吸收、消化和再造能力,他对笔墨质量的坚持等等,均为中国画改良提供了宝贵经验。
丁衍庸

丁衍庸
丁衍庸(1902-1978)于1921-1925年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其间对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等现代画派发生浓厚兴趣,从现存留校彩色《自画像》看,造型简括,笔触奔放,色彩主观而强烈,大体能反映其日本所学和个性倾向,这也是他回国后油画创作与教学的一贯倾向。和关良、朱屺瞻一样,丁衍庸也是中西画并行发展的。大约从1929年起,他开始对古代金石书画尤其是八大发生兴趣,经三四十年的沉潜与摸索,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其中国画终于摆脱所有东西方的摹借对象,臻于成熟。他的花鸟动物画在造型的生动之外,将八大的变形、简略、奇异、丑怪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八大之后无人做到的,同时笔墨兼具八大的浑厚与灵动,但比起八大的冷逸脱俗,更多了些生趣;其山水画在传统章法上融合了更多现代构成、几何化、符号化等因素,结构更简,一目了然,同时用笔极松,趣味稚拙;其人物画包含了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包括神仙、妖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夸张、奇异、丑怪的种种面相,富有喜剧式的戏谑与反讽,是香港世相的真实反映,发人深省,比现实主义绘画更具直戳痛处的刺激感。

丁衍庸《粉墨登场》
或许丁衍庸转向中国画之初衷不一定是为“改良”,但他的确为“改良”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启示。他对古今中外的借鉴、融合绝非限于线条、造型、色彩、构图之类表层元素,而是从诗书画印入手去整体把握传统文化精神;他不为谐谑而谐谑,不为怪而怪,而是在极为奇特的形式感背后呈现出深刻而敏感的精神性;他对笔墨的深入修炼使得油画出身的他成为一个中国画的行家里手,保证了其中国画探索绝非票友式的浅尝辄止。总之,丁衍庸以其苦功、创造力、胆识和悟性,成功完成了最大跨度的“融合”。
傅抱石

傅抱石
傅抱石(1904-1965)于1932-1935年间留日,先是以改进景德镇陶瓷的名义赴日研究工艺图案,又在1934年4月至1935年7月入私立帝国美术学校研究科,从金原省吾治画论和东方美术史——该校师资阵容强大,此外尚有中川纪元教西画,山口蓬春、小林巢居、川崎小虎教日本画。尽管在校学习时间并不长,但他关注日本画坛的各种动向,还利用篆刻之长建立了与日本画坛的广泛联系。

傅抱石《山水》
傅抱石在赴日前有约七八年的书画印方面的自行摸索,对四王、石涛、八大以及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等流行画风均有模仿。留日后画法有了明显变化,勾、皴、点为主的画法更多被泼墨、晕染所取代,受日本画追求画面气氛的影响颇为明显。有研究表明,他受到过竹内栖凤、横山大观、桥本关雪、富冈铁斋、川合玉堂、镝木清方、池田辉方、小杉放庵、平福百穗、内山雨海、子影庵等画家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也能找出不少模仿痕迹明显的作品,但却较少受到“二高”那样“日本气”的强烈诟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笔线的质量——类似顾恺之《女史箴图》的细劲、圆转、绵长、流畅的线条,以及纯熟的散锋笔触,在严谨造型的同时,兼具抒发情感的表现力,或许仕女、士大夫的形象是借自日本的,但画这些形象的笔线却是源自传统中国画且极具质量的;另外,其人物画和山水画所表达的精神性,始终与传统文人画有着明确的一致性,其绘画发展始终未离文人画脉络,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他对日本画画法和形象的借鉴。可以说,在将外来因素融进文人画传统方面,傅抱石做出了少有人超越的贡献。
上述11位画家,年龄落差达31岁,赴日时间由1906年到1932年,前后相错26年,几乎贯穿了民国美术留日史的始终,其中“二高一陈”为1910年之前,关良、朱屺瞻、陈之佛、丁衍庸、丰子恺为1924年之前,方人定、黎雄才、傅抱石为1932年之前,大约属于三“代”。相对来说,第一“代”模仿痕迹较多,第二“代”风格创造性较强,第三“代”更多偏于技巧性,但立足于笔墨几乎是他们创立风格的共同特点。他们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外来“日本因素”和由日本“转译”的“西方因素”,在“中国画改良”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还需注意,从大的方面说,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美术环境等均有变化;从个人的方面说,他们的际遇、个性、知识结构、学艺经历等也各自不同。他们以差异甚大的个体性应对“融合中西”的时代性,所呈现的艺术面貌虽有共性,但更多独特性,在将他们纳入“中国画改良”的范畴中来讨论的时候,只有充分重视他们的种种独特性,深入分析他们各自的特点及其成因,才会真正对“中国画改良”这一课题有所推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标题系编者所加。)
来源:东方早报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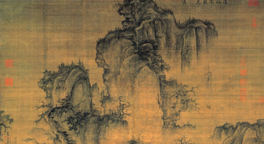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