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苏轼的笔墨心情

花气薰人帖(局部) 黄庭坚
《花气薰人帖》是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一件书法小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内容为一首28个字的小诗,意兴淋漓。老朋友王晋卿数次写诗给黄庭坚,他都没有及时答和,于是王晋卿通过频频送花来催促,想以此提醒黄大诗人。以诗歌作为媒介进行文学上的切磋,是古代文人们进行交往的方式——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方式,人们通过唱和、酬答来表达对风景、历史、事件、人物等的看法,或者记录当时的集体记忆与感受。文人之间的情感在这样特别的叙述、感慨、评论的过程中加深,由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或社群。
面对王晋卿送来的花,黄庭坚享受着它们开放时的香气,仿佛平日修行安定的功夫都被破除了,他想不到自己人过中年竟然还有这样为自然感动的心情。在这个春天,诗人终于动起写诗的念头,却像经历着一层层逆水的滩头,船要上行,何其艰难:“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黄庭坚是一位执着的修行者,他与佛教人士交往频繁,在他们之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甚至享有在禅宗著名经典《五灯会元》中留下声名的殊荣。他的诗歌也非常有特色,写作结构往往出人意表,令人猜测不透,其“山谷体”获得过“硬转折”和“瘦硬”的评价。当我们细心审看这幅《花气薰人帖》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禅、诗、书是怎样同臻一境的。
黄庭坚的运笔温和而倔强,虽然是写草书,笔速并不很快,沉着冷静的过程既像是按照预设的路径行走,又像是在缓缓行进中等待无数种可能的创生。这跟禅宗中的“渐悟”和“顿悟”何其相似,运动中的“遵守”“期待”和“想象”并不矛盾,它们统一在“禅”中。
可是,书写的进程被打断了,黄庭坚将之归罪于“花气薰人”,也许并非如此,但现实是,笔墨既有的节奏慢慢产生了变化,牵绕、萦带也渐渐多了起来,笔画越来越方、硬,墨色越来越焦、渴,速度越来越快、急,字里行间的“硬转折”出现了,随着情感的舒泄,神采也聚合呈现出来:嗔怪、惊喜、狡狯、无奈、烂漫,一时心绪自然而随性地流淌泄露在纸间。
《花气薰人帖》硬朗而饱满的笔画让人印象深刻,观察生活细致入微的古人用“折钗股”来形容书法的这种笔画形态:笔毫平铺,笔锋圆劲,如钗股弯折仍然体圆理顺。“山谷体”的奥妙也尽在于此。诗意点亮了生活,让这幅信手而成的作品成为珍贵的“文物”。如果说闲适的生活能够滋养艺术,那么困顿、苦难的生活则更是艺术的添加剂。
和门人兼好友黄庭坚一样,宋代最天才的文人苏轼也在远谪的遭际中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苏轼的乐天性格是那样的“无可救药”,他非凡的性情化解了不少厄运和悲苦,他甚至在晚年自题小像的诗句中得意地宣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即便心理素质足够强大,在“乌台诗案”之后左迁黄州的苏轼,仍时时被焦虑、悲伤甚至凄怆等心情所折磨。来到黄州三年后的寒食节,苏轼写下了两首寒食诗,后又写成长卷,留给我们一个悲叹伤惋的天才的背影: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生活竟能这样沉重而令人绝望!南方湿冷阴寒的气候无意让苏轼的心绪更加糟糕。在以忠孝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的时代,苏轼却经历着“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煎熬和痛楚,那种“死灰吹不起”的潮湿、困顿、压抑、遗憾、潦倒、孤寂、无助和欲哭无泪,简直穿越千年,扑面撞来。在诗帖中,苏轼一改惯常的温柔敦厚,顿挫提按,转腕如轴,加粗、放大、拉长,沉雄、激昂、婉转,墨迹的变化犹如心情和命运的变化。在《寒食诗帖》中,我们看不到前后赤壁赋书卷中的那种平缓温厚,看不到《中山松醪赋》中的那种畅达浩荡,也看不到《渡海帖》中的那种率真无畏,只有一股倔强、执拗、孤闷、彷徨。这件光彩照人的杰作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声名,人们将其评为继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经历过两宋的文祸和党政,不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肯定,人们对苏轼及其书法的喜爱程度只增不减,这也让历史的书写者真正感受到纯粹的艺术所能产生的巨大魅力和影响。
元符三年(1100年),应收藏者蜀州张浩之邀,黄庭坚在观赏《寒食诗帖》之后,于拖尾题写了长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出于对苏轼的理解和认同,黄庭坚以轻松的笔调赞誉了苏轼这首诗同时也是书法作品的高超水准,他认为其中熔冶了前辈大师如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等的高明技法,并提炼出东坡书法独有的意趣。这些评价可能会让熟悉苏轼和黄庭坚的人们想到以前两人互开的玩笑,黄庭坚戏言肥扁斜侧的苏字是“石压蛤蟆”,对比这个很难看出有什么赞扬意味的评价,《寒食诗帖》的题跋仿佛出自另一位欣赏者的手笔。当然,黄庭坚正是看到了《寒食诗帖》的特别之处,首先是字体不再一味肥厚倾侧,而是大小错落参差,动感十足。二是随着造型的前后变化,许多字的重心也不再稳定地构成中轴线,由此看上去更为自然且更具惊喜,正如苏轼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自然而生活化的艺术,也让生活更自然地艺术化。
不过,可能只有很少人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作为卷尾题跋的黄字,竟然要比作为主体中心部分的苏字大许多,而在内容上来看,黄庭坚在遵循题跋旧式赞扬苏字之后,又谈起了自己,谈起了自己的书法和苏轼书法的微妙关系。正像石守谦先生观察到的那样,“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的自评分成了好几个层次,虽然承认《寒食诗帖》的巅峰成就,称得上是书界的“佛”,但也表露了对自己书法成就的绝高信心,欲与东坡一同称佛称尊;非但如此,他所谓的“于无佛处称尊”还要安排由东坡之口说出。推东坡为“佛”,自许为“尊”,再以“尊”向“佛”抗争叫板,这就是黄庭坚以如许大字骄傲题跋的争胜心理。
其实,在写这段跋文之际,正是黄庭坚生命由困顿转向奋发的好时光,徽宗登基以后,他的“前罪”遭赦,更得到监管鄂州盐税的官职。本拟即刻赴任,却因江水大涨不能成行,索性乘舟到青神和戎州探访亲友,盘桓三月有余,其间应远来求字的张浩之请题跋,留下了这段与苏轼的隔空对话。也许是对苏轼太过熟悉,也许在川期间看到太多苏轼的“身影”,黄庭坚的这段题跋看起来写得非常自然,又暗含力量,绝不比他刻意为之的任何一件书法逊色,或有过之——因此,题跋内容中对《寒食诗帖》的评价转而成为黄庭坚的自况,“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就算让黄庭坚再写一次,同样也难以达到既有的样貌和效果。
次年,也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五月,黄庭坚写下了他另一件重要的作品:《经伏波神祠》长卷。这件书法虽非擘窠大字,仍觉惊人心魄,文徵明评其“真得折钗、屋漏之妙”。苏轼和黄庭坚二人早年均学颜真卿,在颜、柳之外,黄庭坚也常临苏字,直到他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开始剧烈变法,终于脱出陈臼,形成长枪大戟、舟子荡桨的个人面目。《经伏波神祠》是黄庭坚晚年的代表作,黄庭坚亦颇自得,他在卷后题道:“持到淮南,见余故旧可示之,何如元祐中黄鲁直书也。”在诗法上标榜“夺胎换骨”的黄庭坚,终于见证自己书法的“夺胎换骨”——不过,就像苏轼在《寒食诗帖》中写到的“病起头已白”那样,黄庭坚也以“山谷老人病起须发尽白”几字收束《经伏波神祠》全卷。
未及四年,这位耿直、狷介、高傲的老人,在贬所宜州那个狭窄、阴暗、潮湿的戍楼中凄苦孤寂地离开人世,此时他的身上刚刚背负起一条叫做“幸灾谤国”的新罪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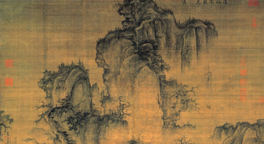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