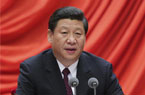元朝是蒙古统治者所建立的一个王朝。元代少数民族入驻中原为政的特殊性,其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也使得文人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文人受到推荐和赏识,积极参与政治而官居高位;一部分文人由于生存所迫而入仕为官,但却迫于正统儒家性情的纠结而折磨半生;一部分文人虽亦热衷于仕宦,却时运不济而沉沦下僚,终生无望出头之日;一部分文人则迫于世俗压力或自觉放弃了仕途追求,或隐山野,或隐市井,成为社会边缘人士;还有一部分文人经营商业,举办雅集诗会来聚集和收留散野文人,成为商圈歌馆应景;还有一部分文人逼迫加入手工行业,亦文,亦画,亦工,创造今天所见不朽的文物艺术品。尽管有上述亦有区别,但是元代文人的思想倾向本质上多有亦同,沉沦感和危机感并存,自卑感和使命感碰撞。
元代文人的情怀大体上上伤感的,从元诗、元词、元曲、散曲、杂剧、南戏等诸多作品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他们的作品要么抒发了对社会底层的同情,要么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或者表达对正统文化的眷恋和回归。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用“肃杀的‘西风’来表达他们的“凄凉”和“惆怅”。“ 西风”一词唐代文人多用,宋代文人也多用,多以借“西风”来表达“孤苦”和“飘逝”的心境。当然,元代文人笔下的“西风”不仅仅于此,也趋于多样的情怀和表达,元代文人用“西风”二词最为多,好像与元朝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著名的当属元代文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了。也许通过对元代文人多用“西风”的词句,可以窥探那些隐含内心深处的诸多情怀。比如:
马致远“古道西风瘦马”(《天净沙﹡秋思》
姚 燧“西风吹起鲈鱼兴”(《醉高歌﹡感怀》),
贯云石“战西风几点宾鸿至,感起我南朝千古伤心事。”(《塞鸿秋﹡代人作》)
赵显宏“青箬笠西风渡口,绿蓑衣暮雨沧州”(《满庭芳﹡牧》)、
张养浩“西风渡头,斜阳岸口,不禁诗愁”(《普天乐﹡平沙落雁》)
王元鼎“夕阳楼上望长安,洒西风泪眼”(《正宫·醉太平·花飞时雨残》)
周文质“西风征雁远,湘水锦鳞无,吁,谁寄断肠书?”(《寨儿令·鸾枕孤》)
李志远“慨西风壮志阑珊,莫泣途穷,便可身闲”(《折桂令·读史》)
吴西逸“长江万里归帆,西风极度阳关”(《天净沙·闲题》[越调] )
吕继民“雨髻烟鬟,倚西风十二阑”(双调·殿前欢·大都西山)
吕止庵“西风黄叶希,南楼北雁飞”(仙吕·后庭花)
卢 挚 “散西风满天秋意”(【双调】沉醉东风)
孙周卿 “西风篱菊灿秋花,落日枫林噪晚鸦。”(水仙子-山居自乐)
徐再思“斜阳万点昏鸦,西风两岸芦花”《天净沙·秋江夜泊》
王举之“芦花被西风向梦,玉楼才夜月云空” (【中吕】红绣鞋·秋日湖上)
赵孟覜“西风一披拂,草木失华滋。”(咏怀六首)
赵孟覜“西风林木净,落日沙水明。”(桐庐道中)
赵孟覜“炎暑尚尔炽,西风犹未秋。”(送谢伯琰﹡太史院都事)
赵孟覜“烟花楼阁西风里,锦绣湖山落照中。”(和姚子敬秋怀五首)
赵孟覜“绿发刘伶缘醉死,往寻荒塚酹西风。”(金陵雨花台遂至故人刘叔亮墓 )
赵孟覜“木落江南天地秋,西风吹子过东州。”(送王子庆诏檄浙东收郡县图籍)
......
总之元代文人非常复杂的,如同当下的文人们一样复杂。严格的讲今天的文人远不如元朝。起码元代文人有言论自由,没有文字狱。元代文人,正如尹占华先生所评论的:“元代文人既有较强的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意识,又迫切希望重新回到仕途功名的彀中去;既有对旧道德旧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又希望伦理纲常得以重振;既要开心纵欲,又痛惜道德风尚的堕落。他们是既清高又世俗,既旷达又执着,既任性又顺从,既享乐又忧患。这种特殊的心态归根结底是在元蒙统治之下大多数汉族文人因失去了晋身之阶而引起的思想动荡所造成的。”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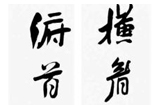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