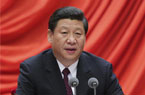元朝是蒙古統治者所建立的一個王朝。元代少數民族入駐中原為政的特殊性,其政治、宗教、經濟、文化、藝術等各方面發生深刻變化,也使得文人知識分子階層發生嚴重分化。一部分文人受到推薦和賞識,積極參與政治而官居高位﹔一部分文人由於生存所迫而入仕為官,但卻迫於正統儒家性情的糾結而折磨半生﹔一部分文人雖亦熱衷於仕宦,卻時運不濟而沉淪下僚,終生無望出頭之日﹔一部分文人則迫於世俗壓力或自覺放棄了仕途追求,或隱山野,或隱市井,成為社會邊緣人士﹔還有一部分文人經營商業,舉辦雅集詩會來聚集和收留散野文人,成為商圈歌館應景﹔還有一部分文人逼迫加入手工行業,亦文,亦畫,亦工,創造今天所見不朽的文物藝術品。盡管有上述亦有區別,但是元代文人的思想傾向本質上多有亦同,沉淪感和危機感並存,自卑感和使命感碰撞。
元代文人的情懷大體上上傷感的,從元詩、元詞、元曲、散曲、雜劇、南戲等諸多作品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他們的作品要麼抒發了對社會底層的同情,要麼表達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慨,或者表達對正統文化的眷戀和回歸。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用“肅殺的‘西風’來表達他們的“淒涼”和“惆悵”。“ 西風”一詞唐代文人多用,宋代文人也多用,多以借“西風”來表達“孤苦”和“飄逝”的心境。當然,元代文人筆下的“西風”不僅僅於此,也趨於多樣的情懷和表達,元代文人用“西風”二詞最為多,好像與元朝文人結下了不解之緣。最著名的當屬元代文人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曲“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了。也許通過對元代文人多用“西風”的詞句,可以窺探那些隱含內心深處的諸多情懷。比如:
馬致遠“古道西風瘦馬”(《天淨沙﹡秋思》
姚 燧“西風吹起鱸魚興”(《醉高歌﹡感懷》),
貫雲石“戰西風幾點賓鴻至,感起我南朝千古傷心事。”(《塞鴻秋﹡代人作》)
趙顯宏“青箬笠西風渡口,綠蓑衣暮雨滄州”(《滿庭芳﹡牧》)、
張養浩“西風渡頭,斜陽岸口,不禁詩愁”(《普天樂﹡平沙落雁》)
王元鼎“夕陽樓上望長安,洒西風淚眼”(《正宮·醉太平·花飛時雨殘》)
周文質“西風征雁遠,湘水錦鱗無,吁,誰寄斷腸書?”(《寨兒令·鸞枕孤》)
李志遠“慨西風壯志闌珊,莫泣途窮,便可身閑”(《折桂令·讀史》)
吳西逸“長江萬裡歸帆,西風極度陽關”(《天淨沙·閑題》[越調] )
呂繼民“雨髻煙鬟,倚西風十二闌”(雙調·殿前歡·大都西山)
呂止庵“西風黃葉希,南樓北雁飛”(仙呂·后庭花)
盧 摯 “散西風滿天秋意”(【雙調】沉醉東風)
孫周卿 “西風籬菊燦秋花,落日楓林噪晚鴉。”(水仙子-山居自樂)
徐再思“斜陽萬點昏鴉,西風兩岸蘆花”《天淨沙·秋江夜泊》
王舉之“蘆花被西風向夢,玉樓才夜月雲空” (【中呂】紅繡鞋·秋日湖上)
趙孟覜“西風一披拂,草木失華滋。”(詠懷六首)
趙孟覜“西風林木淨,落日沙水明。”(桐廬道中)
趙孟覜“炎暑尚爾熾,西風猶未秋。”(送謝伯琰﹡太史院都事)
趙孟覜“煙花樓閣西風裡,錦繡湖山落照中。”(和姚子敬秋懷五首)
趙孟覜“綠發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塚酹西風。”(金陵雨花台遂至故人劉叔亮墓 )
趙孟覜“木落江南天地秋,西風吹子過東州。”(送王子慶詔檄浙東收郡縣圖籍)
......
總之元代文人非常復雜的,如同當下的文人們一樣復雜。嚴格的講今天的文人遠不如元朝。起碼元代文人有言論自由,沒有文字獄。元代文人,正如尹佔華先生所評論的:“元代文人既有較強的與統治者不合作的意識,又迫切希望重新回到仕途功名的彀中去﹔既有對舊道德舊傳統的反思與批判,又希望倫理綱常得以重振﹔既要開心縱欲,又痛惜道德風尚的墮落。他們是既清高又世俗,既曠達又執著,既任性又順從,既享樂又憂患。這種特殊的心態歸根結底是在元蒙統治之下大多數漢族文人因失去了晉身之階而引起的思想動蕩所造成的。”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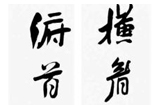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