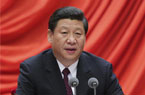歷史上的供用器與官窯
目前已發現最早的供用器,當屬六朝建鄴都城1983年南京出土的孫吳晚期為宮廷燒造的釉下彩瓷(圖1),可能是浙江某個地方窯廠所為,具體產地及用途尚待考証。已知有唐代邢窯“盈”字款,宋代“定州官窯”、“潤州官窯”、“供御”等實物款識資料出土,其應為唐、宋官府經濟的一部分,是受命燒造的地方官辦窯廠生產,大概相當於現在縣級國有企業的隸屬關。
據清涼寺汝窯出土的殘片顯示,該窯廠生產從北宋初年一直延續到金元時期。北宋晚期崇寧、大觀二十余年間生產的天青釉汝瓷,有關於“供御揀退,方許出賣”(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的記載,說明民間擁有、使用汝瓷的落選品是合法的,受命燒造青瓷的汝州具有“地方官窯”的要素:產品有條件地允許在市場流通。它們與金代的“尚食局”款定窯瓷(圖2)及優質的鈞窯瓷(圖3),均應屬於各自地方官府窯廠的“供用器”之類。其中圖2並不比同時期定窯無款瓷器的質量更好,圖3卻更像受命燒造的精品。
湖田窯址出土的標本中曾有宋“迪功郎浮梁縣丞臣張昂措置造”銘文(李放《張昂監陶小考》),卻未見帶本年款識的“供用器”。元“改宋監鎮官為提領,至泰定后又以本路總管監陶”(清·藍浦《景德鎮陶錄》卷五)。常見有“樞府”、“太禧”款識的“供用器”中:印有“樞府”字樣的多不及“福祿”的質量高,與普通卵白釉器差異不大,疑為元代監陶官玩忽職守,或為“供用器”允許流通的基本性質所致。1994年在景德鎮明初土層下方發現“監工浮梁縣丞趙萬初”疑為元代的褐彩銘文瓦,明初時理應沿襲元代由地方官員主持受命燒造“供用器”之“有命則供,否則止”的舊制。
明御器廠之淵源是北宋汴京官窯(待考)、汝官窯及南宋修內司官窯。從杭州修內司和郊壇下的窯址發掘情況中看出,對落選瓷器採取有意打碎后集中填埋,具有絕對的專用性質。但其經使用后的殘片在杭州市內呈分散性出土,意味著當時的落選品也可能允許流通。無論是汝窯、南宋官窯還是元、明初官窯,均不能說是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御窯,說它們是“供用器”或明代“御器廠”的搖籃似更妥。
明“供用器”與御器廠
中國封建制度的歷史有一些規律性的現象,從唐繼隋制以“去奢省弗、輕徭薄賦、選用廉吏”開始,每一個皇朝之初都對此國策格外青睞,自稱大漢子民的朱元璋當然也不例外。洪武二年,明太祖對身邊的大臣強調:“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思耕夫之苦”(《明太祖實錄》卷四十二)。曾托缽流浪的皇帝面對戰爭創傷、百廢待興的現實與自己建立一個理想小農社會的憧憬,必然會節儉勤政,以身垂范。洪武元年朱元璋便下達《諭隱逸詔》:“今天下甫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皇明本紀》)。受儒家傳統“敬宗法祖”思想的影響,朱元璋在建朝之初便詔命燒造以禮祭器為主的宮廷用瓷,即所謂:“洪武二年,設廠於鎮之珠山麓,製陶供上,方稱官瓷,以別民窯”。開始可能順便燒造日用瓷,但數量不會太多,質量亦不會過於苛求。洪武二年之設“廠”應為“供用器”之廠,絕非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御器廠。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燒造供用器皿等物,須要定奪制樣,計算人工物料。如果數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窯興工,或是數少,行移饒、處等府燒造”(萬曆版《大明會典》卷一百九十四,陶器條)。這裡在明確提出“供用器”的同時,也明示了燒造地點、方式及從簡的原則。據筆者近十年來收集的資料顯示:“供用器”最顯著的特征體現在表面上,由於修胎較認真而使釉面平滑,大部分雙面紋飾,繪畫流暢卻欠工整(圖4—6),其內在的瓷胎與同時期的民窯普通瓷沒有顯著變化,甚至有的還稍顯粗糙。由於缺少嚴格的篩選程序,底足時常可見一些不同程度的沾沙痕跡(圖7—9)。北京出土的龍泉窯供用器的瓷胎亦與龍泉窯的優質瓷難以明確區分。值得關注的是,自明代開始,黃釉成為皇家壟斷的日用瓷(圖4)。自從景德鎮、南京發現后,在北京也時有所見,它們往往與永宣官窯殘片出土於同一原生垃圾層中,其器底及足牆較厚,砂底,在素胎上直接施黃釉,可能與洪武有關?是否為永樂早期,尚待實証。《尚書》中五行說認為黃色代表“土”,土乃萬物之本,皇上乃萬民之本。黃釉很可能是由明初的禮祭(祭地使用黃色,祭祀的方位裡“中”亦為黃色)器進而演變為以自我權力為中心的后代皇帝的專用瓷。
自1984年以來,北京第四中學院內及南側發現大量所謂“洪武”釉裡紅、青花瓷片(圖10)。均為未曾使用而有意砸碎填埋,其中伴有龍泉窯瓷出土,但比例較少(圖11)。據說此地原為宮廷庫房所在地(原燕王府,現在中南海一帶,即使是燕王府也不可能有如此巨量的庫存),既然是“宮廷庫房”,理所當然它們應為永樂早期器物。況且,北京各王府及周邊地區也經常出土所謂的“洪武”青花釉裡紅瓷片。因而,洪武至永樂早期的“供用器”有待一步研究。
在朱棣奪權之初,永樂元年(1403年)便改北平為順天府稱北京,原北平行都司改稱大寧都司移至保定。永樂五年(1407年)開始建造北京皇宮,至永樂十八年(1420年)正式遷都。北京出土永樂早期的釉裡紅、青花瓷理應在此13年間燒造。永樂遷都后,南京仍作為留都存在,不可能把南京的瓷器全部解運北京。況且,南京皇宮曾毀於戰火,繼續用侄子建文帝的舊物更是有悖常理。即使有部分瓷器進京,絕大多數也應為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所燒,這正是朱棣已攻佔南京的1402年,亦為永樂早期瓷。發色較好的進口鈷料,可能在鄭和下西洋以后的1407年、1411年、1415年、1419年中的某一次帶回,從而徹底改變了像元代創燒時所謂“延祐型”青花的灰藍面貌。此后,北京庫存(北京第四中學院內及南側)這批“紅不紅、藍不藍”的永樂供用器之歸宿便可想而知了。目前所公認的“洪武”青花、釉裡紅極少出現在南京遺址和有關文獻及洪武時期的墓葬中,明初墓葬出土的青花瓷目前一般也認為是元代,部分有可能為洪武,有待進一步發掘考証。
經在南京實地了解:近十幾年來出土的瓷片中“洪武”白瓷多有出土,而青花、釉裡紅卻極為少見,出土量遠遜於北京市區,這足以說明洪武期間皇宮內極少或根本未曾使用過,是否為宗教祭器或外銷瓷尚待討論。至少,北京出土的所謂洪武青花、釉裡紅絕大多數應為永樂早期。上海博物館藏洪武釉裡紅雲龍紋龍首環耳瓶與朱棣賜給武當山的銅質龍首環耳瓶相似,亦不排除永樂早期的可能。
“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內官張善伏誅。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上命斬於都市,梟首以殉”(《明實錄·宣宗實錄》卷三十四)﹔“洪熙間,少監張善始祀佑陶之神,建廟廠內”(《景德鎮陶錄》卷八)。據以上記載,似乎“御窯廠”是在洪熙(1425年)之前便正式開工——名副其實的壟斷性中央直屬企業究竟是始自永樂白釉梅瓶“內府”款,還是始自永樂青花壓手杯“永樂年製”款?或許這將成為一個曠日持久的謎。僅從景德鎮出土大量永樂晚期的瓷器上看,似應源於永樂晚期。無論如何,明“御器廠”是朱棣在奪權之后確立,從而使“君為臣綱”又增加了“飯碗”這一新內容。這雖然會使“一居一處,吃穿用度”十分儉點的明太祖在九泉之下無可奈何,卻給景德鎮陶瓷史增添了輝煌的一頁,並為官窯日后一枝獨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明洪武三十五年,始燒造歲解。宣德中,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統初罷,天順丁丑,仍委中官燒造。正德初,置御窯廠,專管御器。嘉靖九年,革中官,以饒州府佐管理。四十四年設通判駐廠燒造,尋罷。隆慶六年,復於各府選員管理。萬曆十年,以饒州府督捕通判駐鎮兼理燒造”(《江西通志稿·陶瓷》)。洪武三十五年,朱棣曾詔命燒造瓷器,似在解南京宮中的燃眉之急。崇禎十年《關中五老公碑》中記:“我太祖皇改陶廠為御器廠”﹔明人詹珊在《重建敕封萬碩師主佑陶廟碑記》中記:“我朝洪武末始設御器廠,督以中官。洪熙間,少監張善始祀佑陶之神。”上述無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在天下初定時便匆忙設“御器廠”之說均顯牽強,充其量是在元“供用器”的基礎上繼續燒造,即洪武二年“解京供用,有御廠一所,官窯二十座”(《江西省大志·陶書》)。洪武末設御器廠,隻不過是“督以中官”,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御器廠”應建在永樂晚期。
北京出土相當數量的“空白期”優質無款器,部分應為正統至天順時期“委中官”所造供用器或供御瓷(圖12—15)。自嘉靖九年“革中官”之后,從粗精不一的嘉靖、隆慶、萬曆等年款的官窯器上,不難發現它們又回到了明初“供用器”的起點上。“隆慶五年春,蒙撫院議行將存留器皿委官查解折俸。節經建議發賣,或兌民窯。”從此,御器廠瓷器曾一度不得流通的禁錮正式消失於無形。“萬曆初,內侍潘相監陶務,遂撤回京,終明之世,中官弗遣”。由於明晚期“供用器”有缺乏監督的特點,評價當時瓷器的款識、紋飾已退居其次,它們本身的質量及存世量成為判斷其價值的主要標准。就是說封建社會的“供用器”與“供用人”一樣,通常是選拔而來,卻未必都是當時出類拔萃的。
瓷器,尤其是引領時尚的官窯瓷器是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相對粗糙的明晚期“供用器”反饋出了國力衰敗的信息: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神宗遺詔:“一切榷稅並新造、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實出於內憂外患之無奈。換代而不換飯碗,令天啟、崇禎皇帝十分尷尬,偶然也會抗旨偷燒(圖16),由於不夠“光明正大”,無論是款識還是製作都欠精致,“供用器”的特征暴露無遺。但其流暢的宋元刀法之茶花紋飾,在明官窯(僅在永樂時期偶爾使用)中卻別有洞天,頗具歷史、學術、藝術價值。
清“供用器”與御窯廠
據《江西通志稿·陶瓷》記載:“國朝建廠造陶,始於順治十一年至十六年。康熙十年,部行巡撫,委州縣官監造祭器。”由此可見,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十年所燒瓷器之面目不甚明了。北京出土有無款黃釉碗(圖17)及同類器白、綠、深淺茄皮紫、醬釉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無款黃釉提梁壺,是否均為這一時期燒造,尚待進一步考証。自1654-1680年間,斷續燒造供用器當為清御窯廠的恢復期。相對規范的御窯廠是在平定“三藩”之后內務府徐廷弼、工部臧應選督造的所謂“臧窯” (1680-1686年)開始(圖18)。1705年至1712年由郎廷極主持的御窯廠務俗稱“郎窯”。1720年至1725年負責督辦御窯瓷之人是安尚義,“所燒造瓷器盡行載到揚州轉送進京”(《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這批瓷器的形制、款識、類別尚不明確,質量較好的青花礬紅雲龍紋碗出現在康熙晚期(圖19),可能與之有關。常說堅致的“糯米胎”出現在康熙中期之后,它是清御窯廠走向成熟的象征。1727年即由著名的唐英督陶后,清御窯廠的燒造幾乎從未間斷,其“供用器”允許流通的性質亦從未改變。
北京十年來出土的供用器“大清順治年製”雙圈欄款青花器較多(圖20),它們從紋飾、青花發色及款識的書法風格均與康熙早期的供用器難分伯仲。康熙早期的某些高質量堂名款、無款、仿前朝款、花款器與同時期的供用器的質量不相上下。目前僅見的大清順治年製雙方欄白釉折腰盤(圖21),從繪畫到製作均無驚人之處,彰顯出供用器的隨意。據《清宮檔案》記載:“乾隆二年變價(庫貯)康熙年款圓琢器一百一十一、七百六十三件﹔乾隆二十三年變價(庫貯)康熙無款琢器五千五百二十三件。”這除了提示我們康熙早期的“供用”瓷器部分是“無款琢器”外,“變價”也給之所以北京皇城內外眾多地區出土大量似官非官的“大清康熙年製”款和無款器提供了明確的詮釋。另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九冊:“臣查十九年燒造瓷器至二十五年工竣已逾五載之久,而燒成共得十五萬兩千余件,動用匯省錢糧一萬零三百余兩。”較低廉的造價使大部分康熙早期的瓷器無法保証質量,自然面臨被淘汰的命運,隻不過這些瓷器的變價庫貯器的處理方式與明永樂時的一碎了之大相徑庭,而做出這一明智選擇的是乾隆帝,出主意的卻是唐英。現有雍、乾時期的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八年二月二十日《請定次色瓷器變價之例以杜民窯冒濫折》為証:“從前監造之品,以此項瓷器向無解交之例,隨散儲廠署,聽人匠使用,破損遺失,改燒成之器皿與原造之坯胎,所有數目俱無從查核……隨呈商總管年希堯,將此次色腳貨,按年酌估價值,造成黃冊,於每年大運之時呈進,交貯內府。有可以變價者即在京變價,有可供賞賜即留備賞用……今於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接到養心殿造辦處來文,內有供奉本年六月二十三日諭旨:嗣后腳貨不必來京,即在本處變價……俟核復到日聽商民人等之便,有願領銷者,許其隨處變價。”乾隆七年(1742年)以后,落選“御窯廠”的瓷器不再送京,在當地變價出售(黃釉瓷器除外),這使乾隆以后北京出土的官窯“次色腳貨”極少,大概全部在當地“變價出售”,流散各地。據估計,落選瓷“次色腳貨”的件數可能比正品還要多,而落選瓷的“允許流通”又回到了明初和自明嘉靖以來“供用器”的原始起點上。
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始,御窯廠復歸地方管理:“雍正六年復奉燒造,遣內務府官駐廠協理,以榷淮關使遙管廠事,政善工勤,陶器盛備。乾隆初,協理仍內務人員。八年,改屬九江關使總管,其內務協理如故。五十一年,裁去駐廠協理官,命榷九江關使總理、歲巡視,以駐鎮饒州同知、景德巡檢司共監造督運”(《景德鎮陶錄》卷二)。顯然,由於國家財力日漸式微,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后,“內官”監陶的歷史又告一段落。恰似“三春去后諸芳盡”,隨后雖經歷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時期,但“供用器”每況日下卻是不爭的事實。
據嘉慶二十年(1815年)藍浦撰:“然今則廠器盡搭燒民窯,照數給值,無役派賠累也”(《景德鎮陶錄》卷十)。一語道破了由於經濟陷入困境而“官搭民燒”是恐“賠累”的天機。嘉慶在位二十五年間,從早期楚地白蓮教起義到晚期1813年山東、河南天理教起義從未中斷。“官搭民燒”重蹈了嘉靖九年之后的復轍,高質量瓷器極少見。有趣的是明、清官窯“官搭民燒”瓷器以后,王朝所能夠維持的時間都是百年左右,這一歷史巧合之外的玄機發人深省。
吳宗茲《江西通志稿陶瓷》篇中記:“自咸豐五年,粵賊陷鎮,廠遭焚毀。同治五年,署監督蔡錦青就舊址重建堂舍。”就是說從1855年至1866年期間,御窯廠處於停燒狀態,咸豐和同治的供用器同樣僅燒造了五年,存世量較其他時期更少,想必是情理之中。“光緒末年,江西巡檢會同督臣魏光燾摺奏,請開辦景德鎮瓷器公司,派員經理,以振工藝,保利權之舉”(《江西通志稿》陶瓷)。督臣重新現身景德鎮,促使光緒期間的官窯瓷器出現回光返照。然而,在西方炮艦洞開國門之后,官方才意識到振興瓷器貿易的緊迫性,惜為時晚矣!
由至尊皇權衍生出的明清官窯,終於都以極不光彩的形式退出了歷史舞台。明“御器廠”和清“御窯廠”殊途同歸,皆無法避免地伴隨“供用器”而始終。英國達維德基金會收藏有元未明初“內府供用”款瀝粉堆塑孔雀綠釉罐(圖22),之所以又提出官窯“供用器”的概念,是由於它具備官民同享即“落選品”可以流通的基本特征,元明清官窯(除明永樂至正德以外)絕大部分都屬於這一范疇。同樣是官窯的“供用器”,從質量上說它們粗精不一,有的不如民窯精品﹔就數量而言,它們相應成倍增加,市場價值也就大打折扣。歷代的“供用器”均粗精不一,唯有明永樂晚期至正德由於皇家對官窯異乎尋常的壟斷,決定了其產品的相對稀有,而正因為稀有才使它們成為學術研究及市場最為關注的焦點。
官窯瓷器品質的優劣,在直接體現出當時生產技術最高水准的同時也反映出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及審美的發展狀態。進一步探索它的來龍去脈,可以明確看出封建王朝的起落與官窯瓷器的興衰,恰在同一拋物線上,而它們起落的重要轉折點,尚有待新的發現和探索。無奈才疏學淺,不揣冒昧,僅此置之高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