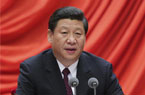道家、道教與嘉靖皇帝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關於“道”的學說為中心的學術流派,它經歷了黃老、魏晉玄學和神仙道教。與儒家人文主義的價值不同,道家曾在中國歷史上對科學技術發展產生過決定性影響。同時,它作為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哲學體系,構筑了第一個嚴格意義的形上學。以正治國的政治、法本於道的法律、少私寡欲的倫理、逍遙世界的審美思想,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進程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道教是道家的支流和變種。它淵源於古代巫術,后以秦漢時神仙巫術和黃老學派的道家思想為主。以東漢張陵五斗米道為端,經歷了趨炎附勢的魏晉道教,政教合一的隋唐道教及“三教合一”的宋元道教。歷代道教均奉老子為教主,尊老子為“太上老君”。因而老子的思想逐漸被引向修道養生,道也成為有意志能懲惡揚善的終極信仰,這使道家向宗教方面轉型成為必然,道家思想也就借助道教的形式得以流傳。
中國南方巫祝文化的母體孕育了道教。據陳寅恪的研究:“道教最早誕生於東南濱海越人區域,以后在巴蜀發展,它主要反應了中國人的文化氣質。它塑造了一個龐大的神靈世界,鬼神之類不下數千。”因而,中國南方人比北方人更熱衷於“造神”。戰國時期越王被吳王挫敗后,國策的第一項便是“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自東漢以來,佛教也入鄉隨俗,“福”成為佛、道共同追求的目標。道教“八仙”人物首先出現在中國元代南方龍泉窯瓷器上,便有著上述歷史原因。明代生活在湖廣安陸(今湖北鐘祥縣)的朱厚熜,正處在與“巴蜀”毗鄰的道教文化氛圍裡,其父興王與當地道士純一交往甚密,嘉靖帝自幼耳濡目染篤信道教可謂根深蒂固。
元太祖成吉思汗重用賣身投靠的丘處機,曾使“全真”教盛極一時。朱元璋逐鹿江南時也利用道人周顛仙、鐵冠子為其編造神話以蠱惑人心。洪武元年朱元璋便立玄道院,封張正常為“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正二品,世襲。朱棣在“靖難之變”時,依法炮製,利用袁珙、金忠等道士製造“名正言順”的輿論。大功告成后,在武當山大興土木為道教盡其所能。道教自宋元以來基本上以“三教合一”為原則,儒、釋、道三者融合,彼此影響共同發展。然而“三教合一”本身已經說明它們自身均缺乏嚴密一貫的宗教思想體系。尤其是道教,由於思想枯竭更是身不由己而趨炎附勢,給人們的印象往往隻剩下煉丹、符?之類,這使它更能體現出“皇家文化”的附庸性及在政治斗爭和戰爭時期的實用性。唯嘉靖時期是一個例外,朱厚熜使道教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反映道家思想、道教主題的流行紋飾也充分表現在景德鎮瓷器紋飾上,其在思想、色彩、形制上都獨樹一幟。
朱厚熜初政時勵精圖治,清除武宗弊政﹔限制宦官逐權內閣﹔革除冗官﹔清理庄田並躬行節儉。正所謂“求治銳甚”(《明史》卷一百九十四),其貌似一隻落在三山之顛的鯤鵬,顯然與以往道教“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供仙人居住的神山”(《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單獨的表達方式截然不同,頗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自我陶醉之感。庄子曾用“鯤鵬”象征自由的審美境界,朱厚熜藉此來表達自己執政的理想。而正是由於鯤(魚)鵬(鳥)之變,才引申出了“天光雲影”。西晉著名玄學家裴頠曾為針砭時弊作了《崇有論》一文,提出“濟有者皆有也”的論題,即每個事物的存在必然與其他相關事物共存,不是因為無才有,而是因為有才有。就像有了天光才出現雲影,朱厚熜有了作皇帝的契機,才有了他凌駕於仙山之上的可能,才有了道教的繁榮,才有了景德鎮瓷器上豐富的有關老庄、玄學思想的紋飾及令人眼花繚亂的彩瓷。
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用道家的思想解釋儒家的義理以鍛造自己的理論。由於道教經典從玄學中借用過來,所以嘉靖瓷器紋飾中往往也不乏儒家崇尚的鬆竹梅。“竹林七賢”是正始玄學之后七位玄學名士的總稱(《世說新語》)。兩晉南北朝時,儒家思想不為統治者重視,許多沒落士大夫便從老庄學說中尋找寄托,崇虛無,尚清淡,雖表面上放達,但骨子裡卻仍想入世。阮籍曾有詩雲:“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放蕩不羈的阮籍為不與當朝太師司馬氏合作,竟一連六十天大醉不醒。“大明嘉靖年造”款彈琴圖,無論它畫的是嵇康還是阮籍,都暗合了朱厚熜“更典改制”時,連遭儒臣們阻撓的內心痛楚和對於迫切尋找“知音”的渴望。另外一幅“彈琴圖”中有兩個人,似稽、阮在一起談玄論道的情景。嵇康也曾有詩雲:“回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與阮籍借酒澆愁不同,嵇康是靠養性服食來超脫,他不僅服“散”,而且還作了《養生論》一文:“留丹石菌,紫芝黃精,皆眾靈含英,獨發其生。”可以“煉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嘉靖帝對此心領神會,命官員赴“五岳”等地廣征靈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禮部報天下進獻瑞芝達一千八百六十之多(《明史》卷十八)。“王者仁慈則靈草生”(《太平御覽》)。靈芝作為祥瑞之物被歷代君王百姓所推崇,明代以來靈芝卷草紋時有所見,而嘉靖及其后靈芝紋更是廣為流行。可能朱厚熜在“宮婢之變”中奇跡般的“康寧”都以為是靈芝的功勞,隨即“五岳山人”款也應運而生。
道教與道家的相通之處主要在於形上道論,尤其是在道體論及養生論上。道教將養生看成是長生不死的實施手段之一,為修得仙體,常以仙桃來傳達對於長壽的願望。朱厚熜根據《漢武故事》(托名班固)請東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一個追求身心自由的“大隱”替他到西王母的瑤池中偷“仙桃”,對后世的瓷器紋飾影響深遠。庄子肯定了變易的普遍性,認為天下萬物莫不處於無止無息的變化過程中:“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嘉靖之前瓷器紋飾中的仙鶴多佇立狀,而自朱厚熜始,仙鶴均呈飛翔狀,充分體現了“無時而不移”的庄子理念。萬曆時的仙鶴成為了“壽星”的坐騎亦不失為創新之舉。翱翔的仙鶴從此成為景德鎮瓷器紋飾最常見圖案之一。耐人尋味的是:在明代官員服飾規范中“文官一品仙鶴……武官一品、二品獅子”(《明史·輿服志》)。表面上看對道(鶴)佛(獅)不偏不倚,實際上明顯側重於象征佛教的武官。因為,誰都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道教以自己的方式回答道家的命題,演繹道家的思維,實踐道家的理念,弘揚道家的精神。老子曾有“上善若水”之論,而庄子的理想是做條自由自在的水中之魚,自得其樂。嘉靖帝“舉世混濁唯我獨清,世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情結,使嘉靖時期官窯瓷器上的魚藻紋成為主流紋飾之一,而此前隻在民窯較常見,嘉靖晚期官窯瓷器多見不加邊欄的款式,似有進一步追求“逍遙”的意味。表面上它們符合道家“逍遙世界”的審美思想,實際朱厚熜更想突出的是庄子有關“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的論斷,以克服自己“小宗”的自卑感。因為根據宗法社會大、小宗的規定:“皇嫡長子為大宗,為帝統,其他皇子為小宗,為旁支,分封為王。若旁支入繼正統,必須立為大宗之后,成為大宗之子,改稱親生父母為伯叔父母,即:為人后者為之子。”顯然,朱厚熜追尊興獻王(生父)為皇帝是越禮犯制之舉,他“應時而變”在與大臣們激烈爭論了二十年之后終於以“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為由,遂了讓自己父母“稱宗附廟”的心願。
青花魚紋“曲蜜華房 上元甲子”款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標准器。“上元”可能是指“金?”而言,據“靈寶玉鑒”稱:“大齋之格有三:一曰上元金?,二曰中元玉?,三曰下元黃?”。它應為道教大齋時上元“降真致神”之用器。它與佛教的齋戒、伊斯蘭教的齋月一起,使文人的書“齋”流露出得“道” 的快感。齋醮的盛行直接影響明末清初以“齋”為款的流行,康熙帝就曾把自己的居所稱為“無逸齋”。朱厚熜把原始祭祀用之“神魚”顛倒成為“魚神”之后,“魚”被徹底融入了本土道教文化中,成為“道教”的概念之神,從此更加頻繁的出現在中國各種民俗藝術門類上。景德鎮瓷器用它作為主題紋飾更是屢見不鮮,其中“雅”字款的魚紋具有儒家特色:“雅”即“正”,正則不違古道,言出於《詩》,行合於《禮》,樂比於《韶》,便是雅(弘治,正德時民窯瓷器的“正”字款,是否可能是儒家之“正”,或道家以正治國之“正”,或仿前朝正統款之“正”,值得進一步探討)。然而,好景不長,“魚龍變化”,最終再度成龍者乃是大清之“魚神”。
漢高祖劉邦的寵臣黃老學派的代表人物陸賈,提出以“仁義道德”為“道基”反對獨斷主義。提倡“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因事而權行。”道家這一獨辟蹊徑的觀念,迎合了朱厚熜挑“祖制”毛病的初衷。他把孔子“文宣王”的稱號改成“聖先師”,以示“書不必起仲尼之門”。祭祀是歷代王朝的頭等大事:“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記》祭統)。明代“天地合祀”是自朱元璋建國以來堅持使用的方式。然而“藥不必出扁鵲之方”,“朕以藩服,仰借天命,入奉祖宗大統”(《明世宗實錄》卷九十),朱厚熜以周朝以前便有“冬至祀於南郊之圓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為由,公然改變祖制“之方”,實施了天地分祀。自1530年開始先后在北京建成了天、地、日、月壇,這促使嘉靖晚期出現了單獨以“地”字為款識的現象(圖48),樹起了一座“天地分祀”的裡程碑。
朱元璋規定:“道士設齋醮,不許拜奏青詞”(《洪武實錄》卷二百零九)。嘉靖帝竟以“青詞”寫的優劣來任免官員,當時人們把寫“青詞”入閣的人稱之為“青詞宰相”。老子曾乘“青牛”西去,道士的衣服稱為“青袍”,因而“青花”瓷興起在恢復傳統文化的明代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朱元璋乃佛家子弟,嘉靖帝卻敢於拆寺廟、燒佛骨肆意妄為,使皇宮內外成為道教的一統天下。可見“因世而權行”的威力(后稱朱厚熜為“世”宗,極為貼切)。宮內禱祀活動頻繁,僅“一齋醮蔬食之弗為錢萬有八千”(《明史》卷八十五)。景德鎮瓷器款識,在弘治前后僅見“湯碗”款(圖49)。而據《江西通志稿》記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曾一次製作“甜白色酒鍾三萬”以供醮壇之用(圖50)。至清康熙“金大醮壇用”款(圖51、52)依然出現在仿嘉靖款的洪流中並演繹出“湯社”款(圖53)。其實這都怪朱元璋,他隻規定“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論”(《明史》卷三),恰沒想到,真正能更典改制並非大臣而是自己無人能約束的宗室子孫。
“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原來是一家”的局面被朱厚熜顛覆之后,他卻沿用了以“蓮花”為主題或輔助紋飾的圖案(圖54—63),因為道家原本便是其中之一,現不過是喧賓奪主而已。嘉靖官窯的“雙蓮花”(圖60、61),除了把佛教剔除,也把“天子”置之度外,隻顯示出道儒兩家,頗有“無為而治”的意味。據《明世宗實錄》卷二中記載:“嘉靖臨御以來,厘革弊政,委任舊臣。凡夫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雖有吹捧之嫌,但依靠儒道這兩朵“蓮花”卻是事實。“朕為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明世宗實錄》卷二百四十七),就連朱厚熜的道號也具有儒家色彩,自封為“伏魔忠孝帝君”(《明史》卷三百零七)。為使其父能稱宗附廟,嘉靖帝經常宣揚“天下之治,孝為先”,把儒家倫理與自己的意願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受此影響,嘉靖期間的“樹下讀書圖”、“平步青雲圖”、“一舉登科圖”、“高官厚祿圖”空前盛行(圖64—67),這意味著對百姓而言依然是“官必起仲尼之門”。“獨蓮”紋可能是嘉靖帝為自己專燒的(圖68—71),在唯我獨尊的盤外壁也學佛教八寶而湊出了道教的八寶。明末清初把獅子滾繡球紋飾中的“繡球”也簡化為“道教八寶”之一的錢紋(圖72)。嘉靖之后,景德鎮瓷器有關儒釋道的紋飾空前混淆,更是不分彼此。
在崇信道教的同時,朱厚熜還喜好祥瑞。祥瑞者,吉祥之兆也。明朝以來官窯中常見的龍鳳、祥雲紋飾,皆由古人對祥瑞的崇拜而發展成為皇家專用的紋飾。據漢代以來的典籍記載便有白燕、白鳥、白雀、白鳩、白虎、白鹿、白熊等,西晉文學家傅玄在《擬天問》中便將“白兔”送入月宮與嫦娥為伴。明宮廷多用白釉瓷,除受佛教影響外,還有祥瑞“白”色的傳統。祥瑞亦來自儒家“天人感應”學說,把自然界的災難和祥瑞看作是天對人的懲罰或獎賞。道教利用祥瑞本來就莫須有,或者是難得一見的自然變異現象討好皇帝。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一月,四川撫臣宋滄獻上當時較為罕見的白兔,謊稱祥瑞。朱厚熜大悅:“茲兔罕有,良由和氣所感,而忠臣賢士攜為王瑞”(《明世宗實錄》卷一百四十四),隨后將白兔獻之太廟,呈於兩宮皇太后之前並接受百官祝賀。因在明代的市民社會裡,江湖文人常用“宅眷皆為撐目兔,舍人總作縮頭龜”來罵人,兔紋則很少使用。正德時白兔紋飾隱於石頭后面(圖73),嘉靖時白兔卻一躍成為石頭前面的主題(圖74)。身價倍增的兔紋,在明末清初仍倍受推崇(圖75-80),天啟前后的“兔款”亦淵源於此。
官窯瓷器紋飾必然體現出皇帝的意志與審美。把龍鳳幽禁於宮牆之內,把黃色釉瓷器作為皇家專用,均始於閉關自守的明代。然而“正面龍”紋的創始者卻是嘉靖帝(圖81),並一直得以延續(圖82-85)。因為朱厚熜是一個敢於追求和直面現實的皇帝:“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有貪暴奸邪者務要指陳實跡糾劾,在外從巡按史糾劾”(《明世宗實錄》卷一)。明人張燧贊譽其為:“至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千年百眼》河北人民出版社)。“正面龍”的形象,恰好表現出朱厚熜不循規蹈矩而神武獨斷的稟賦。標新立異的龍紋,向兩側分開的頭發,顯示出道家郭象(252-312年)“超然心悟,忘形自得”而“獨化玄冥之境”的玄學本體論的觀點。“獨化”(變化)使朱厚熜在偶然得到皇位之后,企圖將改弦易轍的“忘形自得”充分體現在創新的“正面龍”上。另外,輔助紋飾為“陰陽”花瓣的蓮花和主題紋飾極為夸張的花蕊(圖86)此前極少應用於瓷畫(圖87、88),它一方面體現出老子貴“陰柔”的哲思,以陰陽矛盾勢力解釋道的運動辯証法。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道家向秀(227-272年)提出的“自生,自化,各任其性”的主旨。總之,朱厚熜逍遙於宗法之外的理論依據,通過具體的紋飾被充分表達出來。
從嘉靖十一年(1532年)開始,欽安殿內便香火繚繞。尤其在嘉靖晚期的二十四年裡,朱厚熜僅三次朝見群臣。日事齋醮,乞討長壽成為他的主要生活內容。自鬆枝“壽”、靈芝捧“壽”到直書“壽”字(圖89-91),猶如明早期,“福”字蛻變為佛教符號一樣,“壽”字自此也被嵌入道教的靈魂之中,且為后世相習沿用(圖92-96)。1542年(壬寅)十月楊金英等十六名宮女謀殺嘉靖帝未遂,十一月以“宮婢之變”昭告天下:“卒獲康寧”(康寧是中國傳統五福之一)。於是,導致“福壽康寧”款在嘉靖晚期及其后盛行(圖97-101)。因而嘉靖時期的“福壽康寧”款基本上可以判斷以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為上限。嘉靖帝大難不死后,王朝財政開始入不敷出,軍費及宗室生齒日繁,開支浩大。恰如1549年海瑞上疏所言:“吏貪官橫,民不聊生……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老子將“見素抱朴,少私寡欲”看作是無為而治的根本。在老子看來,正是由於權利和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才引起天下紛爭。他告誡人們謹記:“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尤其是作為統治者更應節制自己,才能“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原產中國西北“國色天香”的牡丹花,被國人視為“富貴”的象征(圖102-107)。“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常見於景德鎮瓷器上,嘉靖以后尤為盛行,甚至作為主題並列書於器內底心上(圖108)。它們“斷章取義”於老庄,卻忘記了莫之能守、自遺其咎的教誨。朱厚熜在遺詔中若有所悟:“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明世宗實錄》卷五百五十六)。最終朱厚熜像秦始皇一樣仙逝於“靈丹”,而道教紋飾伴隨道家思想卻在其后的景德鎮瓷器上,真正成就了中國本土文化又一次濫觴。
自東漢以來,道家思想少為封建統治所重,一直處於從屬地位。藩王之子朱厚熜有幸登基,他天生便有追求“自由”、“逍遙”的意識,骨子裡充滿了更典改制,拆廟毀庵,所謂“正前人之舛誤,定萬世之良規”的強烈願望。至於“概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成一朝之作”(《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無非是為鞏固自己的專制地位和滿足個人虛榮而已。然而,景德鎮瓷器在相應反映出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紋飾及宮廷文化底色的同時,也揭開了景德鎮瓷畫史承上啟下的一頁。從此,有關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道教紋飾得以恢復元氣,導致在嘉靖之后和清代民窯的瓷器上,佛教法器“十字杵”紋飾消失於無形。
基督宗教文化后來居上
基督教是世界傳播最廣,信徒最多的宗教。它原是猶太教的一個支派,於公元135年從猶太教分裂出來。然而,它得自希臘哲學(唯心主義)和神學的成分卻多於得自猶太教的歷史、法律及部分道德觀念。基督教文化內在矛盾根源,使其既不能像佛教徒那樣超脫世俗生活,也不能像穆斯林那樣奮勇投入到利害沖突中,頗具“中庸之道”。
中國最早的基督教的教派景教,是在唐貞觀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羅本攜《聖經》來到當時的世界文化中心長安,在唐太宗的默許下得以初步傳播。元統治者把“天主教”稱之為“也裡可溫”教(蒙語意為“有福祿者”),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較高的地位。北京出土較多高質量卵白釉瓷,常印有“福祿”款(圖109),除了受中原文化影響外,可能也為基督教徒所用。約在十三世紀末,方濟會修士孟高維諾奉教皇尼古拉之命來到元大都,據說當時受洗者達六千余人並在幾年后修建了教堂。與此同時另一位西方傳教士安德魯也在泉州修建了教堂。據《元典章》記載:“也裡可溫人氏,素無文藝,亦無武功,系揚州之富豪,市井之編民。”能給外國人上“戶口”,可窺元朝“開放”政策之一斑。
推翻了異族統治的朱元璋把“也裡可溫”視為“異教”,隨元順帝一起被逐出。在其后近兩百年“閉關自守”的日子裡,找不到景德鎮瓷器上有關基督教文化的蛛絲馬跡。第一艘葡萄牙商船從好望角到達廣州是正德八年(1513年),現存裡斯本的繪有葡王曼努埃爾一世(1495-1521年)紋飾的青花執壺,是迄今發現西歐最早的訂燒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抵達澳門:“夷眾殆萬人矣”(《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五十七)。澳門既是葡萄牙人商業活動場所,又是傳播基督教文化的據點。至“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請開海禁”(《東西洋考》)以后,耶穌會修士利瑪竇來華時,天主教幾乎已不復聞於中國。為在中國繼續傳教鳴鑼開道,利瑪竇進京時改易儒服,言談舉止也頗具儒家風范,且“性好施,能緩急”,仿佛“蓋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種釋氏”(《萬曆野獲編》)。按利瑪竇自己的說法:“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望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修居於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焉得為天帝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20世紀40年代,從1595年沉沒的名為“聖奧古斯汀號”的海船上打撈出七十件明萬曆青花瓷,說明當時景德鎮瓷器已遠銷美洲。當時,歐、美洲人已經是商業民族,必然將贏利視為至高無上的目標,他們不遠萬裡留下了傳教士,卻帶走了真正需要的包括瓷器在內的緊俏商品。
北京近十年來出土的景德鎮瓷片當中,所謂“克拉克”瓷如鳳毛麟角,就連“首都”都難尋綜影,可見萬曆時外銷瓷的供不應求之勢。在大批貿易瓷器輸出的影響下,其紋飾自然出現了一些異國情調的圖案。自嘉靖晚期以來的“團螭龍”出現了少量以“右旋”形式的畫法(圖111),由於這不符合中國人自古以來、自右至左的書寫習慣(圖112),其畫面明顯不夠順暢。當中國瓷器主題紋飾獨立存在時,一般都面向左方(圖113、114),這是“字母”文化與“漢字”文化所引申出來的不同的思維方式在紋飾上的必然反映。在頻繁接觸西方理念之后,明末清初的“仕女”(圖115)往往體現出“字母”文化的特征,開始面向右方。
受西方繪畫觀念“寫照如鏡取形”的著名肖像畫家曾鯨(1568-1650年)“每圖一像,烘染數十層”的影響,瓷畫家筆下也出現了“境界雖殊,思致盡同”的紋飾(圖116-120)。從萬曆至清初,從一般瓷器上“分水”畫法的層次逐漸增多的趨勢上,可見中、西交往日漸頻繁之往事。順便說一點,由於文字書寫用筆的不同(西方人用的蘸水筆為不損壞筆尖而倒置),筆筒的使用在西方國家源遠流長,而中國毛筆倒置易使筆根開膠脫落,筆筒隻能放未曾使用的新筆。崇禎以前發現的所謂筆筒,大多只是花插、香筒之類。明末清初,“筆筒”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為時尚的奢侈品,並在其后的數百年裡走入尋常百姓家(圖121)。由於它們缺乏實用性,“筆筒”和“花瓶”難以從用途上區分,可謂時人盲目“向西看”的陳設瓷之一。
由於羅馬教皇嚴禁中國天主教徒敬拜偶像,觸怒了以偶像為生命的儒家官僚。南京禮部侍郎上疏列舉了天主教會的“四大罪狀”,促使朝廷於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頒發了禁教令,迫使西方傳教士回國,史稱“南京教案”。此后,天主教隻好轉入“地下”悄悄發展。為期不久,明崇禎(1628年)至清順治(1644年)的皇帝均對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寵信有加。在天主教恢復的同時,僅1636、1637、1639年荷蘭人便購買優質外銷瓷數十萬件之多。清早期,康熙帝雖然也努力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並重用傳教士,卻終因“教儀”和“曆法”之爭,對湯若望等天主教勢力予以嚴厲打擊。18世紀初,羅馬教皇的特使多羅主教亦被遣送澳門。澳門博物館館藏澳門出土的瓷片中,大多以萬曆晚期至崇禎為主,康熙出口瓷極少見,而北京卻經常出土“出口轉內銷”的康熙瓷(圖122),反映出“天主教”在中國的起落與景德鎮外銷瓷的興衰存在某種微妙的必然聯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隨著清政府海禁的廢止,中西貿易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西方的畫琺琅工藝及製作工匠與“能燒琺琅物件”的廣東工匠一起應詔入宮,參與造辦處的金屬琺琅器製作。在此基礎上瓷胎琺琅彩應運而生。由於琺琅彩色彩豐富、逼真而更接近寫實,頗受時人喜愛,促使以“玻璃白”打底立體感較強的粉彩瓷隨之興盛。粉彩成本相對低廉,視覺效果與琺琅彩相似(圖123),一改以往紅綠彩、五彩的單調(圖124-126),成為清中期至民國主流產品之一。同時期的“廣彩”主要在外銷瓷上大顯身手,受到西方社會的普遍歡迎。
清初與“四王”齊名的畫家吳歷(1632-1718年),曾在澳門有機會接觸西方繪畫作品。他的畫注重明暗、黑白對比,顯然把西洋技法融入其中(圖127)。康熙中期景德鎮瓷器紋飾同樣突破了傳統成法的限制(圖128、129),構圖嚴謹,虛實交錯的紋飾,也傾向於西洋寫實手法。其山水紋飾利用鈷料的濃淡不同,盡可能表現出多色階的效果,頗具“吳歷”風范。明末清初為使“牡丹”的立體感突出,還刻意增加了“雙犄”(圖130)。與此同時,石濤(1636-1710年)提出“筆墨當隨時代”的獨創精神,以深入物理、曲盡物態為手段,達到“物我交融”的境界。他的見解本質上就帶有西方繪畫的理論色彩,是明宗室后裔順應潮流之說。理所當然,景德鎮瓷畫同樣被卷入這一時代的漩渦裡而身不由己。
從教皇發出十字軍東征的號召以來,基督教文化一直把征服東方當作他的歷史使命。然而,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悖離儒家的綱紀倫常,毀傷教化,同時也有“窺伺中華,謀為不軌”之嫌,這使其傳教過程極為艱難。康熙帝一針見血地指出“異端小教之言,如何倒指孔子道理為異端,殊屬悖理。”(《康熙與羅馬使節關文書》第十三件)在政治形態領域傳教受阻的同時,天主教加強了貿易、科技、藝術領域的滲透。郎世寧(Giv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修士,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北京傳教,旋任清宮廷畫家,在他“御用”的中國式西洋畫面上飽含著傳教的苦澀。宮廷畫家焦秉貞(湯若望的高徒)及弟子冷枚(18世紀初),在“同事”郎世寧的影響下,均吸收了一些西洋畫技法。焦秉貞所繪“耕織圖”上有明顯的焦點透視效果。北京故宮藏青花“耕織圖”碗及五彩“耕織圖”棒槌瓶均以焦秉貞“耕織圖”為藍本,可斷定相關紋飾的瓷畫“耕織圖”均以康熙晚期為上限。受其影響,康熙中、晚期的景德鎮瓷器紋飾多趨向於寫實,色調也更加豐富。然而,像基督教傳教失敗一樣,儒家文化特有的韌性使其后的繪畫、瓷畫重蹈覆轍並日顯呆滯。
由於地理上的原因,基督教國家接受景德鎮瓷器的時間較晚,而對其追捧卻遠勝過伊斯蘭教國家—現存歐洲近百萬件的出口瓷便是明証。1717年時,奧古斯都二世為搜集他所喜愛的十二個花瓶,不惜用自己四隊近衛軍換取,足見痴迷之深。古老的東方非但未曾被基督教所征服,恰恰相反,瓷器、絲綢、茶葉、漆器卻征服了歐洲貴族,這是當初“教皇”始料未及的悲哀。但是,西方商業文化的強勢擴張使他們不甘落后,在本地區發現高嶺土之后,德國、英國很快便燒出了耐溫更高的“三元配方”,並逐步實現了機械化生產。乾隆晚期,歐洲諸印度公司的訂單紛紛停止。而經歷了明治維新(1868年)的日本瓷器卻大量出口歐洲。民國時期,日本的外銷瓷也佔據了中國市場的不少份額,景德鎮瓷器的輝煌從此一去不復返。
歷史的迷霧與反思
被皇家統領上千年“三教合一”的中華民族,宗教的重疊現象令人費解卻又順理成章。儒家祭祀大典中把“關帝”、“媽祖”列在其中,而它們本質上屬於巫道文化,實際更接近道教。寺廟中佛、道的神靈也經常一起供奉,使人們心目中菩薩和神靈的形象模糊不清,明代落魄的著名畫家“八大山人”就曾過著亦僧亦道的生活。這種兼容並蓄的現象同樣經常雜陳在景德鎮瓷器紋飾上。所有這些莫名其妙的混淆,實際上都源於被世代沿襲的習慣所風化了的盤根錯節的所謂“宗教”。發人深省的是:清晚期,當中國經濟自給自足被西方商品沖垮的同時,中國人思想上的自我封閉也被西方的“哲學、法律、政治、藝術”觀念所淹沒。然而,他們選擇了西方包括喝湯用的勺子在內的一切,卻唯沒有選擇基督教。雖然中國佛教和西方基督教均把“布施”(無我)擺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但“禁錮者”與“挑戰者”之間的文化鴻溝終難逾越。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此正為中國人缺乏宗教興味且以宗教在西洋亦已過時之故。”
在1500年(弘治-正德)前后,是世界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對各大宗教系統都是同樣公平的。就當時的實力而論,中華帝國、印度莫臥兒王朝和奧斯曼帝國比基督教歐洲更有資格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西方基督教社會內部經歷一系列漫長艱難的宗教、經濟、文化、政治變革,在自己綜合國力遠遠落后的情況下成就了三場(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重大的歷史運動。最終在18世紀完成了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的過渡和工業革命。中國景德鎮瓷器后來被西方創造性的仿製亦可謂工業革命的成果之一。相比之下,在儒家倫理世界的明中期,成化帝非但陶醉在傳統價值體系中,甚至於把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都付之一炬。由來已久的重農抑商,徹底的“閉關自守”是導致景德鎮瓷器生產“大戶”難以為繼的根本原因。當時,這些已經有了品牌意識的製瓷名家與英國農村紡織業具有同樣的歷史機遇,但他們卻無法完成最初的資本積累。從現有資料上看,無論是十五世紀末還是十七世紀末帶字號的“窯主”們均僅維持了幾十年便銷聲匿跡了。景德鎮瓷器由於唯有至尊的“年號”而無知名的“品牌”,隻好任憑封建慣性的牽引而痛失歷史機遇。
自明朝景德鎮青花瓷“片板不許下海”,到如今“藍色資本家”們在海外初試鋒芒,有誰知道,這究竟是亞當出世,還是老子出關呢?無論如何我們從青花瓷紋飾中感到的傷逝遠超過驕傲。儒家學說的主導地位確立於西漢,中國佛教與瓷器的誕生恰都在東漢。從青瓷到青花瓷的轉變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另有玄機?明青花瓷的始作俑者和倡導者究竟是朱元璋?還是朱棣?為什麼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甚至於當下,歷史人物故事頻現於傳媒及瓷畫之上?中國乃至世界近代繪畫是否植根於中國原始民間繪畫,尤其是明早期以前的陶瓷畫土壤裡?還有許多匪夷所思的問題需要解析,決非僅“宗教”所能說清道明的。恰如帕斯捷爾納克所言:“我們無法把握時代的變遷,像我們無法明白草是怎樣一點點枯萎。”在這裡,筆者也僅僅是想昭示草是在怎樣適當的濕度、溫度中慢慢地發芽而已。
長期浸泡在“三教合一”海洋裡的中華民族,從瓷器紋飾上便能品味到那淡淡的咸味。被歷代封建統治者視為思想武器的“儒家”,借助於佛教、道教乃至伊斯蘭教淳風化俗,無論是官、民窯紋飾都具備中華民族的文化屬性。被皇家統領的與“三教”有關的圖案及思想始終是彰顯社會狀態的主流題材,隻不過每個特定時期所涵蓋的范圍與力度有所差異。它們所勾勒出的是一幅既朦朧而又鮮明的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掩卷之余,百感交集。五百年前,以中國紡織業及景德鎮瓷業等其他手工業為契機的發展機遇早已被扼殺在搖籃中。而今我們又站在一個新的起跑線上時,追溯中華民族的封建宗教軌跡,探討它們所反映出有關儒、釋、道的深層次文化內涵,或許能給我們某種啟迪,從而少一些當下的喧囂與浮躁,多一點平靜和怡情,那怕僅僅是一點反思。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