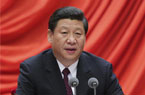縱觀浩如煙海的中國陶瓷史,“瓷片標本”從未像現在這樣倍受青睞。“寧要一片殘破的真實,也不要一件完美的虛假”,正在成為瓷器愛好者的共識。昔日的“垃圾”已成為方興未艾的古文化資源之一。閱讀瓷片可“由一斑窺全豹”,為我們觸摸歷史,追根尋源架起了一座新的橋梁。據悉,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遺址便是根據出土陶片而發掘的﹔1986年上海博物館汪慶正先生偶然發現河南寶豐瓷廠王留現先生在清涼寺搜集的一件汝窯洗,經調研后揭開了汝窯窯址的千古之迷﹔據說,南京博物院館藏洪武白釉瓷碗,首先發現者便是“瓷片一族”﹔明龍泉窯“供御器”的窯址,也是杭州瓷片愛好者通過市場上出現的古瓷片,“順藤摸瓜”而最終找到的﹔西安陶瓷研究者結合本地出土的瓷片,正在探討有關“柴窯”這一古老而又極富新意的話題,一個未知世界的門再次被敲響。
在復之風驟起、造假技藝日臻成熟的今天,瓷片標本更彰顯出其無可替代,甚至無與倫比的“經世致用”性。學術不斷有所突破,藏家練就一雙“慧眼”,瓷片功不可沒。不經意間,瓷片已成為自成體系的新興收藏門類中的一員。目前,瓷片收藏在全國已初步形成規模,許多人都期望辟瓷片為蹊徑,輕鬆走進中國陶瓷歷史的深處,探索其不為人知的奧秘,挖掘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
瓷片的陶瓷史學啟示
在兩千多年“以農為本”的封建統治下,科技發展、手工業生產從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其結果是,中華民族熱衷於在血緣上“尋根問祖”而不屑於在科學技術上“追本溯源”,導致“中國科技史”竟然由外國人書寫的悲哀。中國陶瓷史研究亦不例外,相關文獻少得令人難以置信。最早把中國陶瓷史當作一門科學來梳理研究的,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西方學者布蘭克森(A·D, Brankson)和霍布森(R·L, Hobson)。1938年,首先考察景德鎮湖田窯窯址的是英國的年輕學者白蘭士敦(A·D, Brankston),當時大量的瓷片標本被運至國外。而國人對於瓷器的歷史研究則始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本是學醫的陳萬裡先生開始考察龍泉窯窯址,成為中國陶瓷科學探索的先驅。北京故宮博物院開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全國窯址調查,就是在陳萬裡先生帶領下完成的。1986年8月,馮先銘先生在福建建陽窯考察時撿到一塊宋代“供御”款的瓷片,令其興奮不已。究其官窯最后的形成和發展,便是從全國眾多窯口的優秀“供御”瓷中挑選出來的。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陶瓷研究在各地受到愈來愈多的重視,全國較重要的窯址均有不同程度的科學發掘。2002年經實地考察証實,安徽繁昌窯是中國南方青白瓷的發源地之一,並把中國瓷器使用“二元配方”提前至宋代。事實証明,通過窯址的瓷片來確定存世器的產地,及根據瓷片出土的層位學關系來斷代的方法是不容置疑的:河南鞏義縣白河窯出土的青瓷與洛陽漢魏故城出土的青瓷造型完全一致,為北魏皇室用瓷確定了產地。杭州南宋修內司官窯土層之上出土的哥窯瓷片,說明哥窯是在南宋“內窯”之后質量下降的產物。再者,根據在全國眾多宋墓中,均未見有哥窯瓷器的出土資料的事實,基本可以推定“宋哥窯”應為元代稍晚時期的器物。河南鈞窯窯址出土了刻數字的所謂“宋官鈞”瓷片,同時伴隨其出土的卻有元代才開始使用的“孔雀綠”釉瓷片和與宋代器形不符的其他瓷片,令人疑惑。
無獨有偶,近十多年來,北京出土的此類“官鈞”瓷片幾乎全部來自東、西城區(元明清都城所在地)的明早、中期原始垃圾層,而宣武區(金中都所在地)僅偶有出土,且土層關系不詳。經實地了解,南京尚未見洪武“官鈞”瓷片問世,進一步証實原以為存世稀少的“宋官鈞”陳設瓷極可能是明永樂建都時所造,本書暫定為“永樂”。此外,2006年,浙江省博物館把所藏河南禹縣“八卦洞”出土的“宋官鈞”標本及山西臨汾出土的“元鈞”殘片,送上海博物館熱釋光實驗室進行測定。結果顯示,“元鈞”比“宋官鈞”早八十五年左右。總而言之,過去認為的“宋官鈞”部分陳設瓷器物,應該是元末明初的作品。這些具有顛覆性的科學結論,必將通過出土瓷片的不斷發現而更正各種由主觀臆斷而產生的模式化思維。當然,一種觀念的改變絕非易事,就像我們通常所說的“阿拉伯”數字最早起源於印度,而“阿拉伯”卻早已深入人心,約定俗成。但對專業研究者來說,不能不知其所以然,對陶瓷史而言,許多重要的斷代問題,應隨著新的研究考証的出現而予以修訂。
此外,窯址瓷片的發掘和研究還有助於印証過去的某種猜測。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鞏義白河窯址的發掘中,發現了唐青花瓷片等實物標本,証實了此前普遍認為唐青花的發源地是河南鞏義窯的看法是准確無誤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景德鎮出土了大量沒有傳世器的瓷片,不僅極大豐富了陶瓷史料,開闊了陶瓷愛好者的眼界,同時還証實了從明永樂晚期到正德之前的這段時間是中國陶瓷史上最封閉、最挑剔也是最純粹的“官窯”。
窯址發掘已被空前重視,其出土的瓷片對於確認和修正已有的學術結論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海內外城市古遺址中大量的中國瓷器殘片,其學術價值尤其不可輕視。他們既是陶瓷標本,更是各自城市社會、經濟、地理、民俗、藝術、宗教諸方面文化的歷史掃描器,可以極大地拓展陶瓷研究的視野。資料表明,日本全國有近千處遺址中發現了自宋到清的中國瓷器蹤跡。埃及開羅南郊福斯塔特發現大量的唐三彩、邢窯白瓷碎片,還出土了五代耀州窯“官”字款碗底,証實五代至北宋早期,“官”字款器已有出口,其經營者可能是地方縣級官辦企業,其產品代表了當時最高技術水平,還具有允許任意流通的商品特征,同時,它們也向世人展示了當時耀州窯力圖開辟海外市場貿易的足跡。
北京是有著近千年建都史的古城,遺址內遍布“原生垃圾層”,在夾雜著煤渣、禽獸骨、糞便的私家院內的廁所裡,同樣忠實地記錄了一座城市的發展史及消費史。北京宣武區金代遺址出土了很多在遼代土層之上,質量一般的金代定窯“尚食局”款瓷片,佐証了宋代以來模印紋飾從精細到粗放的一般演變歷程。同時也証實金代依舊沿用北宋宮廷“尚食局”的管理制度而非北宋定窯之尚食局。“尚藥局”款僅見一件,可能為北宋。很簡單,大量的北宋定窯“尚食局”、“尚藥局”款應該出土在古“汴梁”遺址才合情理。
北京歷年出土的資料証實:北京宣武區當時使用的白瓷類以龍泉務窯、定窯、磁州窯系為主,伴有少量的唐代邢窯﹔青瓷類以鈞窯、耀州窯及河南青瓷為主,伴有少量的宋代龍泉窯、汝窯、越窯、景德鎮瓷。北京崇文、東、西城區元代以后,除出土少量的元代鈞瓷以外,在明中期之前,出土的龍泉窯瓷和景德鎮瓷平分天下,其后景德鎮瓷便一枝獨秀。而磁州窯系瓷器在各地區自始至終作為陪襯而出土於社會下層居民區。靠宣武區較近的西城區一帶出土元鈞瓷量大,說明原金中都附近居民仍習慣使用鈞瓷。官窯和高質量瓷片均出自故宮、皇家別墅、寺廟、王府周圍的遺址區域內。周邊地區偶見官窯瓷片,多有鉅釘痕,可能為皇家賞賜不忍遺棄或普通百姓撿拾而繼續使用。明末清初偶見少量德化窯瓷。北京各遣址區內少見元哥窯瓷片出土,其可能多在杭州周邊區域銷售。
北京“毛家灣”出土了大量集中填埋的垃圾坑,由於其時間下限為明中期,因而伴生出土的其他窯口瓷片的下限便十分明確,具有極高的斷代參考價值。從名稱上看,“毛家灣”歷史上極可能是一個碼頭,此碼頭的廢棄時間應在填埋瓷片的嘉靖早期,這給研究北京歷史、地理、水系狀態也提供了難得的旁証。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北京西什庫大街及周邊地區出土的大量所謂“洪武釉裡紅、青花”瓷,而朱元璋時代的南京城內僅偶有所見,顯然這不符合常理,有悖歷史的真實。本書圖中所列國家博物館東出土的明永樂瓷片及正陽門西出土的永樂至嘉靖時期的瓷片,多有火燒痕跡,應為永樂、嘉靖時宮中失火后清掃出來的地表垃圾,填埋前曾被有意再次粉碎過。這兩處瓷片填埋地在印証了宮中豐富的瓷器品種的同時,也給研究北京曾經的城市建筑布局及地貌狀態,提供了科學的實証資料。另外,東城區智德巷及故宮西華門北集中出土的明、清祭器均需深入研究。
遺憾的是,由於思想認識和方法的偏差以及客觀條件的制約,直到全國大規模城市建設接近尾聲時,人們才意識到“千年一遇”城市遺址發掘的重要價值:一個原始城市的地下蘊藏了不容忽視的“原始垃圾”,不少罕見、珍貴,能補史証史的資料,為梳理這座城市的歷史和陶瓷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它們是全國各窯口瓷器在流通領域中實際消費情況的真實寫照,對於研究地方史同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潛在的經濟價值。
瓷片的標准器作用
“斷代”是陶瓷研究鏈條中極為關鍵的一環,許多后續研究和結論均須以此為前提。而出土瓷片在斷代方面所發揮的標准器作用更是無可替代的。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了數枚磁州窯墨書“至元”紀年款瓷片,卻未見有“至正”款。據文獻記載,至正年間在集寧地區爆發了農民起義,從而使研究者推測出,集寧路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生產時間為1340年前后,即至元或至正初期。這些磁州窯的“至元”瓷片,為同時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提供了值得參考的相對標准器。
傳統上的陶瓷紀年、墓葬紀年隻能給出某一時期或者下限日期。前代塔基出土物也有可能是后代的供奉器物,這些都或多或少存在著不確定性。元青花絕對標准器便是通過著名的“至正十一年”(1351年)象耳瓶的絕對紀年款而揭開了景德鎮青花史的秘密。近十幾年來,北京出土了相當一批絕對紀年款的瓷片,其數量之多可能已經超過全世界博物館的收藏總和。通過“毛家灣”出土的百萬瓷片的量化分析顯示,明代民窯干支款佔出土量的十萬分之一左右,相當於都城周邊地區官窯出土瓷片的比例。通過對成化甲午(1474年)至弘治己未(1499年)之間的絕對標准器分析,在眾多干支款出現的十五年(成化二十年至弘冶十年)當中,是嚴令民窯不准落本年款的時期。此前的成化本年款“大明成化年造”、“成化年造”和仿前朝“宣德年造”款,均是為了滿足當時北京官僚階層的物質與精神需要,隻不過是把官窯的“”改成了意思相同的“造”。然而,大約在1484年之前至1499年,這種民窯寫款方式顯然被禁止了。由此引發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大量干支、大明年造、天下太平、銀錠等款識。可能“干支款”這筆斷代財富,是景德鎮民窯出於書寫本年款“禁令”,無奈而為之的產物。而恰是這些絕對標准器,使我們得以理清明中期景德鎮民窯瓷器的基本特征與脈絡,繼而使成化早期及空白期的器物面貌清晰起來。
大約在1500年前后,民窯弘治、正德本年款重新登上歷史舞台,落本年款的需求悄然擺脫了官府的鉗制。直至清末,本朝款和其他款一起構成了官民同享的世界。北京出土“宣德年明”款青花折腰盤,是當時窯工信筆拈來的戲作。這一類本應在盤心書寫草書“福”字款的折腰盤,此前均被公認為洪武時期,現應更正為宣德前后。依此類推,原本陶瓷界認為是“空白期”的瓷器,許多都可能是成化早期所為,由於這一款識的發現使景德鎮青花瓷器在北京銷售的時間也至少向后推遲了四十年左右。而且,在其他相關層面上,它也為我們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題:洪武時期民窯是否燒過青花瓷?如果燒過,它究竟是怎樣的面貌?洪武時期的官窯青花、釉裡紅瓷該怎樣重新認識?總之,“宣德年明”款的出土對當下及后續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萬?帝遺詔:“織造、燒造悉皆停止。”天啟、崇禎的官窯停燒已為瓷界共識。然而子孫並未遵守其“金口玉言”,天啟時便借用他人的名義搭民窯燒造。米石隱,即明晚期書法家米萬鍾,曾為官江西布政使,擁有地便之利。天啟帝隻不過利用“米石隱”變換了御用器款識的寫法而已。崇禎黃釉刻茶花紋“崇禎年”款碗底,出土於清華大學西門外,周邊原為明代皇家達官顯貴別墅區和清康熙暢春園一帶。由此可見朱由檢當初不僅是“偷燒”,還避開皇宮在“偷用”,雖身為至尊仍不便明目張膽地違背遺詔。該器在填補了崇禎御用黃釉器空白的同時,我們可以從其明清官窯黃釉碗類中絕無僅有的宋元刀法上,看到曾懷揣中興夢的朱由檢與眾不同的審美情趣。從碗底表面嚴重的使用痕上,還可想象當初在崇禎時期,由於千年一遇的旱災而造成的“糧荒”之慘狀。進而依稀可見剛愎自用的朱由檢在內憂外患的情形下,尚存“艱苦朴素”的一面。黃釉“崇禎年”四字刻款,不但彌補了明清“御用”器的斷層,且為崇禎時期史學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質量上乘的“錦衣魏造”款,在北京承恩公桂祥宅附近出土,該地是否在明末時與“錦衣衛”宮外駐地有著某種聯系,有待進一步考証。有意義的是,“錦衣魏造”不僅為陶瓷研究增添了一個天啟標准器,還發現了未見史料記載的,公然把錦衣衛的“衛”字,改成魏忠賢閹黨集團的同音“魏”字。這為研究明代的宦官制度、錦衣衛制度及描寫魏忠賢“家天下”的歷史,增添了新內容。
瓷片紋飾的社會史學意義
與款識相比,中國陶瓷器物上的各類傳統紋飾,同樣蘊藏著豐富、深刻的人文信息,從而構成無以倫比的社會史學意義。在意識形態上,封建統治者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在審美上卻突顯出佛教、道家的表現形式。看似簡單的紋飾,需通過層層剝離方見其內核,才可領悟其原始的文化淵源,這無疑是一項極其複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尤其在以儒治世的農業文明社會裡,不同的紋飾代表著歷史曾經流行的不同音符,而從不同時期,不同頻率,不同層次主題紋飾的旋律起伏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統治者與百姓之間、異域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碰撞、交融,而最終還是要統一到皇權之下的必然狀態。
以中華民族的原始圖騰龍紋為例。現藏美國克利夫蘭藝術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U·S·A)的唐白瓷雙龍耳瓶,其雙龍耳明顯帶有新石器時代紅山玉文化寫意遺風,根據其中國北方民族的歷史傳承,它應為北方窯口燒造。宋元龍紋在瓷器上開始得到廣泛的應用——馬頭、鹿角、蛇身、魚鱗、鷹爪逐漸形成定式。由於元代官服上畫五爪龍,因而民窯瓷畫上的五爪龍便遭禁止。五爪龍紋的“元青花”存世極少,北京至今未發現出土,理應為元代晚期或明初作品。朱元璋從外族手中奪取政權后,便把龍紋變成自己的專利,無論爪多少,一律不准民間使用。這造成龍紋在明中期之前的民窯瓷器上完全消失。迫不得已,明早期民窯主題紋飾便以“四靈”之首麒麟取而代之。
許多紋飾都折射出不同時期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佛和菩薩的蓮花座之“蓮花”源於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即成為聖花。“蓮社”是始於東晉元興年間(公元五世紀初),慧遠為其蓮宗。現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U·S·A)的隋代青瓷印蓮瓣紋高足盤(高足碗、盤之類多為供佛之用),盤內在佛蓮周圍印有梵文,顯然為佛教專用供器。2006年10月,鄭州市上街區峽窩鎮出土一件唐代藍彩塔式罐,罐上繪有佛教的“卍”字符。在以藏傳佛教為“國教”的元代,佛教供器極其盛行,著名的元青花象耳瓶據說是來自北京智化寺的佛教供器(據黃清華、黃薇最新考証此瓶原為婺源縣靈順廟的供神器,詳見《文物》2010年第4期P64)。之所以元代青花數百年來不為人知,大概因其當時流行於漢地佛教和社會中下階層當中。朱元璋乃中國佛門弟子,后代出於“敬宗法祖”的需要,對佛教紋飾更加推崇備至。至成化、弘治、正德時登峰造極,使“十字杵”成為明中期民窯的主題流行紋飾之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清代除早期官窯出於籠絡西藏的目的而少量燒造“十字杵”外,不知為什麼?在民窯瓷器上卻蹤跡全無。
瓷器上的傳統紋飾“魚”,始見於現英國阿什摩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 England)藏的吳-西晉越窯青瓷刻花雙魚紋洗。庄子曾有做一條自由自在的“魚”的理想,即使在污泥之中也能自得其樂。就是說“魚紋”也表達出了“舉世混濁唯我獨清,世人皆醉唯我獨醒”的道家追求。宋元以來各瓷窯的“魚紋”均非常盛行,但大部分都表現在民間用器上,這應該與道家思想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有關。明代早中期官窯僅見少量魚紋飾,而由於嘉靖帝獨尊道教,崇尚“逍遙世界”,明晚期魚紋在官窯器中大行其道。幾年前,嘉靖五彩魚藻紋蓋罐還一直保持著中國瓷器拍賣的最高紀錄。由於庄子有關“禮儀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的思想符合朱厚熜更典改制的初衷,就連嘉靖早期所繪夸張而驕傲的花蕊,似乎也在想擺脫季節的束縛。連同中國傳統的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八仙)、仙藥(靈芝)、仙桃、仙鶴及各種祥瑞之物,均在嘉靖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由於朱厚熜手握皇權而又敢於面對自己本是“小宗”的現實,奮勇挑戰祖法、祖制,所以“正面龍”的紋飾便應運而生。一種紋飾的起源時間上限非常重要,例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無款刻綠龍紋小執壺的龍紋是側面龍紋,同樣的壺出土於北京下限為成化地層,應該是成化早期之器。另外,刻意點染仿宣德鈷料的感覺和“別有用心”的仿宣德款,也起始於嘉靖。究其原因是朱厚熜想表現出自己同樣是正統朱家合法繼承人而有意避開正德之祖父成化,導至在嘉靖期間隻有仿宣德款而沒人敢仿成化款。這與清代為籠絡人心,摒棄血緣關系而仿永宣的出發點大相徑庭。
為什麼在元末明初出現了一批超凡脫俗的“文人瓷畫”?歷史上,儒家思想對於有為的帝王來說是近乎迂腐的理論,但對於絕大多數守成的帝王來說,是用於“教化”的最好方法,而元統治者可謂例外。入主中原后,曾一度廢除了科舉,不但斷了文人的官路,還使他們落到了“臭老九”的地步。於是“淪為瓷畫匠”可能成為當時不少江南文人的無奈選擇,加之外銷瓷的刺激,客觀上便造就了元青花具有濃郁天然“文人風格”的瓷畫作品,眾所周知的江西高安出土的高足杯:杯的內底心書“人生百年常在醉,算來三萬六千場”,顯然是李白“人生三萬六千場”的翻版,其遒勁的書法功力亦絕非一般瓷畫匠所為。現藏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托普卡比博物館(Topkapi Museum)中的鬆竹梅紋碗,其畫鬆似朱德潤,竹似高克恭,梅似王冕,蒼勁隨意的實按虛起之筆頗有不遜元四家之勢。事實証明,在“落魄文人”參與景德鎮青花瓷的作之后,中國瓷畫藝術才得以大放異彩,加之“出口創匯”的動力,使元青花瓷器不經意間便成為千古絕唱。在明中期的瓷畫中,藝術家所必備的鮮明個性以及書法、文學、哲學諸方面的表現力都日趨減弱,暗示出通往“金榜題名”的道路重新暢通——就是說科舉制度的振興竟可以從瓷畫水平的下降上窺其一斑。
通過對瓷器紋飾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我們得到諸多有益的啟迪:每個時期的主題流行紋飾必然與其當時的相關社會歷史、政治、經濟背景相契合。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令地方不得貢酒,使其后洪武梅瓶極少見。洪武初期可能出現了歷史杰出人物紋飾,但朱元璋明令禁止在瓷器上畫帝王、先賢后,明早期的官窯瓷器便隻有以仕女、嬰戲、胡人為題的紋飾。“空白期”社會動亂,民窯瓷畫率先突破“禁令”的藩籬並導致“高士圖”首現在相隔五位皇帝之后的成化官窯瓷上,隨后民窯則亦步亦趨。
掌握相應的歷史背景知識,才有可能更加深刻准確的理解紋飾所表達的內容和寓意。正如讀一些古希臘的神話故事,便會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和雕塑家的作品把握得更加具體和豐滿。反過來說:元末明初流行的主題紋飾蓮花、十字杵、月映梅花、刀馬人物﹔明早期的福字、蓮花﹔明中期的十字杵、麒麟﹔明晚期的壽字、樹下讀書、一舉登科﹔明末清初的刀馬人物、老翁持杖、狀元及第等,都各自有其時代背景和深層次的社會原因。包括“十年動亂”時期的相關題材在內,“所創者,必有所因創也”。例如:適用於中、西亞地區的青花大盤,是否真的存在於節儉皇帝朱元璋的宮中?倘若存在的話,南京明故宮遺址區內為何極少出土,令人疑惑。發掘瓷片美學之外的社會史學意義,更是一項新奇而龐大的系統工程,它需要義不容辭的採擷者,更需要后來人逐一解析。
瓷片的教學實物用途
隨著國內文化收藏活動的不斷升溫,十幾年來,各地歷史上一些重要的窯口及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如景德鎮、西安、洛陽、開封、鄭州、杭州、南京、北京均涌現出一批自發的、尚缺乏科學發掘能力的“瓷片一族”,他們在宏觀研究遠比窯址發掘更重要且廣闊的領域裡各自馳騁。這些瓷片愛好者終日奔波於建設工地,樂此不疲,且大部分“拾遺”群體最初都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家中收藏頗豐者大有其人,藏者之間亦不乏相互交流,尤其是一些珍稀品種,入誰囊中,圈內皆知。無論你的原有認識水平怎樣,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緣,都有必要增加或補上瓷片這一課,瓷片會引領你少走很多彎路,少花很多冤枉錢。
必須承認,收藏愛好者,包括從事文物專業的研究人員在內,能夠親自觸摸稀有高檔瓷器的數量十分有限。而“上手”又是了解和掌握瓷器表面、內在特征的“必經之路”。多讀瓷片,尤其是那些佔器物四分之一以上的標本,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零距離接觸”實物的學習機會。“多觸而識之,見者次之”,況且,瓷片還可以讓你直面完整器所無法看到的地方。有了接觸大量瓷片的切身體驗以后,當你再去參觀博物館、參加拍賣會、逛古玩市場、讀圖錄時,就會對真實的器物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在瓷片上反復運用自己的視覺和觸覺器官之后,你會驚奇地發現,潛移默化之中,你已不知不覺地走進了陶瓷歷史文化的殿堂。
每個時代,每種器物均有自己的“體態”特色,以酒瓶為例:從宋、元、明、清的梅瓶器形上,可以明顯看出從修長到粗壯進而苗條的從實用到審美的演變過程。宋代的梅瓶小口、多無蓋。元代的梅瓶加上了鍾形蓋,把蓋拿在手中,可直接作酒杯使用。在明初復興傳統時期明永樂梅瓶,顯然與故宮藏唐代白釉梅瓶如出一轍。時至清代梅瓶已演變為陳設瓷,器口變粗,自然也就不再需要瓶蓋。壺類是從漢之前無流壺發展到晉的裝飾性雞頭流。繼唐代的短流壺之后,逐步演變為宋代的長流壺。景德鎮窯瓷匜來自元代而終於元代﹔瓷爵杯始於元代,延綿於明清﹔饅心底臥足碗源自明永樂﹔馬蹄形碗始於成化﹔帽筒、鼻煙壺多現在清嘉慶之后﹔蓋碗盛行於清晚期。這些都是學習陶瓷首先要掌握的基本常識,至於如何利用實物有效觀察標本,筆者有以下幾點體會:
1.瓷胎與底足:景德鎮元代以前“一元配方”時期的瓷器斷面,以糙米黃和粗石白兩種顏色為主,觸之有粗糙感,叩之聲音沉悶。底部較厚,足矮牆薄,多以墊餅燒、覆燒、澀圈疊燒為主。元代開始“二元配方”瓷器斷面,觸之雖略粗糙卻有堅實的手感叩之聲音清脆。為迎合蒙古民族的生活習俗和審美需求,器物整體厚重,碗足比例小且足牆多外撇,大碗足牆根厚度在一厘米左右,足內底不施釉,孔釘狀突起明顯。元晚期足牆漸薄,外足牆向明初的垂直過渡,這種形式也表現在同時期的其他重要窯口器物上。應該強調的是:所謂“火石紅”本身與瓷器的年代無關,一般情況下它隻與瓷石的含鐵量和淘洗次數及燒造技術密不可分。就是說,同時代同樣的器皿,有“火石紅”者次之。
元青花碗、盤底足的外足牆多無裝飾線。明早期官窯外足牆從無裝飾線到單、雙圈線演變。民窯外足牆單、雙圈線出現在宣德之后。由此可見,元末明初外足牆青花圈線及紋飾的一般規律是由簡入繁。明代高足碗,高足部分的接胎是由元代的胎粘轉變為釉粘,接胎的位置已不見多余的胎粘的擠出物。元代除少數仿定窯印花紋飾的碗足底心施釉外,均為露胎。明代以來,碗足底心普遍經歷了由不施釉到刷釉再到施滿釉的工藝過程:官窯足底心施滿釉約始於永樂晚期,民窯約在宣德之后,盤類器物施滿釉均稍晚,大盤底均不施釉,永樂官窯足底心早期粗糙、晚期光滑、宣德略粗、嘉靖輪旋紋明顯。內足牆與底部的交接處由直折變為弧折,出現在正德至嘉靖,盤類稍晚。足端內側普遍棱邊感強,而成化優質官窯足端已有“泥鰍背”現象。明代官窯早期的“月亮底”由相應外足根向內足根位置移動。明代盤碗類內足牆由離心至向心轉變,天順至成化為向心角度最大的時期。在外銷瓷的刺激下,從萬?晚期開始,由於加大了高嶺土的比例,增寬了燒成溫度范圍,增強了瓷的硬度,類似於永樂“甜白”經多次陶洗后的薄胎斷面之細膩,部分優質瓷的胎已有了潤滑感和絲光感。其內足牆與底的交接處至足端整體出現了弧度。
優質元青花、釉裡紅的胎質細膩接近於清“三代”。眾所周知,就瓷胎而言,雍正前后是景德鎮瓷的最佳時期。所謂細膩、堅硬的“糯米胎”,同樣表現在同期民窯器上,它們較其后的官窯瓷胎,在質量上均有過之而無不及。乾隆晚期,瓷器的胎質開始下降,器足和器底也相應變厚,胎的粗澀感與明代相似,較容易混淆。但因其含鐵量低,胎的白度和硬度仍明顯高於明代,再通過紋飾風格的比較,二者不難區別。同時代的官窯和民窯的瓷胎除厚薄和粗細的區別外(用放大鏡觀察,民窯瓷胎斷面的凹凸感較強),在白度上也存在色差。清雍正前后官窯與道光前后官窯胎的密度、絲光感相似,但后者的胎厚略粗且偏灰。另外,我們還可以利用瓷片的斷面,盡可能多揣摩足牆內側無釉處與胎斷面的相應感覺,為審視整器打下基礎。
胎的粗細與厚薄,與其氣孔率成正比關,粗、厚則多,細、薄則寡。一般而言,器形的大小與胎的厚薄也成正比關,大器形的瓷胎相對較粗,較厚,在厚胎的底部斷面時常可見“生燒”。永樂-宣德時期高38厘米的青白釉罐,器底厚度竟達3.2厘米,內心部呈黃色。嘉靖大缸底之斷面可見有意填充的粗沙粒。明代以來的器底普遍由厚趨薄,明晚期尤甚,導致塌底現象更為明顯。清代以前,由於二元配方和其他技術的不成熟及一元配方瓷器的機械性強度較差,大件器物往往走形,接胎處亦有較明顯的突起,器內尤甚。倘若在市場中邂逅一件無論是哪個窯口“存世悠久的陶瓷”,如果它在圓度、平整度、對稱性等方面均無可挑剔的話,你也許應倍加小心。順便說一點:北京出土金、元鈞窯系高質量的瓷胎細膩,色偏灰白、灰黃,普通者粗而灰黑。元龍泉窯瓷胎普遍粗而偏灰,明早期龍泉窯瓷胎接近南宋高檔瓷而偏白,與同時期景德鎮瓷胎相仿。
有關瓷胎的題外啟示:同樣是習慣於席地而坐的馬背民族,元代瓷器的厚重近百年一而貫之,而滿清僅在康熙早期反映出這一特點,其后便全面恢復舊制,通過改變自己而延長了王朝的壽命,可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2.瓷釉與青花:景德鎮宋代青白瓷釉屬於石灰釉(氧化鈣含量14%),釉內有聚沫般的釉珠,流動性較大,透明度稍差,多見開片,隻有釉較薄,正燒的“宋影青”才較透亮。元代青白釉由於燒瓷溫度的提高,相應改用石灰鹼釉,既解決了流動性大的問題又增強了透明度且少見開片。從釉的斷面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影響釉色深淺的因素除含鐵量外,還有胎質的白度、釉的厚度及透明度,而它們都間接地影響了青花發色。元代卵白釉的透明度最差,在一些國產鈷料元青花和永樂早期青花上使用,其發色明顯偏灰。而元代上乘青花瓷多使用青白釉,青花隨釉層厚薄、溫度變化而產生色階差別,進口鈷料濃重處呈現針孔狀凹陷,釉中氣泡相對密集。冷卻的速度快、釉的顆粒度大、欠燒和釉層較厚都會引發橘皮紋的產生,釉內氣泡也相應分散、放大,以永宣青花最為典型。厚釉積釉處呈水綠色,天順前后的青花紋飾由於釉層較厚青花常隨釉下垂而出現模糊現象。除明早期少量青花瓷釉由於含鐵量高而顯灰暗外,明代釉透明度最差的時期是嘉靖晚期至萬?早期。雖然青花發色主要取決於鈷的濃淡及鐵、錳的含量,但這一時期的青花雖使用回青料,但由於釉的透明度差,其發色極深沉,隻有少部分隆慶前后的青花發色格外幽倩,也是因為釉較薄的緣故。順便說一點,用放大鏡觀察,修復瓷器新舊分界線兩側的氣泡分布呈完全不同的狀態。
明宣德至成、弘時期,似乎是出於商品競爭的需要,景德鎮窯出現了大量仿龍泉窯的瓷器,其中有很多內青花外仿龍泉釉的產品,充分顯示出其表現力較龍泉窯更豐富的優勢。龍泉瓷斷面上可發現多次上釉的層次痕跡,次數越多釉色便越翠綠。通過色澤和色階的對比和底足的處理方式,較容易識別一次上釉的景德鎮“仿龍泉”。明天順至成化早期(1450年前后),由於釉層較厚,在青花繪畫的復筆、濃重處常出現明顯的凹凸現象,青花隨釉向下流淌,形似“鼻涕”,使其繪畫呈現一種朦朧之美和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嘉靖晚期和天啟前后,部分瓷器的釉中曾一度出現疏散的大氣泡,也是由於釉層較厚的緣故。天啟前后,由於胎質變化和釉層較薄,青花發色多顯淡雅,紋飾清晰,令人耳目一新。清晚期,尤其是道光年間,釉面平整度和透明度均差,足內更甚,導致青花發色暗淡,釉薄者亦顯現細密的橘皮紋,陳設類瓷器器底“波浪釉”尤為明顯。順便提一下器足內的縮釉現象:自然形成的縮釉點(俗稱“棕眼”)孔內多可見胎,且深淺不一,人為的往往不夠通透且較為一致。
釉面的手感,除釉的化學成分不同外,主要與燒造時間有關,用柴燒所需時間約為煤氣燒的一倍,因而玉質感強。明代的釉面手感較油膩,清代則較潤滑。釉面開片除有意為之外,往往與胎釉的本質和是否“正燒”有關,溫度的高低和冷卻速度的快慢會使胎釉的膨脹系數產生變化,造成釉面裂紋,就是說凡此類開片者,均屬質量問題。窯溫和燒造氣氛能使富含鐵元素的青綠釉顏色千差萬別,汝窯刻意追求“天青色”,往往是以胎偏灰黃,釉不夠潤亮且“開片”為代價的。
現代仿品的釉面,或過於深沉而呆滯無光,或過於輕浮而明亮刺眼,隻有盡可能多的“識真”以后,才能夠領悟什麼才是既熟悉而又舒服的所謂“寶光”。需強調的是,隻要認真觀察一片“進口鈷料”青花瓷的斷面,你便會理解所謂“深入胎骨”是完全錯誤的,擺在自己眼前的事實証明:無論何種鈷料,它們隻能融於釉中,凹陷感僅僅是釉面的變化而已。使用進口鈷料的元青花“鏽斑”多呈褐色,釉面較平正,永、宣青花“鏽斑”多現銀光且凹陷明顯。
3.瓷器口沿:元明時期景德鎮瓷器的口沿處,尤其是直口、翻口的外口沿處,撇口的內口沿處釉層均較厚,凹凸不平,局部高出體釉表面,用手觸摸感覺明顯。在不能直接觸摸的情況下,側光移動自己的視線時,光影中會出現由點或短線形成的跳躍感,似斷續的曲線。元代霽藍釉口沿由於釉層較厚,沒有明顯的“燈草口”,原因在於或在此位置作了扳沿凸邊或二次上釉處理,這些現象若單從器物表面上是無法觀察到的。永樂和成化早期有口沿處極薄的盤碗,釉的厚度超過瓷胎,對於探討修坯、施釉工藝極為有益。撇口器較為流暢的口沿端部容易受損,成化之后的官窯器多加一點小翻邊(口沿下方有凸出感)既能多挂釉又顯厚實。
由於施釉工藝的改進,從明晚期開始,口沿處積釉的現象逐漸消失,口沿內外均較平整。受外銷瓷淺腹大板沿的影響,明晚期盤碗類口沿處都有相應不易覺察的小扳沿,盤碗口沿外側斜削的現象增多,導致口端格外鋒利(此前僅見於明早期,但口端較厚),由於缺乏厚釉的保護,使用時口沿極易碰損,往往呈鋸齒狀。口沿位置的使用痕一般不易察覺,但觸之口端有異於其他釉面的澀感。
瓷片的鑒定與辨偽
鑒於瓷片收藏有助於提高眼力,其本身又具潛在的升值空間,時下有許多人對此趨之若?。當前,即使在施工工地上,也常有人“埋雷”,蒙騙那些盲目的初入門者。所以,在決定搞瓷片收藏之前,同樣需要做好相應的心理和技術准備,積累一些相關的辨偽常識。瓷片較完整器的鑒別相對容易,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1、出土痕:南方多見紅土,北方多見黃土。紅土是玄武岩等富含鋁質的岩石,在溫潤的氣候條件下強烈分解的產物。主要成分為三水鋁礦並含氧化鐵。由於紅土性黏,在瓷片斷面以至釉面上的附著性強,清水難以去淨,去除后的釉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失光。用化學膠粘劑做假的出土痕有的很容易洗掉,有的粘接過於牢固,用火燒后能聞到刺鼻的味道。黃土是在乾旱、半乾旱氣候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第四紀陸相沉積物,富含溶鹽及鈣質結核。由於黃土性極散,入水后易崩解,在瓷片斷面上可被輕易刷掉,隻留下一點黃色,細膩的胎斷面的土痕,不易察覺,釉面也基本保持本來面目。在城市原生垃圾層出土的瓷片斷面上,往往還殘留了不容易清除的有機物殘渣或黑色污泥,附著力很強。清理后的瓷片斷面,會顯露出與入土時間相符合的紅色或黃色,難以去掉,與未曾入土瓷片的表面白度截然不同。必要的話,可以用鉗子剝一點,以便對比。
2、使用痕:入土瓷片均為使用后所碎,使用痕因使用時間長短而多寡不一。釉表面與玻璃表面相似,均有不同程度的凹凸現象,凸出部分的釉面的器表容易受損。通常情況下瓷器(碗、盤)內底部會有一圈較重的、與其足徑和足厚相稱的摩擦痕。其他位置顯現相對較輕的深淺不一、狀如蛛網的使用痕。在使用時間較長的器底上,可見方向、大小不一致的片狀擦痕,其表面已失去光澤且邊緣模糊。器足著台面處有一周斷續且富有暗淡光澤的潤滑面,其形狀寬窄不一,與不著台面的足端無關。這些基本特征都與觀察傳世器物是相同的。當你經過長期認真地觀察揣摩,切實熟悉瓷器“飽經滄桑”的使用痕時,贗品多半就會在你的審視之下露出破綻。
3、氣孔率:現代仿品的粉碎、練泥、拉坯、入爐,多採用電力設備(高仿品例外),由於真空練泥,即使在厚胎斷面上也很難找到氣孔。倘若你在厚胎上找不到任何氣孔,且顆粒均勻一致,便應該再從其他方面綜合觀察了。一般情況下,瓷胎的細膩程度、厚薄的差別與氣孔率成正比。但細胎雖厚,氣孔率可能較低,粗胎雖薄,氣孔率可能較高。順便說一點:在胎質含鐵量較多的窯口(灰白、灰黃、灰黑、黑胎)如越窯、官窯、汝窯、鈞窯、耀州窯、哥窯的胎斷面上,可以觀察到釉與胎之間有一條由於化學反應而出現的白線。假如用電、氣爐燒,由於燒制時間短而不見白線。當然,高仿品用煤、柴燒便不會露出這些破綻。
如前所述,對時代繪畫內容、風格的理解,對釉面歲月痕跡的領悟,對形制特征的把握,都是需要長時間的摸索和體驗。同時,要克服瓷片“片面”的缺憾,就像在醫學院學了“解剖”,並不一定就馬上能成為好的外科醫生一樣,尚需要至少十年的臨床經驗。作為一個合格的陶瓷專業學者,需注重對瓷器內在和整體的把握,甚至對特定器物的尺寸和重量都要爛熟於心。
瓷片的后續研究價值
隨著絕對標准器的陸續發現,中國瓷器系統斷代的難題已經或必將破解。目前,多數景德鎮瓷器斷代的誤差可達到二十年左右。遺憾的是,現有人借用其他學科簡陋的設備,以“商業秘密”為由,隱瞞“老化系數”來源的數據。並且在標准器匱乏的情況下,除奢談“標形學”之外,還異想天開地搞所謂“古陶瓷鑒定中心”,實乃滑天下之大稽。
窯址、遺址原始瓷片資料的積累,是為后來者繼續攀登瓷山所搭建的“天梯”。同時也為陶瓷的未來學術研究及所在城市消費史、地理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由於每個人一生的所見、所識必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之通過表象、憑藉經驗建立起來的大腦數據庫做出的主觀判斷——世代沿襲的“眼學”、“類比學”,均具有某種不確定性,鑒定中難以避免盲點和失誤及既得利益的誘惑。目前所用的測試儀器,也多從醫學、地質學、材料學學科的設備“客串”而來。相對可靠的熱釋光“α計量識別法”,雖已能識別人工輻射作偽的把戲,卻存在“取樣”的缺憾。
鑒於造偽之風日甚,不少有識者正在研究不受人為因素干擾,專門為陶瓷而設計的定性、定量科學測試鑒定方法。而無論用怎樣的鑒定方法,都離不開可靠的客觀物質標准,沒有一個貫穿歷代、數量巨大的原始數據資料庫,科學鑒定是無法實現的。因此,瓷片是留給科研領域,留給后世的一筆難以估量的財富。既然科學技術能夠日新月異地改變著現實世界,那麼,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它終究也會改變目前這種令人茫然的鑒定現狀。我們鍥而不舍地搜集的瓷片標本資料,必將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日益顯現其作為陶瓷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瓷器之道妙不可言,意會重於言傳,隻有通過實踐切身感受並善於思考,方可領悟其中的原理與魅力。事實上,瓷器生產的源流、表面的紋飾及瓷器本身的質量與同時代的工藝技術、政治、經濟、宗教、集體心境都息息相關。甚至於從宮闈之變、官宦之爭、征戰殺戮到資本主義萌芽,都隱映在這千古不變的瓷器上。譬如:明代的仿前朝款出於“敬宗法祖”之需,清初仿“大明嘉靖年”款,既隱含著“反清復明”的深義,也體現出康熙帝的智慧。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所頒繼位詔裡有明確停止各地“燒造磁器”的詔命(《皇明詔令》卷七)。其后,除景德鎮外,龍泉窯供用器似仍繼續燒造,而鈞窯卻為何不見蹤跡?諸如此類的現象和問題還有很多,均需要大量的實物資料並結合歷史文獻進一步挖掘其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
恰如經濟學家德魯克所言:“今天佔主導地位的資源以及完全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要素,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和勞動,而是文化。”沒錯,就連2007年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都與西方文化密切相關。然而,應該承認,我們的文化目前在全球的魅力不足,而通過瓷片這一文化資源,可以為檢點、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提供一條通往世界的途徑,因為沒有任何器物能像陶瓷那樣把中國歷史文化如此眾多、鮮明而緊密地鏈接起來。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