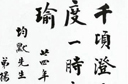去歐洲自由行的人私底下流行一個說法,叫做“宮(宮殿)保(城堡)雞(諧音,指基督教教堂)丁(市政廳)”。這些地方大家認為是必看的,博物館卻被大家忽略了。“博物館”三個字,就像它們的大理石建筑那樣顯得冷冰冰的,讓人難以靠近。湛藍的天空下,斑駁的老城裡擠滿了人,在刺目的陽光下貪婪地揮霍著當下的一切。蔭翳的角落裡,博物館作為歷史的廢墟被今天的時尚封存了。
但是藝術作品的原真性,隻有在博物館的現場可以目擊,長久的停留,你甚至可以嗅到大師的氣息,粗?的筆觸后邊是大師的眼神和力量。想到博物館三個字,總會有一些片段浮上心頭。
出門的時候帶了一本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散文書信集,一下子翻到有關博物館的文字竟讓我潸然動情。女詩人的父親是莫斯科藝術博物館的創始人,一生為博物館的建立而奔走。茨維塔耶娃寫道,當以亞歷山大三世的名字命名的精美藝術博物館不幸失火時,“爸爸默默地流著眼淚”,“母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鐘還想著博物館”,就連女詩人的外祖父“也把自己的部分財產遺贈給博物館”。為了兩代人的心血,茨維塔耶娃記下這樣的文字。只是,博物館還有人看麼?恐怕沒人知道一百多年前在俄羅斯的鄉下,有個打著赤腳,點著鬆明火燭學習古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的弗·茨維塔耶娃教授,憧憬著建立俄羅斯博物館的幻想。
喜歡淘一些畫冊,當然印制要精美。但畫冊就是畫冊,絕沒有博物館的“現場感”。曾經有一年夏天在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兄弟)美術博物館蹲了一個下午,用震撼兩個字來形容毫不過分。且不說它與聖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巴黎的盧浮宮、倫敦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齊名,讓我瞠目結舌的是原作的“光韻”。列賓的《伊凡雷帝殺子》看得我透不過氣來,畫面上,誤殺兒子的伊凡摟住垂死的兒子,那雙恐怖、悔恨、絕望的雙眼直視著觀者。陰暗的背景和深重的紫紅色調隻有在現場才更加“血腥”,瞪著驚恐眼珠的伊凡,那種無可挽回的殺子之痛力透紙背。站在蘇裡科夫《近衛軍臨刑的早晨》前,仿佛你也置身其中,過去都是在大16開的紙張上看,忽然畫面成了一面牆,它們之間的差距可以想象。畫裡的人物就在你的身旁,觸手可摸,巨大的體量感包圍了你,那種歷史的悲劇性沒法不擊中你。藝術作品的原真性,隻有在博物館的現場可以目擊,畫冊和其他的復制品無疑喪失了其獨一無二性的光韻。長久的停留,你甚至可以嗅到大師的氣息,粗?的筆觸后邊是大師的眼神和力量。
比起參觀博物館,人們普遍認為還不如看老城市政廳鐘樓上的整點報時“玩偶表演”,慕尼黑有,布拉格有,連捷克小城布杰約維採都有。但都是大同小異,幾分鐘就可以看完,還不用花錢。博物館不同,歐洲的博物館票價大都在12歐元左右,還要搭工夫,對於走馬觀花的人這不值得,對於購物者更不劃算,他們的要津在於哪個城市的哪個店,哪個牌子的東西更便宜。此外參觀博物館還得了解西方藝術史,不然進去了,十分八分鐘也得出來:有什麼好看的嘛。剩下的就是些老年人、專業工作者和遠道慕名而來的人,在殘破的雕像、斷裂的鎧甲和頭盔前,他們聚精會神地看著,琢磨著,他們和退卻的歷史一同衰老、枯竭,也和歷史一同沐浴在永恆的輝光中。
德累斯頓算得上是個博物館之城,“綠色穹隆”是歐洲館藏最豐富的珍寶博物館,交通博物館的宣傳語是“一座歷史博物館,五種交通方式”,錢幣博物館是另外一種歷史的見証,自然歷史博物館打開了人文科學之外的另一扇大門。我徑直進了茨溫格宮國家德累斯頓藝術博物館(古代大師畫廊)。一層大廳剛好在舉行“拉斐爾1510年在羅馬”特展,二三樓是常年展。這裡的鎮館之寶至少有兩件: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和喬爾喬涅的《睡著的維納斯》,單這兩件真跡,千裡迢迢跑過來就值。何況還有意外收獲。特展中展出了《西斯廷聖母》幾百年中的演變,一些后來者出於不同的目的對這幅名畫進行了顛覆。其中有兩幅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幅畫上小天使的形象被惡搞成了兩隻小豬,另外一幅是二戰勝利后,兩個持槍的蘇聯士兵站在畫面的兩側,一位救護的護士特別關照著小天使。一幅畫的變種見出了西方基督教精神式微的蛛絲馬跡,記錄了特殊的歷史時刻。《睡著的維納斯》在二樓,美人與風景一樣安詳,隻有現場才能真正感覺永恆的寧靜。雖說喬爾喬涅去世后他的朋友提香替他續完了作品(部分風景和維納斯臥榻的絲絨是他的手筆),但即便是仔細辨認也難以找到續作的痕跡。
博物館是藝術的畫廊不假,也是歷史的見証。60多年前蘇聯對德國的那次掠奪就發生在這裡。1945年德累斯頓被攻陷之后,1240幅畫作神秘消失了。毫無疑問是蘇聯人拿走了,但是沒有証據。直到十年之后的1955年,莫斯科普希金畫廊在當年的5月2日到8月20日舉行了“來自德累斯頓的展覽”,一切才真相大白。在藝術博物館的櫥窗裡,我親眼看到了當年的真理報,還有復制的照片,一些士兵正在把密封的畫箱從卡車上卸下來,另外的照片則是排著長隊等著看展覽的莫斯科市的市民。雖然這次展覽之后,蘇聯當局在兩三年內把從柏林和德累斯頓掠奪的150萬件藝術品陸續歸還給當時的民主德國,但這段抹不掉的歷史被博物館記錄在案。
下午六點差一刻,館內輕輕響了一聲鑼,示意觀眾閉館的時間就要到了。我一下著急起來,不少地方還沒有來得及看。此時一位四十幾歲年紀的母親在我的旁邊,正在給上中學的女兒輕聲講著普桑的《遺棄摩西》,一幅聖經故事畫。這並不是一幅出名的畫,但畫面的場景十分生動,摩西的父母正在把嬰孩放進一個用紙莎草做的箱子裡,讓箱子浮在尼羅河上。遠處一位婦女正在警惕地張望。女人關切的眼神,嬰兒熟睡的小臉,無論構圖還是人物刻畫堪稱上乘之作。盡管我聽不懂德語,也看得出做母親的循循善誘。女兒還是乖的,聽得也算認真。我好奇地跟著她們,見母親似乎並不在乎是否要閉館,仍然一幅一幅地講著,直到管理人員上前催促才最后離開。出了博物館,一高一低的身影已經很遠了,我還是望著她們。
街上的光線漸漸暗了,一切都在慢慢地減弱,腦子裡閃回著博物館裡的畫面,還有那些偉大創造者的全神貫注與生命的投射。隻要人類的歷史還在延續,博物館就不會消失。想到茨維塔耶娃書裡的另外一段事兒,心裡不由得庄嚴起來:在亞歷山大博物館開館的前一天,女詩人的父親,也就是館長陪著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女士獨自參觀(為了一個病人,在沒有開館的時候陪同參觀,這種事情怕是絕種了),沒有人說話,館裡靜靜的,一隻滾動的輪椅,沿著空無一人的展覽大廳,在白色的雕像之間緩慢前行……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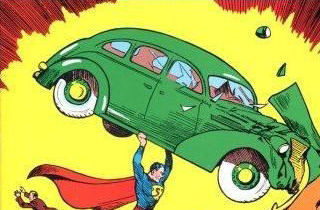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