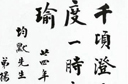留守中國藝術
二十年前中國當代藝術家的處境遠遠沒有今天想象的那樣輕鬆。當時,不少藝術家與批評家也許認為,似乎隻有到西方國家去,自己的事業才能夠有所發展。留在國內的藝術家和批評家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恢復他們的精神,盡管更為年輕的藝術家例如方力鈞和部分“85美術運動”中充滿活力的藝術家例如王廣義在很短的時間裡恢復了他們各自的藝術實踐,但是大多數藝術家還沉陷在對未來的生活與藝術的苦思冥想之中。
無論是無奈還是自覺,大多數人都留下來了,在反復的思考與蠢蠢欲動的嘗試中,八十年代部分重要的現代藝術家正在轉向當代藝術的實踐。生命存在著掙扎的本能,如果增添了理性,生命仍然能夠創造奇跡。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盡管現代藝術家們沒有展覽的機會,但是,社會生活中所充斥的另一種輕鬆——由商品市場帶來的可能性——同樣給予了藝術家繼續工作的機會。
市場問題就是文化問題
在冷戰結束進入后冷戰時期這個大的世界格局上看,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都微乎其微。那時,在國內的藝術家仍然沒有太多的機會展覽。在1993年6月之前,那時候隻有對藝術的信念和執著。盡管有高名潞等批評家於1989年2月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中國現代藝術展”,但是,這次八十年代的現代主義的最后“狂歡”並不意味著相關機構改變了其藝術的標准,更不表明一個新的藝術體制已經誕生。
此后,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就再也難以進入這個被認為代表中國藝術的殿堂。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開始了對當代藝術的支持,“廣州雙年展”就是在市場經濟明確為合法的條件下,在民間力量的支持下得以舉辦的。
在威尼斯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由於市場經濟關於流通與價值交換的游戲規則,在國內沒有獲得相關藝術機構支持的當代藝術家有條件被西方人帶到國際社會之中,那些本來就生活與工作在資本主義的歐洲和美國的中國藝術家例如黃永砯、徐冰、谷文達以及以后開始呈現面貌的蔡國強也在他們各自的特殊語境中努力參與國際性的展覽,並且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國際藝術圈﹔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侯瀚如、費大為這樣一些熟悉西方游戲規則的批評家也漸漸有了“國際策展人”的身份,隻要有機會,他們就盡力將中國的新藝術插入國際展覽,直至放入威尼斯雙年展這樣的展覽中。
無論人們對中國藝術家參與威尼斯雙年展有怎樣不同的評價,事實上,正是所有關注中國當代藝術的人們的參與,使得中國的當代藝術漸漸為世界所知,更為重要的是,事實、金錢、影響力也會改變人們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看法:2000年,上海雙年展開始採用接近國際規則的策展人制度,有不少西方藝術家參加了這次展覽﹔到了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有了中國館,盡管這年的“非典”影響到了中國當代藝術在威尼斯的展覽,但是,設立中國館表明了中國相關藝術機構基於自身的策略也開始了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挖掘。
市場和資本從沒脫離過藝術
在中國當代藝術還完全缺乏制度保護下的合法性的情況下,人們發現了市場對藝術的嚴重影響,人們對市場下的中國當代藝術產生了質疑,同時,對中國當代藝術與市場的關系的批評也來自部分西方人。可是,所有的批評者應該知道:威尼斯雙年展從一開始,銷售、資本以及利益這些問題就尾隨其后,除了1968年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發生的“風暴”對資本主義文化制度的控訴與反抗外,市場與資本從來就沒有脫離過藝術。此外,市場問題在中國還具有特殊性: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隻有市場以及由市場帶來的國際資源在支撐著中國的當代藝術,由於各方面的原因,一個科學的市場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發生實際影響的經濟危機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命運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國當代藝術該如何發展?
藝術創作——永遠是藝術家的問題,而作為批評家、策展人或者藝術史家的我們,卻可以通過對過往的一切進行反省,來梳理並評價之前的藝術歷程,中國藝術家和批評家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充滿著焦慮、荊棘與問題,相信那些早年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家和批評家都有著難以忘懷的感受與故事,而我們所感受到的正是由他們的那些感受與故事構成的。可以說從1993年開始的全球“歷史之路”不僅是中國當代藝術本身的歷史,也是全球藝術史在這個時期最為重要的一部分。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