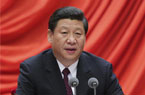馬健培的文與畫結集,叫《清風徐來》,是因為畫在扇子上,而文是由於畫生發而出的。以扇面的形式作書作畫,不必搜尋史料,記憶中就會涌上書聖王羲之曾經為老媼書扇這一故事。這些不必翻檢文獻就可以記得的扇面故事,已經很有趣了。
而歷史記載中的一些史料也頗有意味。鄧椿《畫繼》特別記述:“政和間,徽宗每有畫扇,則六宮諸邸競皆臨仿一樣,或至數百本。” 徽宗趙佶治國無方,藝術卻是高手,現存《枇杷山鳥圖》代表了宋代畫扇的成就——也不難想象,正是在徽宗的親自帶動下,其流風是如何廣被遠近的了!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最高超的宋畫藝術有相當一部分都創作於扇面之上。
南宋的書畫扇,基本是作於團扇或類似於它的變形之上。團扇又稱“紈扇”、“宮扇”,因它形似圓月,且宮中多用之。后來的制作者又別出心裁,乃有長圓、扁圓、梅花、葵花、海棠等樣式,因而團扇也多見於女人之手,我想,這大抵會比較有效地成為遮擋她們的害羞或掩面而泣之物。
明代以后,折扇成為書畫創作的主要形制,折扇也名“折疊扇”,又名“聚頭扇”,收則折疊,用則撒開,出入懷袖,再加上精雕細琢的扇骨的優美的詩畫,竟成為文人雅士的必備之物。比如說泥金、冷金、洒金、片金、色紙、銀箋等,雖說既綺麗又素雅,但要想在它們上面落墨和設色,卻都有一定的難度,明代大書法家祝允明就曾經把在扇面上作畫比做美女於瓦礫上跳舞,一般的書畫家,豈敢隨意渲染?
只是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一把大蒲扇似乎更合乎“人民性”。
曾經被嗤為封建余孽的文人畫以及許多與之相伴的東西,現在又慢慢地回到人們的生活中了。在“西化”與“新潮”之外,“本土”與“古典”更適合一些人的喜好,比如健培,便是如此。雖然我感嘆過,現實中國可能用當代藝術、先鋒藝術、實驗藝術、行為藝術諸種形式更能體現出它的“怪誕”,而國畫必須將一切來自於俗塵的東西排除掉才會為世人所矚目,像健培這樣毫無煙火氣地畫著崇山遠岫、溪澗翠柏,除了幾個會心人之外,實在不知道他的知音會有多少,這也難怪他時時將文筆延展到民國前。
正是因為國畫本來就有知音難覓一說,就如伯牙與子期一樣,一照面、一握手、一個念,都是通的,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語言。想健培扇面上的高山流水,暗地裡也必織了這樣的編碼。反過來看,這種難得的寧靜,在喧囂的當代藝術圈中,散發出的正是一種來自傳統的墨香。
健培的畫,似乎得自於龔賢為多,但又不是,難得的是在都市嘈雜中一種寧靜的心情,墨研清露,筆走彩箋,刷刷點點間,匠心獨具,筆隨意轉,化有限為無限,畫意與詩情交織在一起,無不體現可貴而孤詣的藝術苦心。我向來認為,中國書畫的背后乃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精義,存在與價值、心智與物象、知識與行動、人心與人性、人性與天道,無不在哲思與藝境中兩相浹化,一體不分。沒有哲思,中國文化的精義則無法落實於點線之內﹔而沒有藝術,中國文化也將陷於干枯,失去生命的潤澤與情思的靈動。
無疑,藝術是人的生命的投射,它把我們生命中的偉大與渺小都包含在內。但藝術家優秀與否,就在於他是否能夠區分出什麼是偉大什麼是渺小,而且這會成為他的藝術追求的一種動力。他必須將這種追求牢牢地樹立在自己的內心之上,鍛煉自己的力量,體認世界無窮無盡的美,建立自信,去看這世界,去表達這世界,因而我相信藝術正是表達這種認識並得到最終的自由與快樂。為此,它甚至可以成為一種信仰。
西方藝術分“新舊”,中國藝術分“雅俗”。在西方人眼裡,“新”的要代替“舊”的﹔在中國人眼裡,“雅”的要超過“俗”的。真的好畫好文章,必是他的人、他的心比他的文章比他的畫還要好,如果他的人他的心不及他的畫與文,那文章與畫雖然好看,其實只是浮花浪蕊,並不曾直接明心見性,更不能尚雅樂道了。健培書中諸文,以及他的繪畫方面的表現,無不歷歷在目,不必我多饒舌。
我與健培的交往是比較晚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之間的溝通與理解。一次我拿著小相機坐在他的邊上,看著他與別人對話,眼睛裡充滿著質疑,我順手一拍,給他看,他竟然覺得這種犀利的目光並不屬於他,因而很不好意思地用手將臉捂住,我也順便將此拍了下來,於是我覺得,健培本來是犀利的,只是他覺得這樣藏起來會好一些。可是,我不能不讓他有些失望地說,這種鋒芒是藏不住的,收在此集中的文字,已經將他“出賣”了,而我的鏡頭,不過是將這一剎那永恆化了而已。(劉 墨)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