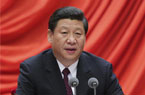《論語·八佾》有這樣一段文字:“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當學生子夏問老師孔子,文採與素質到底是什麼關系時,孔子說:“先有可以承受筆墨的素質,然后才能繪畫。於是,子夏把這個意思引申到道德層面說,如此說來,禮是后於忠信等素質的了。孔子非常欣賞子夏這一引申,以為子夏很能領略他所提倡的“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這一教導的真諦,很可以與之論詩了。的確,要辦好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須首先具備辦好這件事情的主、客觀條件。還不會走就急著跑,那是必定要跌跤的。我看過健培若干繪畫作品后,留下了一個十分明確的感覺,就是他在繪畫上的一切成就與建樹,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繪事后素”這一真理的感召下得到的。
大約在十七八年之前,我結識了健培,最初的印象是,他有一襲偉岸的身材,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副聰敏的頭腦,卻不知道他還有一腔精於繪事的睿智。直到最近幾年,才知道他是中國畫壇上新文人畫派的重要一員。起初我在中國新文人畫派的一本畫集上,看到過幾幅他的畫作,頗覺別致,這才有意識地關注他的畫藝。接著看到了他題名《累了·歇歇——馬健培水墨畫集》,這是一部大寫意間夾現代東方藝術氣派的花鳥畫專集,在集子的前言裡作者說用“累了就歇歇”作為書名,是想說集子裡的畫都是畫著玩的,過把癮就知足。這番語言與集子裡的畫,似乎與中國文人派繪畫風格有些“風馬牛不相及”。我不知道“新文人派”之名是如何界定的,但顧名思義,他應該是傳統文人派的新生,可集子並非如此。正疑惑間,又看見健培的題名《萐風雅韻》的山水扇面專集。整集除一幅工筆奇石外,全是皴擦有加、富於古風的山頭畫。細看每幅山頭,盡皆有筆有墨,布局輪廓明晰合度,皴擦點染無不扎實厚重,與時下一些輕狂討巧之士筆下的,或有輪廓而無皴法、或有皴法而無輕重背向的,無筆無墨的作品迥然不同。看得出,健培筆下的山石是很講究法度的,畫石注意三面,畫山注意三遠——雖然只是山頭。在皴擦點染上下了很大的工夫,披麻皴、解索皴、折帶皴、雲頭皴穿插使用,十分得當,尤其是雨點皴,用得最力,很得黃賓虹點皴真諦。有的山頭,干筆雨點皴,看來何止三層五層十層八層?后來才知道,他有時候一幅畫竟然皴進萬筆,由此看到了健培新文人畫的端倪,去年初又得了由劉二剛先生題名,並由劉先生與王和平、王孟奇先生作序的健培新作《老馬的山頭》。這本畫集有相當規模,收畫九十五幅,在畫的空當中還刊載了健培極具風趣的近四十篇筆記散文。這可能是健培的一部階段性的繪畫結集。
健培的畫,經歷了一個由放任不羈到回歸傳統,從“放心”到孟夫子的“收放心”,再到融古自創的過程。說到繼往、繼承,健培是從這樣的兩方面起步的:一方面,從臨摹前賢的筆墨開步,可看到“四僧”、“四王”直到黃賓虹、李可染的影子,可以斷定,健培一定在臨摹“四僧”(特別是弘仁與石濤)、“四王”(特別是王石谷與王原祁)和黃賓虹、李可染上下過苦功,說不定他還臨摹過唐宋之荊、關、董、巨及元之四大家。健培為了把畫畫好,一直埋頭讀書,書畫的、文學的、史學的、哲學的、東方的、西方的,隻要有空,便夜以繼日地讀。健培有一個能“說文”能“解字”的親密伙伴,那就是他的夫人林姝,林夫人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愛書嗜書,由博物而歷史而文學而哲學……林夫人的嗜書,對健培的讀書,無疑是一大助力。他們夫婦,無兒女之累,全部業余時間都用在讀書和書文切磋上面,說他們“學富五車”是一點也不夸張的。
我向健培提了一個問題,我說足下甫出“不惑”,尚不及“天命”,正富於年華﹔足下的大山剛露出地面,正蓄勢待發,待到足下“耳順”之年,能聽到足下“全山”的拔地而出的轟鳴嗎?健培說有這種可能。為看健培的全山,我拭目以待。(辛冠絜)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