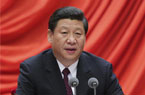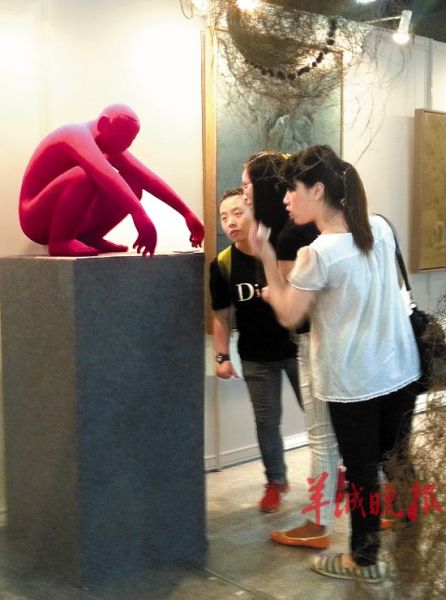
新星星藝術節展覽現場
●中國畫潛力股人群鎖定60后
●當代藝術潛力股人群鎖定80后
特邀嘉賓
鄧箭今
(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第四工作室教授、油畫系副主任)
周湧
(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教授、嶺南中國畫研究院副院長、碩士研究生導師)
嘉賓主持
趙利平
(收藏家、資深藝術評論人)
原本說了不再出讓自己藏品的比利時收藏家尤倫斯夫婦,最近在香港蘇富比秋拍又拿出了一幅曾梵志的畫作《最后的晚餐》,最終拍出了1.8億港元的高價。
追蹤再次賣畫的理由,尤倫斯夫婦稱:“作為收藏家,我們的職責是提攜年輕一代藝術家。”他們將用拍賣所得繼續買進新晉藝術家的作品,並維持手中約1000件的藏品量(大多來自中國藝術家)。
對新晉藝術家的關注,挖掘潛力板塊,也是眾多收藏家最樂此不疲的一件事。一大批80后的年輕藝術家還未站穩腳跟,90后的新銳已經開始冉冉升起。他們都是生活在中國經濟復蘇后享受后工業文明和網絡信息化的一代人,不單知識面廣,對東西方文明也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
如今年國慶節第一次落戶“藝術廣東”的新星星藝術節,還有之前的“青年100”、“廣州美院畢業生優秀作品提名展”,在廣東,對青年藝術力量的關注與推廣頻率越來越高。很多人想知道,如何以藝術的眼光評判潮水般涌出的新銳藝術家?
1尋找新銳藝術家
趙利平:關注藝術新銳,我們就從剛剛結束的新星星藝術節談起吧。這是一個全國性青年藝術家海選平台,很多人希望從中尋找美術界的明日之星,但今年分量最重的“藝術場”大獎仍然空缺。鄧老師,你們7位終審評委是以怎樣的藝術角度及標准來選出優秀作品的?
鄧箭今:這一屆的新星星藝術節終審評委有7個人:何多苓、呂澎、劉家琨、汪建偉、葉永青、展望和我,我們投票評選出了7位獲獎者。很多人都在問,我們是以什麼標准評獎的?對這個問題,我們7人私下並沒有討論過,但說出來的話非常相似,我們都在尋找一種不同類型的藝術,尋找一個能夠沉下心來做一件事情的新銳藝術家。我們最后評選出來的作品,都是那種默默無聞但是下足工夫的作品,這些作品沒有受到外界的影響,顯得非常干淨。“藝術場”大獎已經連續幾屆空缺了,沒有發現符合這個大獎的作品,那就讓它空缺吧,我們不是為了評獎而評獎。
趙利平:與往屆相比,今年這批參賽的年輕人在獨創性等方面有沒有什麼突出的特點?
鄧箭今:求新。不擇手段的求新,這點我覺得也是對的。他們要想盡辦法不要雷同,比如有人就直接畫出了一幅說明書,雖然表現手法略顯稚嫩,但起碼是一種全新的嘗試。但也有一撥人參賽純粹是為了獲獎,他們採用了很多討喜的辦法,但我們很多評委不喜歡這些東西。很多人在創作中會反問自己:我老是這樣畫下去有意思嗎?新銳其實就是探討一種可能性,去看看還有多少藝術創造的空間。
趙利平:現在畫畫的人太多了,一場比賽就有幾千人參加。對年輕人你有什麼建議?
鄧箭今:我覺得可以將心態放慢一些,在某些問題的思考方面可以再尖銳一些。然后是要勤奮、多讀書。
2什麼是新銳藝術?
趙利平:除了學術上的海選,現在一二級市場上的新銳專場也越來越多,這與收藏家尋找潛力板塊的想法是吻合的。請兩位老師談談對新銳藝術的理解。
鄧箭今:什麼是新銳?好像也沒有一個很確切的定義。所謂新銳,我覺得就是一種先鋒的姿態,對過往事物的一種新的顛覆,不用去介意它究竟代表什麼主義。每一個時代,每一個階段裡出現的一種新的類型,我們稱為一群新銳的年輕人對藝術的追求,包括對傳統的一些模式、樣式、觀念、方式的調整。
趙利平:那麼,是不是凡是新鮮的、陌生的事物,我們都可以稱之為新銳?
鄧箭今:不是,它必須呈現出一種態度,並且帶有實驗性,但是最后得到了肯定。
周湧:我覺得實驗性是第一點,然后是反思性,要對過去進行批判和反思。現在很多年輕藝術家也都在思考,怎樣才能與上一代不同,我想這就是新銳。新銳不是一個藝術方式,它只是代表一個年齡層。比如當代藝術裡面的新銳力量,一般就是指80后和90后。
鄧箭今:也有一些人會比較在乎風格或樣式。比如有段時間卡通很流行,也確實好賣,導致一大撥人跟風。其實卡通最早出現在廣東,當時是真正形成了一種主義,因為它帶有綱領並真正提出了一些問題。之后在四川成型,剛好與商業接上軌了。
趙利平:近幾年廣東的新銳藝術有沒有發生什麼標志性的事件?
鄧箭今:目前還沒有出現標志性的事件,廣東年輕藝術家的反叛和實驗精神主要是體現在作品裡面。
周湧:可能有一些事件,但是它們的力度不夠大,沒有產生像北京那麼大的轟動效應。
趙利平:前年廣州美術學院的畢業作品展,有位女學生的作品《30天,600例》是由35個早期人體胚胎做成的,當時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名女學生關注的是越來越普遍的墮胎現象,無言地表達女性身體所受的傷害。這種表達算不算新銳藝術?
鄧箭今:算,但它持續的時間太短暫。所有先鋒性的東西都帶有連續性的特點,像裸奔這種持續性很短的過程,我們很難把握它是行為藝術還是一場鬧劇。所以我認為所有的藝術作品必須有一個持續性,這樣才能有足夠的空間去干淨地陳述。
周湧:鄧老師講到了一個關鍵點,就是要回避藝術的即時性體驗。因為這種體驗來得快也去得快,有時候不一定能夠成為真正有高度的藝術品。真正好的藝術就像酒一樣,有一個體驗提純的過程,而有些具有轟動效應的短暫行為,我們稱為藝術事件。
鄧箭今:其實我們不要過度糾纏在新銳這個概念裡面,這樣反而會讓新銳變成一個很空泛的事物。
3現在廣東新銳藝術的特點
趙利平:說一說廣東的新銳力量吧。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現在廣東的當代藝術群落和自我組織的現象還是很引人注目的。
鄧箭今:廣東的確有一群很不錯的年輕人,但他們跟北京、上海、成都的年輕人不一樣。廣東的年輕人更固守本土的文化,但也局限在本土裡開展藝術批評,廣東的這種傳統有利有弊。好的是它可以讓人沉下心來研究一種藝術態度或者樣式,這是廣東相比其他城市做得最好的地方。但由此引發的新問題是,廣東的藝術沒有北京、上海、成都交流那麼頻繁,過於局限在這種相對封閉的群體性、地域性裡面,最終會帶來一種前進上的停滯狀態。
但是,在北京或其他地方的當代藝術家,很容易產生焦慮感。因為在那裡每天都有新的機會,這種新的機會導致年輕人比較著急,好像出場就必須要獲得成功。而且那些地方還真的每天都有人成功,但每天也都有人失敗。在北京,藝術家容易獲得機會,也容易變得浮躁,這導致藝術家從出場開始都是焦慮和冒險的。
廣東這邊的年輕人就相對穩定得多了,有展覽就去參加,沒有的話也覺得無所謂,這就是一種相對安定的狀態。不像在北京,那是一種漂的感覺,漂的不僅是生活,還有藝術。在廣東,成功慢一點無所謂,但在北京,一旦慢了就會馬上被淘汰。
周湧:如今的新銳藝術家,跟我們那個年代的新銳也有很大的區別。在我們也是新銳藝術家的時候,我們對社會有著強烈的關注,有一種反抗意識和批判意識,有強烈的知識分子情結和精英意識。現在的年輕人,這種意識好像淡了些,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批判,相對平和一些,沒有我們那時候強烈。或者說,他們現在的這種表現可以稱之為微體驗、微批判、微反叛,這是我體驗到的兩個時代的新銳的一些區別。
鄧箭今:我們那個時候的藝術經常與社會責任捆綁在一起,並注重提出社會問題,比如當時有很多先鋒的詩歌、戲劇等。
周湧:還有音樂。從藝術的選材和表現上,我們當時非常注重將個人經驗轉化成一種社會經驗,現在的藝術家不需要對社會表達他的看法和責任,這是現在的新銳與我們當時最根本的一個差別。
鄧箭今:現在的網絡時代,讓很多東西很快地融為一體,藝術風格最后也被模糊化,不像以前,南方和北方區分較為清晰。
4中國當代藝術翻身了?
趙利平:最近香港蘇富比秋拍,曾梵志的畫作《最后的晚餐》拍出了1.8億港元的高價。有人認為曾梵志的成功是拿來主義的勝利,認為這是一種抄襲。你們怎麼看?
鄧箭今:在藝術創造中,很多人都會借鑒一些樣式,或者作品帶有一種他人的一些痕跡。
周湧:在西方,也有一些比如給《蒙娜麗莎》畫上胡子等調侃名作的行為,這只是一種很傳統的做法。
鄧箭今:上世紀90年代很流行的偷換概念就是指這種行為,拿他人作品的一部分融入到自己作品裡面,這不是抄襲,因為大家一看都知道,那就是拿一張名畫來做新的創造。
趙利平:1.8億港元的高價出來后,有些人將此視為當代藝術的翻身。兩位老師怎麼看待中國的當代藝術?
周湧:中國的當代藝術,有一個缺陷就是模仿太多,沒有真正創造出在世界上拿得出去的藝術語言。當代藝術經過模仿期之后,還必須要用當代藝術的語言來表達本土發生的事情。我覺得,用當代藝術、實驗藝術的方式來表達這種本土性,或者說用本土資源和傳統資源來做當代藝術,代表著目前整個中國新銳藝術發展的一個趨勢。傳統和地域應該重新成為一種資源,而不再是成為一個反叛的對象,這是現代新銳要考慮的問題。
另外,我認為當代藝術要成為大眾知識的一部分,語言的表達很重要。當代藝術裡面很多關鍵詞大眾比較陌生,這也是當代藝術知識普及需要做的內容。
鄧箭今:但這30年當代藝術已經發展得夠快的了,我們幾乎把西方美術史刷洗了一遍,現在可以慢下來反思一下了。我說的“慢”不是怠慢的慢,是一種學會等待的慢。現在的人都很著急,今天你的價位比我高,明天我要比你高,你畫了兩張,我畫三張,在追趕的過程中損失了很多思考的東西。
周湧:美術史以后記載這個時代,會叫浮躁的時代,留下的東西不多。
趙利平:浮躁的時代找到一件不浮躁的作品很難。
鄧箭今:是很難。要在一大堆實驗性作品裡面,找到真正很好的作品,能夠站住腳並且繼續前行的作品並不多。但是我相信,有那麼一小撮人可以形成很好的模式和榜樣。
5什麼板塊值得收藏?
周湧:如果從收藏投資的角度來說,現在有兩大板塊值得投資。一是傳統的國畫,另一就是當代藝術了,夾在中間的是沒有意義的。
鄧箭今:對!夾在中間的最尷尬。當代藝術因為其藝術形式還沒有最終蓋棺定論,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走到盡頭,這種期待感很重要。但是現在很多人在創造中會走向表面,變成偽古典、偽前衛。
趙利平:現在很多人都在尋找下一個曾梵志,能夠成功的藝術家,有沒有一些共同必備的特質?
鄧箭今:我覺得這樣的人本身有一種底氣存在,他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以及動手能力都會比一般人要強,同時性格開放,具備一定的交際能力。而且肯定是喜歡閱讀、喜歡實驗的人,喜歡不停地尋求解決問題的人。
周湧:還有一點,作品必須具備有效性。首先是題材的有效性,比如說有的題材你無論怎麼畫,現在都不會有人關注﹔其次是技法的有效性,比如有的題材適合冷靜的筆法,但你卻用了很瀟洒的筆法,最后畫得再好都沒有效果﹔最后是造型的有效性,有的畫適合很憂郁很病態的造型,如果你把他畫得很飽滿、很雍容那也不對。
這是作品生效必須同時具備的三個條件,因為繪畫是一種形象藝術,就擺在那裡,不用講多余的話,如果你找對了,作品就具備了日后拍高價的可能性。
當然,一件能夠傳世的作品還需具備三種特性:第一,要有自己的獨特性﹔第二,能夠滿足普通大眾的審美﹔第三,具備創造性。
鄧箭今:有些作品會給你帶來一種愉悅感和思考,這種感受不是因為作品表面的美麗和真實,而是它會在背后勾起你一種欲望或者沖動。
周湧:唯美的繪畫在今天已經算不上一個唯一的標准,但中國目前還是處於這樣一個最初級的階段。隨著知識階層進入到藝術品投資時代,對繪畫的審美標准會隨之進入到第二個階段,有沒有創造性、實驗性,將會開始成為大家比較關注的一個點。
鄧箭今:能夠傳世的作品,要具有一種獨特的無法代替的風格,即使過去很多年還會引起關注,並且有可能改變之后美術史的畫風。
但說到收藏,其實中國的收藏家當中,真正懂藝術的人不多,他們只是把藝術當做商業的一種砝碼來玩。看到《最后的晚餐》拍出天價了,他們也爭著把錢投向同類的作品,這是一種投資者的心態,也是一種投石問路的做法,這些收藏家急需被引導。
周湧:如果是投資傳統國畫,建議從50歲左右的畫家當中尋找潛力股,因為中國畫是一種老年人藝術,需要時間的積澱。如果你投資一個畫國畫的年輕人,起碼要等上幾十年,因為國畫沒有新銳一說,它就是一個老年人藝術。
而如果是投資當代藝術,我建議你從30歲左右的年輕畫家裡面尋找潛力股,相比投資中國畫,投資新銳年輕的藝術家回報時間更短。
知多D
廣州比較成規模的
六個藝術群落
●廣州美術學院老校區周邊的Loft345群落
(鄧箭今、胡赤駿等8人)
●海外花園群落
(鄧瑜、伍思波等10人)
●廣州大學城群落
(羅奇、劉可、陳子君等)
●小洲村群落
(林偉祥、柯坎法、張湘溪等20人)
●華南師范大學的伍仙橋群落
(江衡、黃海清等20人)
●番禺市橋的3號線群落
(楊小彥、何建成等十余人)
延伸閱讀
米莉恩·尤倫斯:
我們的收藏目標是中國當代藝術品
尤倫斯夫婦青睞的到底是哪些中國藝術家?米莉恩·尤倫斯透露,他們夫婦在中國最早購入的畫作是劉小東的《Relaxing in the Spring》。而《最后的晚餐》是他們在2001年的時候,以2萬美元的價格買下的。
在她看來,中國藝術界的轉折點是1997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從那以后,中國藝術品開始成為藏家追逐的東西。在此之前,他們僅屬於一個小圈子裡的藏家。
在畫作的選擇上,米莉恩·尤倫斯這樣說:“我能看上的是那些讓我興奮得起雞皮疙瘩的藝術品。”
“我們的收藏目標是中國當代藝術品,過去是,將來也是。未來,我們的收藏重點將集中在冉冉上升的年輕藝術家身上。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欣欣向榮,年輕藝術家不斷涌現,全世界的藏家都對此感興趣。”
“我們藏有一些非常年輕的中國藝術家的畫作,還沒有什麼畫廊去挖掘他們。我剛剛從徐渠的工作室買來了幾件作品,價格從1.3萬到2萬美元不等。我們還買下李姝睿、仇曉飛、趙趙等年輕藝術家的作品。”(許悅、樊美玲)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