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文化”的美術猜想

太陽紋彩陶片

圈足盤 本文配圖由浙江省浦江縣上山遺址管理中心提供
上山遺址位於浦陽江上游的浙江省浦江縣黃宅鎮上山村,是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考古學家在浙江省浦江縣發現上山遺址。此后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者陸續發現了一萬年前屬性明確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遺跡和大量彩陶遺存。
關於“上山文化”的研究文章很多,筆者作為來自“上山文化”發現地的文化工作者,想從美術的角度談談對“上山文化”的認識。
仔細觀察上山遺址出土陶器的造型和紋飾,就能感受到先民的智慧及審美。這些文物,無論是造型還是紋飾,古朴而精美,體現了“上山人”對自然的觀察和描摹,對天地萬物的思考。
在上山遺址出土的文物中,大口盆最具標識性:大敞口、小平底(極少量有圈足、齒狀足或乳狀足),口沿及器腹上壁向外翻,口徑大於通高,體量大、器壁較厚,造型古朴大氣。作為“上山文化”遺存的代表性器具,大口盆的材質雖看起來粗糙,但紋飾縱橫,盆口極大,從實用價值來說,類似於碗。大口盆外表有白色紋路,赭色中帶有殷紅,在審美意義上有一種高級感,同時又與成熟的稻谷顏色相同。先民們就地取材,揉土為器,在不經意間,造就了傳世經典。夾炭胎是大口盆最為典型的特征:在陶胎的內外壁均有紅陶衣,陶胎中摻和大量稻殼。這些“與陶共存”的稻殼,如今已成為上山先民馴化水稻的直接証據。
藝術源於生活且高於生活,是人類對生活的記錄和對自然的寫照。上山遺址出土的陶壺,造型精致,壺身的圖紋似兩條騰飛的龍。這兩條龍是大寫意的,也可以理解成兩道閃電。壺頸長且富有曲線美,已接近現代意義上的花瓶。
一切美術的緣起,皆是生活,首先是出於實用價值的考慮,其次才是美化生活。既實用,又美觀,是人類制造生產生活工具的標准,自古皆然。“上山文化”中的石磨盤和石磨棒,看上去類似現代水泥構件,其表面之光滑,使人想起“雖由人作,宛自天開”這句話。
上山遺址出土的石鐮,考古學家認為可用於水稻收割。由採集野生稻到人類種植水稻,其意義在於從遷徙的生活狀態,過渡到定居的生活狀態。擇定一地而居,既免去了頻繁奔波之苦,同時也讓人有時間靜下心來,謀劃自己的未來,包括制定生產計劃、選擇生活方式等。筆者認為,正是在這個時候,以制陶工藝為代表的美術開始萌芽。石鐮一邊的齒狀,從實用價值來說,便於收割水稻等植物﹔從美術價值來看,是一種連綿的起伏,一種水波紋,讓人感到曲線之美。
“上山文化”中的太陽紋彩陶片上,不僅有太陽的圖案,而且在太陽圖案下方還有三角形對沖圖案。這表明人類已經學會從日月星辰等天象變化中汲取美學內涵。而“上山文化”中的圈足盤和圈足罐,以通體裝飾的印紋、刻劃紋為主要特色,証明上山先民不再滿足於陶器的實用需要。
在文字尚未發明之前,美術是承載文化和思想的重要載體。“上山文化”陶器的紋飾盡顯質朴神秘,可以理解為一種粗獷、質朴、本能的藝術。先民們以自然為師,以天地萬物為參照,用簡潔的線條構成圖案,反映他們所認知的世界。單純與簡約同在,變形與夸張並存,體現了“上山人”粗獷而率真的“美術觀”。
去年底,浙江考古與中華文明系列“‘萬年上山:稻作之源·啟明之光’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埃及舉辦。展覽以“上山文化”的稻作、定居和彩陶為主題,通過呈現“上山文化”稻作証據、定居村落、陶器技術等重要標識,帶領海外觀眾踏上萬年時空穿梭之旅。我想,這也是一次中國向世界展示人類早期制陶工藝和美術成就的旅程。
“上山文化”的美術元素,蘊含了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念,體現了中華先民審美意識的覺醒。勞作、自然與美術是水乳交融的關系,人類文明就在這一筆一畫間不斷豐富完善著。
(作者系中國攝影出版社總編輯,北京市寫作學會副會長)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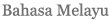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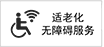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